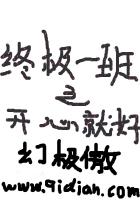那地方,有很多村落还实行配给制,没有牙膏,男人剃须用的是发亮的匕首,女人头顶打制粗陋的纯银发簪,但他们的汽车有最先进的定位系统和电子导航仪,他们的居处每隔十里就有网站连通世界各地,这里有十几个国家的自愿者在教习语言,那里的沟通方式是:心与心相通。每次开课,先是一大帮人在站直了,在胸前画一个“心”字。我上课没有这条,我通常把教鞭一拍,他们都直了……后来是二拍,再后来是三拍,拍到第五拍也没有认真听讲时,我就把他们带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劳动改造成了他们最喜欢的课。
年纪小的玩泥巴,年纪大的做“木槽船”,更大些的学手艺。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敢讲这里是绝对的天堂,哪怕是厕所——除了浓浓的臭味外建筑风格也颇具浓浓的民族味呢。我天天生活在歌舞升平中,到这家转转,那家尝尝,一喝酒就是通宵,一唱歌就是一宿。
江司令当副村长的秘书之类的职务,是个绝对的纯种男人,热血、臭脾气、激情和歌声,雄性正当年。我曾设想,做他的女人,只要拥有一对大容量的好耳朵和肥沃的子宫就足够了,但他偏偏很喜爱多情的女子,生就多情的民族,难怪走婚生生不息。
也有不一样的小年青人——哪都有这类人,他们看着很聪明,但成绩却随着年纪成反比,做他们的老师很牛比,只有少数的几个西方人可以和他们交成朋友,女性老师都靠边站,因为他们会说很下流的话,他们把头发染成黄色,根根被烫起,脱离了地心引力,向上竖起,江司令的弟弟叫“扎西”的,就是其中一个,学校最终让他们几个退学了,因为他们不能再往后坐了,再往后坐就要掉到校外的湖里去喂水草。离开了学校,扎西大部分的时间是到在到处乱逛和在网吧闲聊中度过,他说他交往了一个女朋友,是广东人,还很有钱,准备同爸妈旅游时来看他。他一直津津乐道这事。
有个叫“密密奴”的居住区旁边树林子里,如果不小心会被地上隐匿的针头一针扎上,扎上了最好去当地的卫生所做个细菌培养,有不少人被检查出感染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病症。江司令说,他弟弟之所以染上毒瘾,就是因为被针头扎了一下。扎西不断地吸毒,江司令会帮他从很远的地方带来白色的东西。他说他们以前连酱油都吃不到,现在却可以享受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我说那是毒。他说少吸点就行了,反正他吸不惯,他还是喜欢长长的竹筒烟。他们整个村子都不在乎这类事。
直到来了一批批的贩毒犯,来了一批批的公安。
直到我在公社的简易公告栏上看到我哥、西瓜头、肚皮和毛毛的头像。
我才知道我在湖边跟少数民族儿童玩泥巴的时候,我哥和毛毛正在玩与枪有关的“贸易”。他们从云南走私大批的日用商品、香烟和车辆,他们把生意搞得铺天盖地、风声水起。不过,话要说回来,那时候像他们这样搞贸易的人还不少,以至地方设立了专案组专门追捕和围歼,话又要说回来,他们能这样风风火火,也跟当地政府不无关系,官商勾结的贸易自古以来就畅通无阻。
这也是为什么毛毛总是深夜来访的原因。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已被当地民族同化,这不就是实际的走婚吗?
某年某月的某日,小简面色紧张地说:“外面传言说你屋子有一个男人会来?”
“走婚的。”
“你可别被钱和色迷惑了双眼。”
“这是我的事。”
“可他让扎西卖货,现在公安在调查扎西了,我那口子在搞环保调研时告诉我的,叫你千万小心,扎西还在局子里到如今也没放出来呢。”
我那时想的是,毛毛该不会又什么都不说,就离开我吧?
我匆匆跑去见扎西,他坐在派出所的地上,面露菜色,染黄的头发也不根根竖起了,都搭拉在头皮上,他一见到我,说的是:“我饿!”他说这里的公安不地道,二三天不给他饭吃,还打他,还让他不能睡觉。
我安慰他:“孩子,哪都一样。”毛毛对政府的叛逆也是这样慢慢积少成多的——很多人也是。我是自愿者,我不能对他说:“我代表政府来慰问你。”我永远只代表个人意志。我也不能写请愿书,让政府对在押犯落实点政策,至少一日三餐管饱饭。
我问:“江司令呢?”
“他不管我了,他说我满十八了,都可以睡姑娘分家了。”
“你哪里满十八了?明明是十六啊。”
“我们这里算虚的。”
“哦。还有这么算的。”
我问他是不是有个男人,看上去还蛮好看的男人会让你出货。他说是,他说“是”的时候一直观察我的反映,我轻声问他:“你们卖的是毒品吗?”
他脖子往后缩:“啊?不是啊,我只是帮他卖卫生纸,一筒一筒的,还有你们女人用的,呵呵。你们说的毒品哪需要去外面买,我们这里到处都是,他要,我送给他就是了。”
“你送了很多?”
“朋友嘛,无所谓的,不值几个钱,我们这里早不生产这个了,我家的自留地都被干部推掉了,现在都搞承包,政策让家家推了罂粟,种苞谷,后来啥也长不出,没事干,都是偶尔做点自已人吸,还不如带客到处玩,那还有钱赚。”
“难道公安打你不是为了这个吗?”
他更惊讶了:“不是啊,家家都有的。我是因为我偷光缆线了,我不该听他们的,剪一些旧的才看不出来,我剪的都是新的。”
“小心电死你。”
“是埋地下的。”
“你活该挨饿。”
“喂!你不理我吗?没人给我送饭。亲爱的老师。”
没办法,就为了这个称呼,我一连一周给他送亲手做的饭。
他没见到网上谈的那个女朋友,他因盗窃国家通信资产罪数额巨大被判了三年,比起他不时拿给朋友的毒品在黑市上的价格来说,那些钱根本就不是什么钱了。还好,他没见到那个女朋友,因为那是个大胖子,把两根细细的小辨子甩得摇来晃去。至少我不喜欢。
他们居然染指毒品,这非同小可,我想找毛毛大吵一架,可有个晚上来的却是肚皮和白皮肤的西瓜头,他们送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说毛毛被人打伤了,在医院里躺着。如果不严重,不至于他们俩亲自过来,他们已经是一大帮人马的头目。他们一个劲地说毛毛打伤了,我那时还在发呆,说实话,我一直在想自己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还没想明白,他们就走了。
再后来,我哥突然打来电话,说,毛毛快死了。快死了就不一样了,没想明白也要去。
我哭哭啼啼地去了医院,按我哥说的房号找,但是,那床上躺着的是个老头,呆呆地看着我,我问他:“你前头是不是住了一个男青年。”
“死了啊!死在我前头了。”
这就死了吗?我再问护士小姐,她们回答我:“没有这个人,从来没住进来过。”
于是,毛毛和他们又消失了。
是不是真死了,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的支边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又见到了肚皮,他偷偷给我带了不小的一笔钱,说是四人帮给的。我给肚皮炒了一桌子好菜,他告诉我,他们用赚来的10%的钱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一把钥匙一个人管理。以后钱多到花不完的时候,就在海外随便买个小岛,大家都带上心爱的女人,看看潮起潮落就过一天,像《美国往事》里的那样。
我问了他很多,他都让我别管。
肚皮那晚酒喝了很多,他似乎还有很多话想跟我说,但总也不开口。他说人生很多事,该替朋友想的就要多想想,就是这一生的朋友了,哪有什么来生。他翻来覆去地讲朋友和忠诚,爱情和道义。他说退一万步,也还会选择这条路,只要朋友让他走的,他义无反顾。他说到毛毛那次受重伤,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我终归有一次拿命还他。”他埋在手掌里,眼泪从里面渗出来。
“是枪伤吗?”我问他。
“这事,你别管。”
“他伤到哪里了。”
“这事,你别管,有人打理他。”
“什么都别让我管,你还来我这里做什么!!你滚出去。我不想见到你们!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你们离我最好远远的,别来烦我,别再给我钱,我不需要!我讨厌你们,你们根本就是渣碎!是疯子!是王八蛋!草你奶奶的……。”我把所有的气砸在肚皮的身上,把炒好的一盘盘的菜往地上摔,它们七零八落,在黑夜中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没收肚皮的钱,以后也再也不收。我跟肚皮说:累了,我要自己走,大家互不相干吧。
从此,我和我的四人帮彻底绝裂了。同时,我也即将完成我的支边生涯。其实,即使绝裂,我依然见到过他们,他们总是零星地穿梭在我身边,某个时刻甚至同期出现。在云南的这个小村子为自愿者返城开的一个篝火晚会上,他们四个人分别在四个方位,东、南、西、北,在欢笑歌舞的人群中摇摆和放纵,他们的尖叫和大声歌唱像是对我致意告别他们的示威。
再往后,渐渐没有了消息,没了消息,我便设想他们的人生,我还设想,把自己也全面搅动一下,谁都有毁灭的力量,这是人本性的恶在做怪。现在想想,青春时候的一无所有还蛮牛比的,现在连半点一无所有的勇气都没有,就怕被人看见天天就着咸菜下稀饭,谁要是被抖落一些陈年糗事,满世界抓狂。
——这样,其实不好。
有时女人尤其喜欢强调:没有爱了,就对什么也不爱。
——这样,也不好。
还有,男人总以为钱和地位最牛比……这个,我们要从长计议,《一无所有》的歌词里有:你爱我一无所有……。我草!这样下去,现实会告诉你——
——这样,更不好。
呵呵。
还有“精神”。在下,要谈谈,有人还在讥讽我的纸上人生,根本是他自己活得不够劲道,就像慢性便秘一样。人有时要相信精神生活,荼毒自己的灵魂,终有一天它会让你愰愰不可终日。以前遇到过一个女人,离过几次婚,带着孩子,还屡被骗财骗色,得了乳腺癌,割了,她挺着坏掉的胸脯跟我说上帝的坏话,说完依旧拉着收来的一车货走掉,嘴里念:来年就靠这车货……还有什么理由鄙薄精神。
有一年,我哥打电话来说,毛毛什么什么,后来,听明白了,说是自杀末遂,我那时候也一滴眼泪没有流,有个名词,叫“舍得”。舍得、舍不得,有时都要统统放下。想想我们在雪地里打滚,在农家院里拍摄,那时,我们一无所有,却是最幸福的时候。
后来,我再打我哥的电话……
——对不起,用户已欠费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