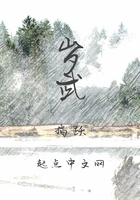莎莎心里清楚,韩强对她是动了真情的,所以就处处让着她。有次她曾问他:“我究竟在哪些方面优于南妮,让你离开她呢?”
他想了好半天,说:“你这话倒是把我难住了。我打个比方吧:有两个美女站在你的面前,让你评判谁更漂亮,你可能第一眼就已经确认了。但如果让你说出她究竟哪些地方比另外一个美女漂亮,你可能就有些为难了。其实漂亮只是个整体印象,再具体到每一个细微之处就很难判定了。你和南妮都是很优秀的女人,各自有着不同的动人之处。但每个人的审美观点和情趣都不一样,我和南妮之间都相互有不适应的地方,所以分手也是情理之中了。”
“你很会讲理由。这个逻辑今后会不会又运用到我们之间啊?”她说。
“你又将了我一军。我想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分开了,那肯定不是我的原因。”他信誓旦旦地说。
她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韩强现在对她简直就像个护花使者,关心的程度甚至让她有些生厌。其实,男子汉就应当有男子汉的风度,大可不必那么婆婆妈妈的。她由此想到了刚刚见过面的何野。他看起来要比韩强刻板,但也比韩强稳重。她早就听丁璇抱怨过,说他不懂得生活情调,不知道关心人。但南妮对他的溢美之词,却是发自肺腑,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了。
莎莎带着一种好奇心对南妮说:“何野他好像不大爱交际,挺稳重的。”
“汉语的辞汇就是丰富,换个词说,就是挺死板的。”南妮笑了说,“不过,他要谈起古代文学可是振振有词的。”
“也许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有的人在酒桌上侃大山,他可以滔滔不绝,可你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讲句话,他就颠三倒四了。”
“其实,这就是一个文化层次的问题,你不管他多么会‘做秀’。唯独这方面他做不了。”南妮说“我挺佩服何野才学的,同他谈天说地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嗬,咱们交往这么久,我还头一次听你讲出‘佩服’这两字呢。”莎莎笑着说。
“你就嫉妒去吧。”南妮也笑了,脸上溢出幸福的微笑。
飞机在下降着高度,空中小姐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
南妮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说:“我的手机号换了,在广州有事儿就给我打个电话。”
“谢谢。”莎莎感慨地说:“我们有好久没有电话联系过了。”
丁璇离开了何野,曾让秋婷从中看到了爱的希望。她充满希望地迈进了何野老师的家门,受到的除了何野的热情之外,还有玲玲的白眼。正当她充满希望时,南妮却闯入了何野的生活。她嫉妒南妮,认为是她夺走了她的爱情。
女孩子的梦是透明的,但也有迷离的时候。少女的浪漫,少女的天真,少女的羞涩,少女的幽怨,在秋婷的梦境中都曾经出现过。
梦是女孩子自由的精灵,是宇宙最任性的女神。
秋婷在情窦初绽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找到心中的白马王子。最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了,便情投意合,两心相知;成年后,便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老年了,便相濡以沫,相依相伴。可是这梦中的境界在现实中竟从来没有出现过。既无青梅竹马的意中人,又无两小无猜的男子汉。自然余下的梦想就更无从实现了。
何野就是在她极度失望中出现在她眼前的。
十八岁那年,她带着几分缺憾,把情感收藏起来,走进了省城这所高等学府。
起初,她便对这位教授古代文学的老师印象颇深。这位带几分书生意气的何野几乎每天都端着一只很大的磁化杯,挟着讲稿,踏着上课的铃声走上讲台。他当年27岁就成为了副教授,一副少年得志的样子。他的习惯动作是,先放下杯子和讲稿,用双手撑着讲台,环视一下教室,然后便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才开始讲课。
他渊博的学识和口若悬河的口才很快便让她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上高中时,那枯燥乏味的古文课曾讲得她昏昏欲睡,没有想到在他的口中,那古文课也变得妙趣横生了。惭惭她对何野老师生出了一种朦胧的感觉。每当他的课时,她会早早赶到阶梯教室抢一个前边的位子,虔诚地听讲。课后,她也时常向何野提出几个或很深奥,或很幼稚的问题,以其引起他的注意。
果然,何野开始注意她了,有次还问了她的名字。她兴奋极了,连踹带跳地跑回了宿舍。同寝的江苏女孩肖怡惊讶地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有男朋友了吧?”
“去你的。”秋婷挥手就是一拳,让她躲过了。她们围着宿舍地中央的桌子追打起来,直到肖怡主动告饶为止。那是一种初恋的感觉,让她既兴奋,又惶恐。何野毕竟已经结婚了。她一不小心爱上了他,无异于在进行一场前途未卜的爱情游戏。
“你疯了。”肖怡在得知此事后,大惊失色。她无论无何也理解不了秋婷的这种举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肖怡,你根本也不懂什么叫做爱。这是一种最美好的感情,它可以抛弃人世间所有的世俗和偏见,追求一种无怨无悔的幸福。”
“你没发烧吧。”肖怡用手摸了摸她的额头,说:“咱们班的男生那么多都对你有意思,难道就没一个值得你爱的?搞‘师生恋’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诚心告诉你,到此为止吧,现在还来得及。”
“你不要说了,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她倔强地说。
她恍然发现,她已经深深爱上何野了。她眼里的何野是那般的英气迷人,从他清癯的脸庞、眉宇的灵气和身型的挺拔中都能寻觅到女孩子所欣赏的气质。肖怡是她最要好的女友。她的忠告,秋婷也不是没考虑过。但是,她无法遏制爱的芳草在心田中疯长,她也无法放弃对何野的那份真挚的感情。她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度矛盾的心理中之中打发一个又一个日子。单相思的滋味对一个少女来说是一种精神的折磨。而何野似乎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他只是将她当成他的得意门生来加以关照。
在清冷的月光下,她一次又一次徘徊在何野所住的那座宿舍楼前。她想走进那间房子向他袒露积淤很久的心里话,但她又没有那个勇气。她害怕见到何野的妻子丁璇。尽管她已经风闻他们之间的婚姻出现了裂痕,但她还不想给人留下是她插足的印象。她寄希望于丁璇的主动退出。这是她“大三”上学期时的心态。
丁璇终于离开了何野。这让她从中看到了爱的希望。她充满希望地迈进了何野老师的家门,受到的除了何野的热情之外,还有玲玲的白眼。那天,何野和她谈了很多,可大都是围绕着古代文学的话题展开的。她很少插话,一脸虔诚地听着,可心里却早已是倒海翻江了。她趁着这个机会欣赏着她心仪已久的男人,不觉有种渴望亲近的冲动。
玲玲坐在一旁开始不耐烦了。她不时扑到父亲的怀里撒着娇,还用敌意的目光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女人。她幼小的心灵中对父亲身旁的女人似乎有种天生的抗体。她害怕将她的那份爱分散到别的女人身上。秋婷失望地离开了何野的家。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相见之时并不知晓埋下了忧伤的种子,分别的时候才发现那棵嫩芽已开始疯长。思恋是根,追求是叶,期待是杈,未来的爱情是否会开出鲜花?”
那天,她彻夜未眠,脑海里交替闪现着何野与女儿的影子。
“如果……一旦……我将如何面对这个聪明又任性的小女孩呢?”她有些不安地想。
她从小便失去了父爱,是母亲将她一手拉扯大的。妈妈曾指着几张发黄的照片,给她讲述了一个遥远的故事。父亲是她出生的那年离开她的。他死于一次意外的车祸。当时,他正在内蒙古的霍林河一带考古。那里新近发现了一个辽代的墓葬群,他在赶赴挖掘现场的途中与霍林河矿区的一辆载煤卡车相撞,当即身亡。母亲告诉她,父亲是个很有才华的考古工作者,足迹几乎踏遍了长城内外的广袤原野。他没有给女儿留下什么遗产,只留下了许多历史书籍和厚厚的几本考古日记,还有一张她满月时父亲抱她的照片。照片上的父亲很英俊,宽宽的额头,炯炯有神的眼睛,高挺的鼻梁和轮廓鲜明的下巴。他正慈爱地将她的头贴在脸上,她却傻傻地笑着。
儿时,她无数次缠着母亲要爸爸,母亲却总是哄她说爸爸出远门了。当她看到别的孩子在父亲的引领下逛公园,去郊游,她幼小的心灵就会感到忧伤,以至于有一次她竟脱口对街上一个陌生的叔叔喊了声爸爸。母亲流泪了,将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长大了,她方知道缺少父爱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让她失去了许多童年的快乐。她并不喜欢和同龄的男孩儿玩,却喜欢和父辈在一起。她渴望父爱,总希望依偎在他们的身旁。
她不清楚这是不是书上所讲的恋父情结。
走进大学校园,她对人生有了一个全新的感觉。她敬重那些满腹经纶的老教授,但也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一个年轻的教师何野。她觉得她已经长大了,应当从“恋父情结”中解脱出来,找一个大哥哥来爱她,呵护她。在他身上应当集父爱和情爱于一身,让她不但有安全感,还要有愉悦感。但是,她一次次地失望了。何野在她赤裸裸的柔情面前却显得很冷,像一块化不开的冰。每每遇到敏感的话题,他总会巧妙地绕了过去。但是,她一直也不愿放弃最后的努力。她相信她的魅力是一把万能的钥匙,足以打开他那把锈锁的。
前不久,她得知女作家南妮已经介入到他的生活之后,伤心地哭了。第二天,她在校园里拦住了刚刚讲完课,走出教学楼的他,直言不讳地寻问是否有此事。何野坦率地告诉她,这是真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质问道。
“哎,你这话问得好没道理。”他说。
“我就是要问!”她大声说,两滴泪珠滚出眼眶,沿着脸颊滑进嘴里,咸咸的,涩涩的。
“因为我爱她。”他直截了当地说。
“可她并不适合你。”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比她更关心你。”她抽泣地说。
“好啦,我现在不想和你理论。你看你哭哭涕涕的,别人看到会成什么样子。”他说着递给她一个手绢,匆忙走开了。
这情景让肖怡撞见了。她跑过来问秋婷是怎么回事?秋婷一五一十地向她倒着苦水。
“咳,我看这倒是件好事,省得你掉进情网里无法自拔。何野老师他人不错,可毕竟是离过婚的人,你若是嫁给他,我觉得还挺屈的呢。”
“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地爱他。”她泪眼涟涟地说。
“人家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肖怡摊开双手,无可奈何地说。
何野接到秋婷打来的电话时,正在电脑前赶写他的论着《论花间派词风》。这部专着是省社科院“十五规划”的重点科研立项,人家追得紧,让他下月前交稿送审,他这些日子紧赶慢赶总算快收尾了。谁知,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秋婷请他去白露餐厅吃饭。
“实在对不起啊,我现在很忙,脱不开身的。”他推辞说。
“您又在托辞。”她不高兴地说,“是不是挺烦我的?”
“秋婷,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是真的有事。”他解释说,“我在完成一部专着,出版社催得挺急的。”
“那也不至于连吃饭的空都挤不出来吧。”她依旧不相信的样子。
“你还请了谁?”
“还请了我自己。”她调皮地说。
“这不大合适吧,我看还免了吧。”他发现这个秋婷越来越难缠了。
“你放心,我不会死缠着你的。”她显然有些生气了,大声说。
“好,好,我去还不行吗?”他百般无奈地说。“定个时间吧。”
“今晚7点。”她现出如愿以偿地欣喜,清脆地说。
何野撂下电话,叹了口气,心说:“这个秋婷啊,我可真拿她没办法。”
对于秋婷的热情,他一直采取了“冷却法”的对策。他不愿意太直白地拒绝她。这样做太伤一个女孩子的自尊心了。他只想用时间来冲淡一切。等到毕业,她就会现实起来的。没想到她时值今日还是那般执着。这让他不得不考虑采用什么方法来遏制她的幻想了。
他决定利用今晚的时机和她摊牌,从而结束这一切,并重新开始各自的生活。
他准时来到了白露餐厅,秋婷已在门口守候多时了。她穿了件比雪还要洁白无瑕,比云还要活泼自在的连衣裙,乌亮的长发同样活泼,同样自在地飘逸在肩上。她甜甜地微笑着,说:“请到您,我真高兴。
“你啊,总爱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不知今天你摆得是哪门子鸿门宴。”
“何老师,古书读得太多了,总喜欢拿古人的眼光来审视当今的年轻人,此风断不可长。”她边说边将他引领到二楼的包间。
何野一踏进这扇门,便给里面的布局惊呆了。落地的玻璃窗垂挂着天鹅绒的帷幔,餐厅的一角摆放着全套的组合音响设备和背投式彩电,仿古式的餐桌和椅子都是楠木的,镌刻着精美的花纹,脚下铺的是深绿色的提花地毯。
“你怎么能选这样一个奢华的地方吃饭?你有这个经济实力吗?”
“何老师不必担心,几百块钱,我还是花得起的。”她粲然一笑,露出两个圆圆的的酒窝。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他说,“这个帐由我来结好了。”
“行啊,您还从来没请我吃过饭呢。”她大方方地说,“不过,这个帐我先替您记着,日后由我来定时间,定地点,到时我一定要狠狠宰上您一刀。”
“岂有此理。”他说,“这种城下之盟,我是不会干的。”
他们双双入座后,身着唐装的女服务生端来了一尊蜡烛,烛光跳跃着,在茶色的玻璃台面上映出了倒影。秋婷点了甜酒,荷叶鸡翅,北京烤鸭。
“这个秋婷又搞什么鬼名堂呢?”他见她在低声对女服务生说着什么,那女孩儿点点头退了出去,便忍不住想。
秋婷起身倒杯酒,递给何野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您能来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来,让我先敬您一杯。”
“慢,我想知道你指得是什么?”他没有端杯,露出不解的神色。
“这说明您对我了解得太少了。”她黯然伤神地说,“看来,您只能和淳朴的女孩儿做朋友,她知道怎么样去宽容您。”
“你的话让我越听越糊涂了。”
“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您今天来了。”她独自呷了一口酒,那宁静的黑色眸子蕴含着难以破解的心思。
“南妮她不会在意我请您吃饭吧?”她突如其来的话让何野有些吃惊。
他将已经夹起的鸡翅又放了下来说:“她刚刚去了广州,开一个女性文学方面的研讨会。”
“哦,是这样。”她若有所思地说。
何野从坐到餐桌上的那一刻起就在考虑用什么方式来打消秋婷的念头。既然她已经主动提到了南妮,他也就莫不如把话挑明了。他正欲开口,包房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请进。”秋婷大声说。
话音刚落,那个女服务生端着一盒生日蛋糕翩然而至。
“秋婷小姐,我代表我们餐厅老板祝您生日快乐。”她的嘴唇很小,话说得很甜。
何野怔住了,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可真傻,怎么就没猜到秋婷的用意呢?”他心里在自责,也很尴尬。
穿唐装的女服务生将生日蛋糕摆在桌中央,上面一层雪白的奶油,转圈已插上了二十一根五颜六色的小蜡烛。她划着了火柴,一支一支点燃了。
何野眼睁睁地看着那二十一朵黄色的火苗汇成了金灿灿的一片,照在雪白奶油上的红花和“生日快乐”几个火红的大字。
“许个愿吧。”女服务生微笑着望着秋婷。
她闭上眼睛,脸上充满了少女的恬淡、温柔和企盼。蓦然,她睁开了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张开那花瓣似的嘴唇,吹灭了那一根根的蜡烛。
“怎么,不想祝福我两句吗?”她笑盈盈地注视着他。
何野像是刚刚从梦境中醒来,她叫住了正欲离开的女服务生,说:“小姐,请你到附近的花店给我买上二十一朵红牡丹。”
“不,我要红玫瑰。”她大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