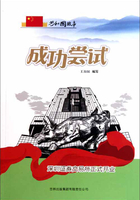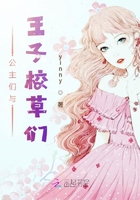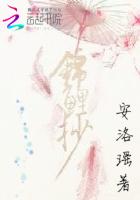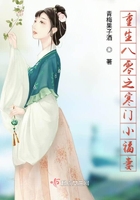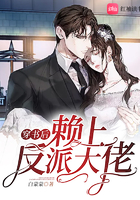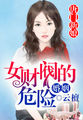如果只会清谈,只会拘泥章句,只会背诵师长的言论,你问他一句话,他回答你一百句,如果再问他说话的主旨,他就会张口结舌无所适从,这种博士卖驴的学问,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你们应当利用有效的时间,去广泛阅览那些有用的知识,并借此来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孔夫子说了:学也,禄在其中矣。
什么意思?好好学习的话,俸禄就在其中了!
第四,勤学的毅力。这是坚持下去,或者说是成功的关键。苏秦用锥子刺大腿防瞌睡,孙康借助雪地里的夜光读诗书,车胤用袋子收集萤火虫用来照明读书,这些故事家喻户晓。现在,我再给你们说一下朱詹苦学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义阳的朱詹,非常好学,但家境极为贫寒,有时接连数日都无米下锅,就经常吞吃用过的纸来充饥。严寒的冬天没有毡被御寒,只得抱着家里的狗睡觉。狗也很可怜啊,饿得两肚紧瘪,实在忍不住,就跑到别人家去偷东西吃,尽管朱詹大声呼唤,饿急的狗也不再回来,朱詹叫狗的声音,凄凄惨惨,让听到的邻居都极为悲伤。尽管朱詹如此的穷困潦倒,连最忠心的狗都弃他而去,可他仍然不改初衷,苦学不辍,最后终于成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学士,且官至镇南录参事,连孝元帝都非常敬重他。
第五,勤学的方法。会不会读书,还有方法问题,成功的人都是勤奋的,但勤奋的不一定都会成功,这其中就有方法问题。《尚书》上说的,只有喜爱提问的人,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礼经》上也说,独自学习而不与朋友共同商榷,便会孤陋寡闻,这都说到了一些方法问题。从我自身所积累的一些方法看,主要有以下两点:
共同切磋,相互启发。学海无涯,一不小心就会闹笑话。江南有一位权贵,读了误本的《蜀都赋》注释,书中把“蹲鸱”解释成“芋”,巧的是,这个“芋”又错写成“羊”,后来有人给他送羊肉,他竟回信说:“谢谢您惠赠的蹲鸱。”满朝官员对此都十分的惊骇,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典故,很久以后才找到出处,也知道是这么回事。试想一下,如果,这位权贵,问问人,切磋一下,就不会有这样的差错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列举不完,太多了,这都是不交流沟通引起的。
援引事例,切忌道听途说。一些士大夫,不肯读书学习,又怕别人把他看成是庸俗浅薄之人,就把一些耳闻之说拿来牵强附会,装饰门面。提起吃饭就说是糊口,谈到钱就说孔方,问所迁之处就讲成楚丘,谈论婚嫁就说是燕尔,提起姓王的人便都称“仲宣”,说到姓刘的人全称为“公干”。若有人问起这些典故的出处和意思,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了,用到言谈和文章中,常常是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
举个我亲身碰到的例子。我在益都的时候,有一天,天刚放晴,阳光格外明媚,我和几个人坐在一起聊天,忽然发现地上有许多个小亮点,就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东西?有一个蜀地的童仆弯腰看了看回答说:这是豆逼呀!大家听了都有些吃惊,不知道这个“豆逼”是什么东西。我让他取来看,原来竟是一颗小豆粒。
为此,我便问了许多蜀地人士,为什么把这个“粒”叫做“逼”,当时竟无人能解释清楚。我便告诉他们:《说文解字》中,这个“逼”字是“白”加下“匕”的“皂”,解释为“豆粒”,大家听了都很高兴,终于明白了这种称呼的原由。
上面这个例子不是说我多有水平,只是说,学问无处不在,但一定要和现实结合起来。
下面再结合自己的读书,说一个最新的研究心得。
《礼记》上有句话:“定犹豫,决嫌疑。”《离骚》中也有句“心犹豫而狐疑”,前代学者都没有人对这句话进行解释。《说文解字》上有“陇西人称小狗为犹”,考查《尸子》,上也有“身长五尺的狗叫做犹”。你们不是常见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吗?人带着狗一起走路,狗喜欢事先跑到前面等,等人等不到,又跑回来迎接,像这样跑来跑去,直至一天结束。这就是“豫”字解释为左右不定的缘故,因此把狗叫做“犹豫”。也有人根据《尔雅》中说的“犹长得像麂,善于攀爬树木”的说法,认为犹是某种野兽的名字,听到人的声音后,就预先爬到树木上,人离开再爬下来,像这样上上下下,所以称为犹豫。另外,狐狸生性多疑,总要听到河里面冰下没有流水声后,才敢在冰上过河。
总算弄清楚“犹豫”了!
总之,勤学体现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勤学是人的立身之本。不勤学,一辈子都不得安宁。
肆、“三易”原则做文章
说了勤学,下面我要给你们讲关于文章的作法了。
虽然刘勰《文心雕龙》已经给你们说了很多做文章的实践和理论,他的道理都十分正确,我这里只是补充或者强调。
我很欣赏沈约先生的观点:文章当遵从“三易”原则。第一是要选用易于被人接受和理解的典故;第二是使用容易认识的文字;第三则是便于诵读。按我的理解,用典让人感觉不出来,就仿佛是写作者从内心发出的言语,将最深奥最复杂的内容用最浅显最简单的说出来,那是真本事,要活化,不要泥古;容易认识的文字,那更好理解了,毕竟现在有文化的人不是很多,有许多人识字也有限,如果用一些生僻偏冷的文字,势必让人理解不了;至于诵读,那必须是朗朗上口的,在许多的场合,文章都可以诵读,一来活跃气氛,二来也能达到交流的目的。
文章千古事,因此,要全面理解这个如何作文章还是要下一些工夫的。
文章的本质,就是要表明兴致,抒发感情。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的周围,你们很快就会发现,有些人是偏离了这个原则的,他们往往将文章当成追逐名利的工具。有了这样的前提,会写文章的人,往往恃才自夸,忽视操守,他们甚至都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要有一个典故用得恰当,一句诗文写得清丽奇巧,就会神采飞扬,心气高傲,孤芳自赏,目中无人,甚至还雄视千载名人。
我看当世有些人,根本没有才思,却自称文章清丽华美,还装模作样开作品研讨会,并把这些拙劣的文章四处散布。最近我在并州,就见到一位这样的人士。
这个人喜欢写一些可笑的诗赋,人们都嘲弄他,假意称赞他的诗赋,这人于是信以为真,竟杀牛斟酒,大宴宾朋,希望通过结交名人来扩大自己的声誉。可是,此人的妻子心里很清楚,自己先生文章有几斤几两,哭着劝他不要这样张扬,自己印成集子,娱乐一下也就得了,干嘛要这样啊?此人却叹着气说:我的才华不被妻子承认,可是我真的是有才华啊!
上面这个例子告诉你们,学做文章,可以先和亲友商量一下,得到他们的评判,知道拿得出去,然后出手。千万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为旁人所取笑,如果自以为是,必定贻笑大方。
自古以来写文章的人不计其数,但是,能达到宏伟精美境界的,不过几十篇而已;只要符合文章的基本格式,辞意表达得较为贴切,就可以称为作家了,但要写出流芳百世的作品,几乎像要黄河澄清那样是不太可能的事了!
好文章的标准应该是这样的:以义理为核心脊梁骨,以气韵格调为筋骨,以用典合宜为皮肤,以华丽的辞藻为冠冕。这个标准和沈约的“三易”原则其实是不矛盾的,它更强调的是文章的内在,用典合宜,就会变成自己的东西,就如皮肤,那是自然天成,如果用了不合宜的典故,那就像人身上贴了一块不合适的狗皮膏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总之让人感觉是多余的。而现在许多文章,多追求华丽的辞藻,浮华艳丽,这就像一个畸形的人,头上戴了顶硕大的帽子,而且这顶帽子还五彩缤纷,和下面的脸、身材,完全不搭调,很像万圣节上游行的鬼怪,自己认为很帅,但很容易吓到人!
照以上标准,就如我前面说的,确实没有多少可以称得上好文章的。而且,虽然能写出好文章的人很少,但评判文章好坏的评论家却很多,此谓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王籍的《入耶若溪》诗中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人认为这两句诗无与伦比,没有人说不好。简文帝吟诵这两句诗后,也久久无法忘怀,孝元帝诵读品味,认为再无人能写出如此佳句,以至在《怀旧志》中,把这两句诗记载于《王籍传》中。可是,范阳人卢询祖却有异议,他说:这两句根本不能算诗,怎么说他有才华呢?《诗经》上有这样的句子:“萧萧马鸣,悠悠旆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