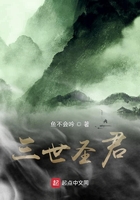壹
皓月当空,清景无限,整个皇宫沉浸在悠长的大梦中。
后宫,广庭深处突然出现一个小黑点。黑点缓慢却毫不犹豫地向着外面移动。月光透洒而下,原来是个八九岁的小孩子。
三皇子萧岿,梁帝最宠爱的儿子,又开始了梦一般的游走。
他身后,小心地跟随着一大批宫人内侍,他的母亲蓉妃也在其中。
萧岿走过了几个庭院,似乎走得累了,便停了下来。
他坐在石阶上,抬头仰望着星空。所有的人全都屏声静气地看着他。
良久,萧岿似乎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乌亮的眼睛眨了眨,突然开口道:“你们跟着我干吗?”
众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蓉妃明白他们受了儿子的愚弄,生气道:“岿儿,你搅得宫里好不安宁!待天亮母妃禀告你父皇去,让老师好好管教你!”
萧岿轻笑一声,满不在乎地应答:“父皇才不会呢。沈不遇管教不严,我让父皇撤了他。”
蓉妃愣住,一时无言以对,见儿子拍拍屁股想走,连忙哄他:“乖,回去好好睡,别再玩什么把戏吓唬人了。”
说完,她伸手摸上儿子的面颊。萧岿却不经意似的侧头避过,甩起睡袍袖子跑了。
大群宫人内侍紧随而去。
夜色浓重,微风中沙沙的脚步声远去。树影婆娑摇曳,映着蓉妃婀娜的身姿。她站在原地,长久凝望儿子寝宫的方向。
困意席卷而来,她才缓缓走回自己的雯荇殿,一路心中忖道:“这孩子,这段日子,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
一大早,梁帝传话蓉妃御书房。
“听说岿儿昨晚梦游了?”他不满地问,“你当母妃的,怎么可以任由他半夜吹风?冻坏了怎么办?”
蓉妃惊骇,垂下头跪地不起。
梁帝看不到蓉妃眼里的委屈,看她凄楚不胜状,又有点不忍,不觉叹道:“起来吧。岿儿大了,不喜欢沈爱卿继续当老师,那就随便他。沈爱卿政事繁忙,朕也想要他在朝中多做事,干脆去掉这个师职也好。”
蓉妃垂下眼帘,婉转说道:“皇上所言极是。不过岿儿不喜拘束,爱捣乱,一旦无人管教,臣妾怕他做错事。”
“这个不用担心,岿儿从小聪明过人。”提起宝贝儿子,梁帝萧詧脸上露出笑容,“朕今早议事,叫岿儿多睡会儿,不用请安了。”
蓉妃唯唯而退。
回到雯荇宫,蓉妃望着殿外的玉荷池出神。镂花香炉里燃着瑞脑香,香气袅袅纠缠升腾。
不久,她听到外面宫女的声音。紧接着,珍珠门帘哗哗作响。
萧岿一个人打了帘子进来,请了安,站起身就想走。
“你站住!”蓉妃猛地喝住他。
她生性温婉,待人说话向来轻柔,这一喝却把所有的人都吓住了。萧岿不情不愿地站着不动。
蓉妃近到萧岿身边,垂眼看他。儿子又长高了,却黑着脸不理人。她不禁低声幽怨道:“小祖宗,你想害死亲娘就直说!小时候你乖巧懂事,越长大越顽皮,搅得宫里天翻地覆的。多少只眼睛在盯着咱娘儿俩,巴不得雯荇宫出点事!一早母妃遭你父皇叱责,长此下去,你教母妃往哪儿待?”
说到这里,她泪眼盈盈,差点呜咽出声。
萧岿只顾低头看脚,不吭声。蓉妃猜不透儿子的心思,以为他又要顽劣逃开,心中悲悯翻涌。冷不丁地,萧岿抬起头说道:“我讨厌沈不遇,你让他走!”
蓉妃暗地里一个激灵,忙斥道:“沈大人当了你三年老师,你一向懂事好学,怎越来越没规矩?这话要是让外人听到,少不了被人猜忌。”看儿子不以为然的样子,她心生怒意道,“好好,你父皇已经撤了他的师职,遂了你的愿。”
“真的?”萧岿眨眼间恢复了活泼相。
蓉妃无奈地叹息:“真的。”
“那我不惹事就是了。”
萧岿唇线一抿,一丝似有似无的得意从秀气的眉角处扬起,人嗖的一下跑出内殿,珍珠帘子又是一阵哗哗作响。
蓉妃站在花窗前,殿外照例静悄悄的,只听到儿子轻快的脚步声。他的身影在晨曦的掩映下,像个跳动的精灵,眨眼间就消失了。
“今日定是一个明媚的晴日。”
蓉妃无波的脸上,平添了少许生气。可想起儿子留下的话,她的眼光又暗淡了下来。
在漫长的宫廷生涯中,她总是寂寞地打发日子。初进宫时,她承蒙梁帝眷宠,就在这里辟了玉荷池。萧詧爱牡丹,却也学《郑风》笑曰:“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赐名“蓉”。如今美景依旧,爱莲之人难见。她独守着这片荷池,满池荷花只落得个“食莲驻颜轻身,固精气,乌顺发”之用了。
蓉妃轻轻叹气,浅抿一口手中的碧螺春,两耳仔细地聆听外面的动静。
不久,守在外殿的宫女进来禀报道:“娘娘,沈大人求见。”
蓉妃一如既往的端坐模样,微一颔首,侍女便打了帘子,宰相沈不遇一身朝服走了进来。
沈不遇就要行跪礼,蓉妃见殿内已无他人,急忙上前拦了。沈不遇就势起身,轻说:“臣已见过皇上。”
蓉妃怔然地凝视沈不遇,随即苦笑道:“岿儿少不懂事,总是任着性子来,他父皇又宠他。”
“娘娘切勿担心,这是好事。”
“何以见得?”
沈不遇略微思忖,反而安慰蓉妃道:“定国公死后,穆氏势力不弱反强。究其原因,是其党羽早已遍布朝野。而萧韶既是皇后所生,又是大皇子,民间看来这太子之位非萧韶莫属。而皇上为何迟迟不立太子?他的心在三皇子那头呢!再说,西魏久不退兵,国家内忧外患,正是皇上重用微臣之时,这师职不当也罢。”
“表哥性情豁达,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宫里多娇娥,想我早晚会成失宠之人,岿儿的前途就交给你了。”蓉妃又悲又喜道。
“这是自然。沈家也就娘娘这门皇亲,微臣定要誓死护佑。只怪微臣教诲过严,三殿下向来不羁,怕了臣、畏了臣,也是人之常情。等他成人,自然明白微臣用心良苦,对母妃也不会大不敬了。”
蓉妃释然,连连颔首道:“怪我纵容过度。这孩子,是我的命啊。”
“也是皇上的命。”沈不遇微笑了。
后宫不宜久留,沈不遇告退。蓉妃一直送他到殿外。待人去鸟噤,她还久久未回殿,一身华服拖了一地阳光。
沈不遇出雯荇宫,由宫人在前面引路,走在绵长的甬道上。
他低着头想心事,步伐缓慢从容,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沉重。然而这样幽静的地方好似起了大风,头上的繁枝茂叶浪头一样地拍打。沈不遇回神,仰头看见几名宫人满脸的惊惧,没等他反应过来,当空掉落一个黑糊糊的麻雀窝,不偏不倚砸在他的头上。
朱红墙垣上爆发出孩子的笑声。
沈不遇顾不得头上的污秽,拐过月洞门,但见两个小身影窜下墙垣,飞一般跑了。
为首的正是萧岿。四皇子萧灏跟在后面,长袍差点绊倒了他。萧岿跑得从容不慌张,回头还看了沈不遇一眼,示威性地扬了扬眉。
沈不遇站在那里干生气,又无可奈何。众宫人赶紧上来帮宰相大人掸灰尘、去污秽,好容易收拾干净了。
沈不遇整了整衣冠,继续走路。一路上他心里在骂:“小子,我会灭了你的戾气,早晚你得乖乖听我的!”
这天,梁帝设宫宴为浣邑侯郑渭接风洗尘。
宴席开在白日。梁帝信任的几名朝堂重臣包括沈不遇陪宴。郑渭还携了家眷,加上梁帝的两个皇子,整个宫宴看上去只是个家宴,这样能避开西魏的耳目。梁帝对驻防已久的西魏兵心存忧虑,尽管西魏对他有所松懈,但他做事依然小心谨慎。
皇后并未到场。蓉妃因是三皇子萧岿的母亲,又跟沈不遇有亲缘关系,自然陪在梁帝身边。这天她一身严谨的碧色宫服,只垂眉端坐,手中宫扇轻摇。
梁帝举杯与众人共饮,一时觥筹交错。酒过三巡,梁帝的目光转移到萧岿身上,见他闷闷不乐的样子,便叫他,“岿儿。”
萧岿对着案上珍馐毫无胃口,思想仿佛还在游离,旁边的萧灏偷偷用手肘捅了他一下。萧岿惊醒,起身,将手中的酒盏高举过头,朝梁帝朗声道:“父皇,孩儿啥时替父皇杀敌立功?”
满庭大笑,钦佩的、折服的、赞赏的目光尽数聚集在萧岿身上。萧詧自是乐不可支,说:“你们看看,岿儿越来越像寡人少年的时候!”
“连说话的语气也跟皇上如出一辙。”
“三殿下忧国忧民,真是少年雄才!”
满堂附和声连连,梁帝笑得更欢,蓉妃心中窃喜。唯有萧岿以为,自己一句豪言发自肺腑,却被大人当做小孩子天真的稚语,反而越发沉闷。
他并未发现,郑渭旁边有个小女孩,此时正用晶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梁帝见萧岿默然不语,便大是感叹道:“国有积难,朕自知并非雄主,需与诸位爱卿同心方能聚合国力,补朕之弱。君弱三代,此国便要衰微了!”
众人停止喧笑,脸上凝了沉重。便在此时,郑渭站起身拱手道:“微臣为官十年,蒙皇上恩典受封浣邑侯,只知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君。皇上,臣愿为大定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沈不遇等人纷纷出列,匍匐在地,齐声道:“臣等齐心报国,振我大定。吾皇万岁万万岁!”
萧詧哈哈大笑,心中积郁顿时消散,酣畅淋漓的笑声在殿内激荡。
“诸爱卿平身!朕心甚慰。诸位都是朕的爱将重臣,只要君臣同心,合力治国,大定王朝根基定会固若金汤!”
君臣再度举杯共饮,沈不遇将酒盏端到郑渭面前,半开玩笑道:“半年不见,浣邑侯言谈功夫见长啊!”
郑渭咕咚咚将酒饮干,搁下碗,慨然一笑:“小弟粗人武夫,自是没有不遇兄那般能说会道。”
两人心照不宣地笑起来。
萧詧将四皇子萧灏唤到面前,对郑渭说道:“可惜郑美人过世得早,灏儿自打出生便没了娘,可怜啊!他虽不及岿儿顽皮,却斯文、懂事。你当舅舅的膝下无子,又向来疼爱灏儿,这样吧,将灏儿过继给你,同享天伦之乐,对郑美人也好有个交代。”
郑渭喜出望外,跪地谢恩。萧灏也拜过舅舅。满殿一片恭贺之声。
萧詧满面红光,大笑正酣,却突然望着郑渭身边的小女孩睖睁了:“这是—”
郑渭禀道:“微臣侄女。今日宫宴,便将她带来了。懿真,快来拜见皇上。”
懿真方才还瞅着萧岿,这会儿盈盈一拜,小嘴甜甜地说了句:“皇上万寿无疆”。
萧詧乐了,呵呵笑道:“朕就这几个皇儿,如若与诸爱卿结为儿女亲家,岂非更好?虽说是十年后的事,光阴荏苒,到时亲事大成也!”
闻听此言,蓉妃与沈不遇不约而同地对望了一眼。
沈不遇暗中使了个眼色。
蓉妃会意,依然浅笑盈盈。
午后的皇宫
沈不遇独自一人走着。周围莺啼燕啭,一派明媚。这样的景致丝毫勾不起他的兴趣,回味宫宴上梁帝的话,他心里更是一股焦灼燎了上来。
蓉妃的步辇出现在柳荫处。沈不遇恭立在道旁,直到步辇缓缓落在前面。
寂静中,蓉妃的裙裾光影般迤逦。她与沈不遇保持一段距离,装作无事般轻摇宫扇,缓缓道:“今日好事都让浣邑侯占尽了。”
“皇上惜才,浣邑一带地处边境,需郑大人这样的悍将严守把关。”沈不遇回道。
那声音淡然,仿佛这只是件正常不过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蓉妃听见这话,惊讶地微张开嘴巴,查看周围,终于忍耐不住道:“不知皇上心里到底想什么,看他对郑大人的侄女赞不绝口,莫非想让她当皇子妃不成?”
沈不遇沉稳道:“娘娘莫急,那也许是皇上的玩笑话。再说,他们都还是小孩子。”
“别人的事我管不了,可是岿儿是我的孩子,若是皇上看中郑家侄女当三皇子妃,浣邑侯岂不更加不可一世?表哥,你要想想办法。”
“知道了。”
沈不遇低声回道,眼里浮起一丝难以解读的恍惚。他躬身想退,蓉妃及时叫住了他。
“表哥,你已辞了师职,以后见面……就少了。”
“这样也好。三殿下近来对微臣……”
“他还是个孩子,喜欢意气用事,孰是孰非分辨不清。表哥多保重。”
沈不遇仍是低低垂着头,踌躇了少许,道:“娘娘保重。”
他抽身而退,刚抬起头,却见柳荫处闪过一道人影。那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俊秀的脸上透着冷峭。只一个跳跃,他又跑到湖石假山那边去了,那身玉色锦袍一点一点地抖着。
又是萧岿。
沈不遇冒了一头冷汗。他听到蓉妃在叫着“岿儿”,便赶紧加快步子离开了。
回到宰相府,沈不遇的两位夫人出来迎接他。
沈不遇为官多年,以清正廉明、恪尽职守在朝中获得好口碑。家里就两位夫人,再未纳妾。沈不遇早年师从二夫人柳茹兰的父亲,恩师见他敦厚又有才气,便举荐给当时还是岳阳王的萧詧,并将女儿许配给他。萧詧称帝后,沈不遇升擢至相位,一路顺风顺水。
“去把家里的姑娘叫来。”沈不遇示意大房黎萍华,自己徒步进了柳茹兰的院子。
柳茹兰叫丫鬟呈上新茶给老爷,沈不遇只轻轻一抿,就放在桌上。柳茹兰看在眼里,笑意浅浅却温柔:“老爷莫非有心事?”
沈不遇半倚在摇椅上,荡了几下,才长叹道:“人事莫测啊!倘若椅脚不活络,人坐上去便会翻跟斗。沈家就指望三皇子这根脉络,没想到这小子一点也不待见我。”
“哦……”柳茹兰似有明白,笑说,“跟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好生气的?三殿下从小长得粉雕玉琢似的,谁见了谁喜欢。加上皇上宠溺他,自然有点乖张跋扈了。多亏这样的个性,宫里谁敢惹他?连大皇子也让他三分。三殿下是蓉妃亲生的,蓉妃又是沈家人,虽说是远房表亲,可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这样的话语极为受用,沈不遇也忍不住带了淡淡的笑意。
相府唯一的两个千金是大房夫人所生,都十岁左右年纪。她们由丫鬟领着进来,未待行跪拜之礼,沈不遇便一挥袖,道:“免了吧,都站好了。”
午后的阳光透过纱窗落在两个千金的脸上,只是片刻工夫,沈不遇的神情就显出阴云似的黯然。他的眉端微微一蹙,厌烦似的挥手让她们离开。
柳茹兰不解地望着老爷的举动,却不吭声。
愣坐了半晌,沈不遇定了定神,方起身去书房。
柳茹兰适时地给老爷披上薄长衫。沈不遇转眼,淡淡道:“明日我去孟俣县。”
“老爷有公事?妾身这就去准备。”柳茹兰想起什么,又笑道,“咱家奶娘也是孟俣县人,这一晃几年,也不知道过得怎样?”
沈不遇只是沉沉地“哦”了一声。
孟俣县
六岁的休休趴在长满青藤的土墙上,旁边同样趴着的是倪秀娥的两个女儿。三女儿站在墙边,双肩被她们的脚顶着,已经吃不消了,嘴里不断地叫嚷:“快点了!好了没有?”
大姐低头“嘘”了一声,呵斥小妹:“别嚷嚷,小心被先生听见!”
私塾里,捧着书本的天际听到墙上有动静,侧脸看过来,朝休休做了个鬼脸。休休扑哧笑出声。尚在晃头晃脑念文的先生发现异样,立刻举着教鞭跑出来驱赶。
“快跑!”
三人慌乱地滑下墙,倪秀娥的三女儿始料未及,一屁股坐在地上。只听“哎哟”一声,老二的衣裙不慎被青藤勾住,摔了个四脚朝天。几人连忙扶起她,狼狈不堪地跑回家。
倪秀娥正站在自家的大门口紧张地东张西望,看到二女儿被搀扶着回来,便生气地骂道:“四宝上学,你们凑什么热闹?看看,把脚扭伤了不是?”回头用怪异的目光瞥了休休一眼,叮嘱道,“休休你就在这儿待着,哪儿都不要去。”
回到屋内,倪秀娥查看完女儿的伤势,待她回过头,休休已不见了。她心里一紧,急忙奔出家门,看见休休的小身影已经在弄堂深处。
她张口想喊,不知怎的,还是生生闭住了嘴。
休休想到父亲留下的活筋骨络散药膏,飞快地往家赶。穿过弄堂跑过一段石板路,她的家就在眼前。
冷清的道口肃然站着两位穿青色衣袍的男人,平时那里是鲜有外人走动的。大概是休休年幼的缘故,休休过去时,两人面无表情地睥睨她一下,并没有上前阻拦她。陶家大门半掩着,瘦小的休休一闪就进去了。
院子里寂寥无人,想必母亲曹桂枝在楼上打瞌睡。休休不敢惊动她,灵猫般溜上了楼梯。
曹桂枝的房门向来紧闭,休休轻轻地走进父亲的房间,轻轻地拿起放在床头的药瓶,一切都是悄无声息的。正要下楼,曹桂枝的房间里传来说话声,是男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