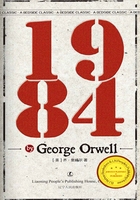我扭过头来,用双手捂住眼睛,不敢看。发桥随着棍子打在屁股上的响声,发出痛苦的**。我的心像被刀缴,真想求他们放了发桥,又怕弄巧成掘,只好偷偷地哭泣。这时,人群一阵骚动,一个耳熟的声音传了过来:“住手!住手!不要打了!”我立即抬起头,童锐走了进来。他一把夺下大桥二叔手中的棍子,斥道:“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大桥二叔说:“童警官,这是我们的家务事,请您不要插手。”几个老年村民也附和着,要求童锐离开这里。童锐大声叫嚣:“什么家务事?你们这是滥用私刑!我今天就站在这里,看谁再敢施私刑!”几个老年村民纷纷指责童锐:“你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
就在村民与童锐对峙的时候,村里的陈主任站了出来。他要求村民冷静,说现在是新社会改革开放的年代,干什么事情都要讲法,无法就无天,过去的老规矩也要接受法律的领导;陈发桥干了什么犯法的坏事,要由警察处理,警察就代表法律,警察说他有罪他就有罪,警察说他无罪他就无罪;如果不通过警察私下处罚陈发桥,就犯了法,就要坐牢。陈主任走到大桥二叔跟前问:“老哥,你就不怕坐牢?”最后,大家听了陈主任的话,按照童锐的意思把发桥给放了。
这次发桥是不幸中的万幸,碰巧童锐到陈家寨协助镇税务所征收村民去年欠缴的农业税。否则,他很可能被打残,至少会受更多的皮肉之苦。因为按照陈家寨的族规,胳膊肘往外拐的人,轻则挨族人棍棒,重则被逐出村寨,而族内通奸,最高可以被处死。虽然他们没有抓到我与发桥暗通的证据,但是他们猜测得到。都处在性强欲旺的年纪,孤男寡女经常在一起,弄出一点事情来也不是没有的事。再说,如果没有那事,发桥会甘愿冒风险帮我逃跑?村里人怕童锐,所以不得不给童锐面子。也是由于童锐的缘故,村民在处置了发桥后,只是斥训了我一顿,并没有对我动武。
自此以后,发桥就从村寨消失了。有人说他被县教育局调到离陈家寨很远很远的学校教书去了,也有人说他跟老婆一起到南方打工去了。我不知道发桥伤得怎样,他妻子知道了这事后如何对他?我一直挂念着发桥。
当山沟里最后一片积雪消融之后,杜鹃花便开了。起初像是山间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火苗,接着便燃烧成了漫山遍野的火海,远远望去,如同镶在天边的晚霞。可惜,我不能到山上去近距离一睹杜鹃花的芳容,嗅一嗅春天的气息。现在,我像被囚禁的逃犯,只能在村周围放放风。发桥没有了消息,童锐不知能否指望……难道我真的要像翠一样,在这穷山沟过一辈子?我的信心开始丧失,精神也逐渐走向崩溃。我好想回到以前,和同学们在一起,无优无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大雁塔、兵马俑、华山……甚至洛阳、北京……现在,这一切似乎成了梦。我甚至想,谁要是能够救我出去,我就嫁给他。
一天,我正在屋里洗衣服,大桥妈在家陪我。陈主任的儿子过来要我到他家去一趟,说是童警官来村里了,有事要问我。童锐是陈家寨的户警,经常找村民问这问那,而且我也报了案,找我去问话非常正常。我揩干手,站起来就跟陈主任的儿子走。大桥妈不放心,就陪我去陈主任家。
童锐让所有人都到外面回避,然后闩上门,面对我露出一丝淫笑。我警觉地问:“你干吗闩门?”
“为了安全。”童锐笑吟吟地向我靠近。
“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想支开话题。
“想你呗。”童锐嬉皮笑脸。
“你是人民警察,要注意影响和形象。”我严肃地斥他。
“人民警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啊。”童锐过来牵我的手。
“如果没有正经事,我就走了。”其实我本打算问一下,我报案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有人来解救我?见他咄咄逼人,对我非礼,我缩回手,欲开门出去。
“如果你依了我,我马上带你离开这里。”童锐从身后拦腰抱住我。
我反抗,但不彻底,更有些犹豫。童锐抱着我走进房里,发狂地吻我。然而,迟疑片刻后,我突然清醒过来,拼命地推开童锐,跑出房间。童锐恶狠狠地说:“不识抬举的东西,你跟我走着瞧。”
我逃了出来。在外面“回避”的人,见我脸色不好,就问我是不是被姓童的欺负了。童锐紧跟出来,语无伦次地大嚷大叫:“你们不要瞎猜疑!谁敢在光天化日下欺负妇女?我是警察,是保护妇女的,是保护群众的。你们知不知道?我在屋里向苏姑娘问话,是执行公务!我在办案!”
大家慑于童锐的淫威,同时也想象得见,我与童锐在屋里呆的时间很短,即使童锐起了淫心,也不可能得逞,所以都没有与童锐过不去,进一步细究此事。
通过这一次,我完全认清了童锐的虚伪和奸淫本性,再也不对他抱有希望。报警这条路行不通了,反而让我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脱身的对策。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走出山村,还要寄希望于村民。事实上,现在,除了村民外,我没有任何依靠。我必须作长远计,融进山村,取得村民的信任和理解。然而,要融进山村也并非易事。首先大桥爸妈就都我不放心,无论我怎么说,怎么保证不再逃,他们就是不肯让我到地里干活;其次,我与村民套近乎,他们表面很热情,但内心却对我有戒备。没有办法,我只好从与孩子们搞好关系开始。
山里的孩子,懂事早,自立能力强,他们六岁就能放牛,七岁就会做饭,八、九就可以下地干活,但是文化知识缺乏,一些孩子快十岁了还未上学,不知道安徒生和米老鼠是什么,许多孩子从没有走出过山沟。我看见有孩子聚在一起玩耍,就过去试着给他们讲故事。讲《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灰姑娘》、《孙悟空》……起初,他们都怯生生地远远站着听,慢慢地他们能够跟着故事情节发出会意的笑声,后来有些孩子还问一些问题,最后他们一没有事就跑来赖着我讲故事。开始,听故事的都是没有上学的小孩子,后来十六、七岁的大孩子也跑过来听。渐渐地,孩子们都跟我混熟了。他们原先都叫我大苕媳妇,很快都改口喊我陈姐姐,我喜欢他们这样喊,觉得自己已经和他们打成一片了。
孩子们的求知欲望特别强,除了听故事外,有时候还问一些别的事情。比如,有孩子问:“陈姐姐,你是从山外来的吗?山外是什么样子的?”我告诉他们:“山外有大海,有平原,有沙漠,有草原,还有比这里更高、更大的山。”我给他们讲大海里的鲨鱼、沙漠中的古城堡、草原上的蒙古包……他们一个个都张着嘴,听得出神。有的孩子还问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如数学题怎么解,汉语拼音怎么读等等。对孩子们的每一个问题,我都尽量予以解答。
有一个叫石头的男孩,十分调皮,由于家里交不起学费,十一岁还没有上学。他特别喜欢听故事,每每听我讲故事,都凑到我跟前,听得眼睛都忘了眨。别的孩子要是问一些学习问题,他就瞪白眼,老大不高兴。有一次,我问他想不想上学读书,他眼眶忽然湿润了,一个人默默走到一边呆呆地站着。我走过去抚摩着他的头问:“跟姐姐学认字好不好?”他感激地望着我连连点头。翠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莲子听说我要教石头认字,就跑回去拿来了她读一年级的课本给石头。从此,石头只要一有空,就跑来跟我学认字。
当我教石头认字的时候,经常有四、五个没有上学的六至十岁的孩子也跟着学。其中有大桥二叔的孙女娜娜,村北头的两个男孩小五和胜军,大桥邻居家的小女孩慧英。我们围在一起,或蹬着,或扎个草把坐着,以地球为黑板,用树棍或瓦片作粉笔,认汉字,学数学,也“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一天,我照例来到我们学习的“教室”——大桥家门口的打谷场上,等着石头他们。可左等右等,一个孩子也没有来。我不知道孩子们为什么未来,就跑到邻居慧英家去问慧英。可慧英也不在家,她奶奶说,她一早就跟石头几个孩子出去了。我决定到石头家去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会不会出什么事。走过两栋房子,拐个弯,我就看到石头他们正抬着什么东西走过来。七岁的胜军用两只手扶着肩膀上的木棍,佝偻着腰,敞着衣服,十分吃力地摇摇晃晃地走在前面,石头走在后面,其他孩子就在两旁扶着抬的东西。他们一边走,一边喊着号子。我赶紧过去帮他们。走近时,才发现他们抬的是一块石板。我接过胜军肩膀上的木棍,用两手托着,感到十分沉重,边走边问石头他们:“你们把石板抬到那里去?做什么用?”娜娜抢先答道:“石头哥说,把石板放在打谷场当黑板。”
娜娜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我仔细的看了一遍那块石板。它平整,光亮,颜色青中泛绿,简直是一块天然的黑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鼻子酸酸的,想哭。我问孩子们:“这石板是从哪里弄来的?”孩子们都你看我,我看你,似乎不愿回答。最后娜娜说:“是石头哥捡来的。”我抬着石板没走几步,就感到有些吃力,胜军大概看出来了,马上过来接我手中的木棍:“陈姐姐,让我抬。”我将沉重的木棍放回胜军的肩膀,扭过头去,眼泪潸潸流下。
石头他们将“黑板”斜放在打谷场旁的一面墙上,慧英从口袋里掏出几把白色石块放在“黑板”旁,孩子们面向“黑板”盘腿坐在地上。我用颤抖的手拿起一块洁白的石子,在“黑板”上唰唰地写下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教孩子们认熟这些字后,我让孩子们上“黑板”练习。胜军写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后,就问我:“陈姐姐,sheng字怎么写?”我问他:“什么sheng?是胜利的‘胜’,还是茂盛的‘盛’?”胜军说:“就是sheng军的sheng。”胜军不识字,不知道胜利的“胜”与茂盛的“盛”有什么不同,也不知道自己名字的sheng到底是什么sheng。我就在“黑板”上写下胜利的“胜”和军人的“军”。刚写完“胜军”的名字,就听见有人骂骂咧咧朝我们这边走来。原来是村北头的鳏夫陈憨子。孩子们见了陈憨子都猛地站起来,纷纷四散跑开。陈憨子冲到我跟前,抓住我的衣服大喊大叫:“你这个贱人,不教孩子好,尽教他们偷东西。走,到陈主任那里评理。”我感到莫名其妙,本能地挣扎着:“你要干吗?放开我,放开我。”陈憨子硬不松手,拽着我往陈主任家走。刚好有几个村民经过这里,纷纷过来劝解。陈憨子不依不饶,非要到陈主任那里讨个公道。正在这时,陈主任过来了。他叫陈憨子放开我,说有话好好说。陈憨子激动地指着墙边的“黑板”告诉陈主任,是我教唆孩子们偷了他家的石板。石头钻到陈主任跟前红着脸小声说:“是我们自己拿的,陈姐姐不知道。”陈主任问:“你们拿他的石板做什么?”石头吞吞吐吐地说:“我,我们想用石板做‘黑板’,让陈姐姐教我们认字。”陈主任看了看靠在墙边的“黑板”,对陈憨子说:“我说憨子,不就一块石板,孩子们要拿就给他们,让他们认几个字,也是积阴德,下辈子也好讨个媳妇。”陈憨子很不情愿地说:“给他们了,我用什么做饭桌?”陈主任说:“行了,把我家的旧桌子赔给你,可以了吧。”
乡里的孩子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样嘴巴甜,他们尊重或者喜欢一个人从不挂在嘴边,甚至见了他尊重或者喜欢的人也不问候一句,但是他们待人非常真诚,会用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情感。我只是为孩子们讲了几个故事,教他们认认字,他们就把我当成“恩师”。经常主动帮我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譬如我凉衣服时,孩子们就会跑过来,用水打湿自己的手揩干净绳子上的灰尘。有一次,娜娜问我,山寨里有没有我喜欢的东西,我说我喜欢山里的杜鹃花,可惜现在杜鹃花已经凋谢了,见不到了。第二天中午,石头、胜军和娜娜就每人抱了一大抱粉红色的杜鹃花送给我。看到这么多鲜艳、悦目的杜鹃花,我又惊又喜,山上的杜鹃花好像早已谢了,怎么还有杜鹃花?我问他们:“这些花是从那里弄来的?”娜娜说,在山上的一个洞口采的。山很陡,很难爬,他们一大早就去了,采了好多,路上拿不了,丢了一些。
我抽出一支杜鹃花,放在鼻前,眯着眼睛轻轻地呼吸,顿觉一股清香沁入心脾。孩子们见我对杜鹃花如此痴迷,爱不释手,都开心地笑了。我睁开眼睛,望着孩子们满脸的笑容,高兴地哼起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唱着唱着,无意间,我发现胜军的脸颊上有几道透着血丝的红杠杠,就关切地问他:“胜军,你脸上是怎么弄的?”胜军用手摸着脸上的红杠杠,面容羞涩地低着头,不说话。石头说:“是刺树划的。”娜娜补充道:“石头哥叫他不要过去,他非要过去不可。”从娜娜不连贯的讲述中我了解到,原来有一棵非常绚丽的杜鹃花长在一排刺树后面,胜军为了采到它,硬是钻了进去,结果被刺树划伤了脸。我上前摸着胜军脸上的伤痕,心疼地问:“痛吗?”胜军摇着头说:“不痛。陈姐姐如果喜欢,过几天,我们再去采一些回来。”听了胜军的话,我眼眶热热的,紧咬嘴唇,努力地镇定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姐姐喜欢杜鹃花,更喜欢你们。”
孩子们已经把我当成知心朋友了,不管什么事都愿意跟我讲,有什么好吃的(如红薯片、野山桃等),都忘不了给我捎一点。我教孩子们认字,给他们讲故事,孩子们则教我打陀螺,玩推圈。在孩子们面前,我几乎忘却了自己的处境,与他们一起快乐,一同伤心。
就在我暂时抹去了心头的苦闷和烦恼的时候,童锐又撞进了山寨。
那是一个下午,天空阴沉沉的,我得了感冒,睡在床上,大桥在家陪我。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有人叫大桥到陈主任那里去一趟。过了片刻,忽然有人在掀我的被子,我以为是大桥妈回了,来看我。我懒得动,仍然闭着眼睡。接着,我感到有一双手在脱我的睡衣。我猛然睁开眼睛,看见童锐正赤身**地朝我扑过来。我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喊:“来人啦,快来人啦!”。童锐用力把我按在床上,轻蔑地说:“你喊吧,喊破嗓子也没有人来。外面都是我的哥们。”我大声斥责道:“你跟滚开,流氓!”童锐见我反抗得厉害,便软硬兼施地说:“只要你依了我,我保证带你离开这里。”我不相信他的鬼话,气愤地说:“我愿意留在这里,不要你管。”童锐一听这话就火了,恶狠狠地说:“你给跟陈发桥好,不就是想逃吗?可陈发桥没有本事帮你逃啊?我要帮你,你却被让,我看你生的贱。今天,你不依也得依!”童锐使出浑身力气,我无力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