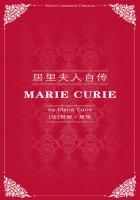1考验
这天清晨,天气突然变了,天昏地暗,电闪雷鸣,狂风大作,豆大的雨点不断地打着玻璃门窗。人们或是撑着雨伞,或是披着雨衣,匆匆而过,不时喷出一句“这鬼天气”。居维埃路居里住的小院子里,呈现出一阵紧张匆忙的情形。
皮埃尔的时间表堆满了这一天的工作。首先要到科学院去参加研究论文的评定,然后要到出版商高替叶·维亚尔那里去看自己即将出版的一本最新著作清样,还要参加理学院教授联合会的聚餐。诸事办完之后还要去实验室。晚上,由于这太多的事搁在大脑里,使他无法入眠。他早早地起床后,简单地梳洗着,然后吃女佣给他准备的早餐,自己整理好公文袋。
玛丽也要去赛福尔上课。由于大雨滂沱,7点钟时,屋内还十分黑暗,她点上灯,早早地起床后,除履行妻职之外,还要履行母职。叫伊雷娜起床,给艾芜穿衣服,替她们梳头发,扎丝带,然后是整理床铺,还要为自己梳洗。皮埃尔在窗前看了看天气,倾盆大雨仍下个不停,他拿好雨伞临出门时,大声叫喊:“玛丽,你今天去实验室吗?”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玛丽一边忙乎着,一边回答丈夫:“我今天没有工夫去。”家里一片嘈杂声,外面又是特大的风声雨声,夫妻俩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玛丽又一边干活,也不知皮埃尔听清楚了没有。因为时间关系,皮埃尔急着要走,只听见“砰”的一声,大门关上了。这天早晨,这对夫妻面也没碰上,话也没说一句,就匆匆分开了。
午餐聚会是在一种和谐、亲切的交谈中进行的。这次聚餐都是一些志趣相投的学者、教授。饭店为他们选择了一间安静、无人打扰的餐厅。他和他钦佩的同事们亲切地谈索尔本,谈科研、谈职业。进餐时皮埃尔与坐在他旁边的亨利·普安加瑞教授谈笑风生,津津乐道。皮埃尔告诉他此刻他正专心研究的一些问题:镭射气的定量;镭射气的生理作用;他最近参加的招魂术实验;还有一些关于女子教育的独特见解。他谈他的新奇理论。谈他的新发现,滔滔不绝,眉飞色舞。皮埃尔平时一脸的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然而,当他谈到科学时,便是那样神气活现,精神焕发。亨利教授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称赞,间或提出一些问题。皮埃尔此时的心里,只有科学,只有放射学,只有镭和镭射气。他是那样专注,那样投入。他的宏论、他的假说、他那伟大的天才使他的同行们不得不折服,不得不惊叹。
教授们这次聚会主要是讨论科学职业上的问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烈攀谈之后,谈话转到实验室里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大家都是搞科学的,都有自己的实验室,化学物理学的杀伤力多大,造成的危害性多大,大家心里均有数。皮埃尔立刻赞成拟订一个减少研究者所冒危险的规则。在皮埃尔长期的艰苦的研究中,他和夫人的手上脚上身上,都留下化学酸液烫伤的疤痕。
这种平静的聚会是皮埃尔很欣赏的,没有俗套,不带政治色彩。皮埃尔很轻松愉快。大致两点半钟时,他突然想起还有别的工作要做,不顾大家都未退席,余兴未尽,他便微笑着站起来向朋友们告辞,并且与当天晚上还需见面的让·佩韩教授握手,互相祝福着:“晚上见!”
皮埃尔匆匆来到门口,一阵冷风扑来,他浑身打了个寒颤。大雨仍是倾盆而泻,热烈的心情顿时被冷落了下去。他不经意地望着天空,紧蹙着眉头,表示对这种天气的愤怒,然后撑开他的大雨伞,顷刻间,消失在茫茫雨帘中。
他挤进川流不息的人流,走进塞纳区,周围都是嘈杂声,电车喇叭声,烤香肠、烤面包浓郁的香味,他充耳不闻,目不斜视。他的脑子里装满着物理实验,放射学、镭射气……有时想到一个新奇的问题,他会露出一丝微笑,算是对大脑的赞赏。
到了!高替叶·维亚尔出版印刷厂。他抬头看了看,大门紧闭。他感到纳闷,因为他是不太关心政治和战争的。一打听,工人罢工了。“倒霉!”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表示对工人罢工不理解。他在门前徘徊了一阵,总希望会出现奇迹。在他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便又转身往多非纳路走去。这是巴黎旧区一条十分喧哗热闹的街道,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行人摩肩接踵,马蹄得得,车夫叫喊,呼呼的电车声刺入耳膜。马路上挤满了奔驰的车辆,人行道上拥挤不堪,这条原本狭窄的街道,更是负荷沉重,喘不过气来。
皮埃尔本能地选行人稀疏的路面走,有时走在马路栏石牙上,时而又来到马路上,颠颠簸簸,步伐极不稳。由于天气太冷,他把手插进口袋,本能地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叠稿纸,看了看,又塞进口袋。这是他的朋友余班提交科学院的论文,请皮埃尔修改。于是皮埃尔的脑子里又增加一个新问题。我应该赶快看看,不能耽误人家,老是装在口袋里,怎么行呢?今天不行,明天一定得看。这时他又想到实验室,今天还没去实验室呢!玛丽是否去了实验室?如果她去了,没看见我,她又会着急……也许她已经在做实验了。他想的事情太多,眼神集中,脸色凝重,大脑不停地转动。想到这,他加快了脚步,跟在一辆向诺夫桥驶去的轿式出租马车后面,走上了柏油马路。到了波恩纽夫路与滨河路的叉路口,喧哗声更大,穿梭而过的电车,马车筑成了屏障,大有挡住行人通过之势。皮埃尔正想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去,全然没有注意一辆满载货物的四轮马车正向他奔来。他突然抬头发现后,一惊,正欲转身快步避开,可是已来不及了,马儿惊得前蹄腾空起来。皮埃尔慌忙之中脚下一滑,一声大喊,引起了周围惊恐的呼喊,马车轮子飞驰电掣般地从他身上辗压过去。霎那间,一颗天才的头颅被轧得粉碎,当即脑浆迸裂、血水、泥水、雨水混成了一条黑色的河……风在呼、雨在吼、行人在大喊;“停车、快停车!”然而晚了,晚了!一个伟大的生命瞬息间被夺走,巨星陨落了!
有人抬来了一副担架,几个警察抬起那个鲜血淋漓,却还有体温的躯体,一连拦了好几辆陆续驶过的马车,但是没有一个车夫肯用自己的车来运那满是污泥,尚在流血的尸体。最后还是警察硬性拦截一辆马车,才把尸体送到附近的医院。医生用海绵洗净那张泥泞的脸,看看已经压碎的颅骨时,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已经无回天之力了。无可奈何,警察只好将尸体抬回警察局。人们根据死者那极旧的衣着,不整理的发须,被化学药品灼伤的手,判定他是工人或搬运夫。当警察打开他的钱包,检查他的证件时,发现牺牲者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皮埃尔·居里,索尔本大学物理系教授,一个著名科学家,风靡世界的“镭”的父亲!惊讶使他们张开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消息传开。行人骚动着,越挤越多,并发出怒号,不少人举起拳头朝车夫路易·马南打去,并怒喊着要用路易·马南换回皮埃尔的再生,有的人抓住马南就往门外拖。警察怕出危险,不得不出面干涉。路易·马南无意反抗,他愁丧着脸,痛苦地抽泣:“你们打吧!打死我,我该死啊!”他是无心造成这次惨案的。多少人围过来,挤在一起,多少人想看看这位科学巨星,多少人悲泣恸哭。一时间,满街的人都停止了脚步,悲号痛哭充斥着这一方阴霾的天空。车辆停了。交通堵了,几个警察不得不分头疏通交通,迅速安放好尸首。
这飞来的横祸突然降临到居里这老少三代和睦的家。风声、雨声、雷声骤然停了下来,只留下一片血污,一片哀寂。居里家的门前,破天荒停下了不少汽车和出租马车。连共和国总统府那令人炫目的汽车也停在门前。门铃呜呜地响着,大门缓缓地拉开一条线。传话说:“居里夫人没回来”,又慢慢地关上。
门铃又响了,理学院院长保罗·阿佩尔和让·佩韩教授来到了这所阴冷的住宅。他们接到通知,迅速赶来了。他们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噩耗告诉玛丽,得知玛丽不在家,他们只好保持一种尴尬的缄默。
这所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居里大夫和女仆,显得特别的孤寂和冷清。见了客人,女仆惊慌失措,连茶水也不知道送上。老居里大夫见面前的客人表情严肃,情绪低沉,蕴含着一种忧郁的心情,心里极慌乱,瞪大着惊讶的眼睛。保罗·阿佩尔不愿在玛丽知道之前把消息告诉她的公公,所以保持一种困窘。然而,这个头脑清醒敏锐的老人,在客人痛苦的表情,疑虑的脸上,找出了一个他不想知道的可怕的结果,他似乎自言自语地道:“我儿子死了?!”
他希望这不是事实,希望有人出来否定,他的潜意识里,根本就没有把事情想得如此坏。
到此时,保罗·阿佩尔才把这件憋在心里的不幸的事情向老人叙述着。慢慢地,他那皱纹巴巴的脸上滚满了泪珠,佝偻的身子显得更加瘦小。他喃喃地重复着:“我儿子怎么了,他当时在想什么?”有什么比老年丧子更为悲痛?皮埃尔是他一手教育和培养出来的,他对儿子充满无限的希望。早晨出门时,雨伞还是老人递给他的,他说中午不回来吃饭,晚上会早点回来,怎么会不回来呢?儿子向来是说话算数的。可是他,他怎么会走了。“他当时在想什么呢?”老人那枯皱的眼眶里泪水不断线地往下流。
大约晚上6点多钟,锁孔有被钥匙启动的声音,门开了,玛丽愉快又欣喜地出现在客厅里:“爸,皮埃尔回来了吗?给你买了……”
当他抬头看见客厅里出现不少朋友时,话语打住了,并惊奇而客气地打了招呼。这时老居里大夫的哭声越来越响,朋友们的脸上极其哀伤和忧郁,此时的玛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一下子掉到了冰窖里,她想可能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故了,但是她没有想到皮埃尔会出现如此不幸。她的耳边响起保罗·阿佩尔哀惋的声调,隐约听到皮埃尔被车撞倒,当即死亡……
玛丽僵直了,她手中的皮包、食品啪地掉到地上。她认为是耳朵有问题,没听清楚,又急促地问:“什么?皮埃尔死了?这不可能,不可能。……”
她渴望听到相反的结果,渴望听到否认的语言。保罗·阿佩尔院长只得再次安慰她:
“夫人,你要冷静,这是真的,真的……”
玛丽像木头一样僵直着,毫无生气,毫无感觉,喃喃地说:
“真的,皮埃尔死了,这是真的……”有如晴天霹雳,有如万箭穿心,她无法适应,无法转过弯来。她完全痴呆着,一动不动。教授们非常着急,紧紧地扶住她的手臂。
此时,也许是几分钟内,她眼前浮现出多少美妙的画面:皮埃尔那坚决固执的求爱;他们那美妙的郊游;臂挽着臂在去实验室的路上;那艰难的岁月;那苦度的四年中相依为命,艰苦奋斗,并肩研究;如今,荣誉、教席都来了,经济也好转了。索尔本大学教授教席是皮埃尔的目标,他刚上任,刚开展工作。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许多课题等着他去研究。他的助手,他的学生,他的孩子,他的父亲,还有他相亲相爱的妻子,他的合作伙伴都需要他,都离不开他。他怎么会撒手不管?他是个责任感极强的学者、丈夫、父亲、儿子。他怎么会死呢……她内心的纷扰,思想的纷乱,心灵的碎裂都在她那悲惧的脸上显示出来。
“皮埃尔死了,”这个她连想都不敢想的字眼传入她的意识中,立刻就涌上一种落寞,一种凄凉。从现在开始,她就要成为遗孀,一个孤苦无助的妇人。他们合作的事业就要告一个终结了?她的脸色苍白如纸,浑身颤抖,嘴里喃喃地说些什么,只有她自己才能听懂。
“夫人,别太难过,要坚强一点。”人们表示哀痛和安慰的话,她什么也听不见,只是神情专注地盯住前方,当大家问她必须要她回答的一些问题时,她丝毫没有反应。她在等着、盼着她亲爱的丈夫。
有人把从皮埃尔衣服口袋里找着的几件遗物送来:一支自来水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表。接着一辆救护车停在这所房子的前面。玛丽像触电一样立刻有了反应,她迅速地跑出去。爬上车。是他,她的丈夫,她的师长,她最崇拜的工作伙伴,她最熟悉的平静和蔼的脸。她俯下身去,泪水像打开的闸门,哗哗地滚落下来。她哭着,喊着,不停地吻他那满是血污泥污的脸,吻他那还有热气而柔软的身体,吻他那还能屈伸的手。这种炽烈的爱,这种痛苦、这种惨像,使周围的人为之悲伤,发出沉重的哀号。
大家强拉她到房间里去,把皮埃尔的躯体慢慢地抬进屋里,准备入殓。玛丽使劲地挣脱出去,再一次扑向皮埃尔的身体,紧紧地抱着那渐渐僵硬的躯体嚎啕大哭,任凭别人好说歹说就是不放,直到她疲倦地晕倒之后……
命运真会捉弄人,竟把一对“天配良缘”的恩爱夫妻,一对天才合作者生生地拆散分离。玛丽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是1906年4月19日,皮埃尔 46岁,而他们的女儿一个 8岁,一个仅16个月。
第二天一早,雅克·居里来到玛丽的面前,他本想对这个十分悲痛的弟妹安慰几句,然而当他们面对着的时候,双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看见眼睛里,闪动着伤心的泪花。还是玛丽坚强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踱着步子。她用嘶哑的声音,安排女仆为艾芜梳洗,安排一对女儿的早餐,以此来冲淡这忧郁的气氛。
玛丽失去了丈夫,居里一家失去了亲人,世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舆论界哗然,各地报纸纷纷刊载这一噩耗,报道着多非纳路的悲惨事件。许多表示同情和悲哀的函件雪片般地飞到克勒曼大道的居里宅第。国王、部长、诗人、学者,各个国家各个阶层,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崇拜者。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克尔文勋爵,法国著名化学家,曾任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的马斯兰·伯特娄,巴黎大学校长李普曼教授等都发来了十分沉痛的唁电。皮埃尔的助手舍纳弗代表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发表了极其沉痛的悼念文章:“皮埃尔先生是我们最敬爱的人。他对任何人都十分友善,品德高尚,精神伟大。就是对于一个卑微的合作者,都是那样关怀备至,体贴入怀;就是地位最低下的工友、仆役,他也十分同情和友善。他在我们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噩耗传来,实验室的所有人员均嚎啕大哭,其伤心至极,是前所未有的。”
法国和世界科学团体,纷纷以各种方式哀悼和赞扬这位伟大的学者。
法国科学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亨利·普安加瑞教授,代表他的同事们在悼文中给皮埃尔一个准确而崇高的评价:“所有认识皮埃尔·居里先生的人,都会感到与他交往的愉快和轻松。他谦虚大度,正直善良,聪慧敏锐。他那众多的非凡发明,显示他非凡的才能和神妙的智力。”
皮埃尔这个十分温和而善良的人,有一颗如此高洁和顽强的心灵。他所奉行的道德行为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皮埃尔的灵柩被送回梭镇,将以最简单的仪式安葬在他母亲的墓地里。玛丽挽着她的公公居里大夫手臂,缓缓地跟在后头,最后一动不动地站在灵柩前。当人们把一束鲜花放在墓前时,她忽然拿起花来,一朵朵摘下,一瓣一瓣地撒在墓穴里。她旁若无人,静静地把花瓣撒完,然后扔下枝干,默默地回到居里大夫的身边。
处理完了后事,玛丽的一切也随之而去了。她要把这一切告诉皮埃尔,她木讷地打开那个灰色的笔记本,刷刷地写着,涂改着,每天都有,写满了一张又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