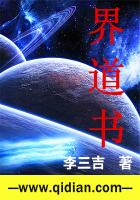冬天的山村总是黑得特别早,还没到八点,就已经完全黑透了。没有月亮的夜晚,繁星显得格外璀璨,地上的厚厚的积雪泛出莹莹的白光。
我爸手里提着两只活的野鸡,被冻得有一声没一声的叫着。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聂三娘定下的规矩,但凡是来找她看相问卜的,除了卦资,还必须准备两只活鸡,否则一概不看。
被大雪覆盖的乡间小路,看似平整,其实路上的坑洼,水窝都隐藏在雪下,一不小心就会一脚踩空,陷入积雪下冰冷的水洼之中。
因为生怕被人瞧见,父亲连手电都没带,就这样不知道摔了多少次,才摸到了聂三娘的家。
聂三娘风光的那些日子,为家里赚了不少钱财,聂家也因此成了后溪村的大户,在村北的土岗上要了一块三亩的宅基地,盖起了三进大院,聂老汉夫妇也为他们儿子聂栓宝娶了媳妇,一家四口搬进了大宅子。
唯有聂三娘还在村东头的老宅子独自一人生活,每每人们对着聂老汉提及,为啥子,三娘莫得跟你们一起住?
聂老汉眼中总会露出恐惧和焦躁的目光,口中却说:管你们莫啥(什么)事?老子跟女儿分家了不成?要你们这些八货(白痴)管!
这年头见过跟儿子分家另过的,聂家这跟女儿分家的事,倒是第一次听说,不过,人总是有一种见怪不怪的心理,日子长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话有说回来,聂老汉跟女儿分开也是有原因的。虽然女儿能够赚钱,这个家都是她挣出来的,哪里有不让她去住的道理,但是,女儿一天比一天怪异,对家人也一天比一天冷漠。似乎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事情和东西,能够让她动心的了。
最让聂老汉受不了的事,从人们开始找聂三娘求香问卜起,她的容貌似乎就定格在二十岁,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她更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人。额,这里用“人”,可能不太确切,应该用妖。
对,聂三娘从给人看相起,她就不再是“人”,在众多村民眼中她就是披着一张不老人皮的诡异精怪。靠近聂家老宅的住户,几乎都搬走了,只剩下家里没有亲人的绝户儿,没得办法,才留着那里。
其他来往这里的,都是事要求聂三娘的。莫得什么事,谁愿靠近她那鬼气森森的老宅子?
我爸在聂三娘家门口,犹豫的一会,几次想要身手去敲面前那扇掉漆的木门,都生生在半空中停住了。不知道他是因为害怕,还是别的什么。
用他的话说,一看到聂三娘家院墙里,那棵参天的老槐树,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爸想起在家还命悬一线的我,咬咬牙,鼓足气,换了下拎着活鸡的手,狠狠的拍在了木门上。
“吱吖——”
聂三娘家的门,竟然没有插,父亲因为用力过猛,一头便扎了进去,垫了几下脚才站稳。
他还是小的时候,跟着人家凑热闹来过这里,院里的东西一样都没有变。只是院里的那株老槐树有长大了。
“三娘!三娘在家不?”
父亲拎着活鸡穿过过道,就往院里堂屋走,一阵阵嗤嗤的笑声,从西屋耳房传来。
“三娘?”父亲转身向漆黑的西屋望去,就听到一声声怪异的嬉笑声夹杂这话语,从里面传来,好像不是一个人,他心中疑惑侧耳倾听。
“嗤嗤——你不要闹了——嗤嗤——弄的我好痒撒——”
“咯咯——是哪个不长眼的大晚上打搅我们——”
“嗤嗤——你不是早就算出了?还在我面前装——嗤嗤——”
“咯咯——那件事我不管——麻烦的很——”
“嗤嗤——那就轰他走——嗤嗤——”
我爸看着西屋亮起昏黄的油灯,一阵悉悉索索的穿衣声音后,西屋的门被身穿白色衣裙的聂三娘打开了。
聂三娘光着脚,一身白色的衣裙,踩着厚厚的积雪,身上散发着一阵阵妖媚的香气,宛若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走到父亲面前嗤嗤笑道:“嗤嗤——你的来意我知道。回去吧,我帮不了你,嗤嗤——”
“额……”父亲看着在这么冷的冬天,仅穿着一身夏天的衣裙的聂三娘,被深深震撼住了。
额,这是父亲后来回忆时对我说的。不过,回头想想,我想应该是父亲被聂三娘出尘绝艳的美貌所吸引了,生怕我在母亲面前说他的坏话,才找了被她的穿着震撼的借口吧。
停了好一会,父亲被聂三娘一声轻咳惊醒,这才回过神来,说道:“三娘!求求你救救我家幺儿吧!我都快三十了好不容易才升了这么一个儿子,不能就这么没了啊!”
聂三娘眼底泛起一道金光,整个人的气质陡然一变,嗓子像被人捏着,发出尖锐的声响:“咯咯——你家孩子没了管我屁事!还不快滚!再来打扰我们快活,咯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父亲被聂三娘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得连连后撤,手中的野鸡也发出凄厉嘶鸣,不过也就叫了那么一两声,便没了动静,父亲心中纳闷,难道是被刚才的声音吓死了?
“咯咯——还不走?”
“三娘!求求你了!我是村西的方耀国啊,小时候你还抱过我,我爸让我喊你幺姨。幺姨,求求你,救救我家幺儿吧!”
“耀国?你就是那个一笑眼睛就像小月牙的方耀国?嗤嗤——”
“对对!就是我,幺姨,求求你救救我家幺儿吧。”父亲苦苦哀求着聂三娘。
聂三娘脸上神色变幻莫测,一会发出嗤嗤嗤的声音,一会又咯咯咯的笑着。
父亲恭敬的站在一旁,也不敢打断,心中早就想要离开这个不是人呆的鬼地方,但是为了能够治好我他强忍着不敢离开。
“嗤嗤——既然我们有旧,你还叫过我幺姨。那就把你手中的鸡放下吧。”
“哎!”父亲见聂三娘答应就我,激动的把已经死了野鸡放在她的脚边。
聂三娘弯下腰,摆弄一下,拎起一只还要一丝气息的公野鸡,说道:“咯咯——算你运气——嗤嗤——这只还活着——咯咯——不要转身哟——嗤嗤——快扭过头去,别看!”
“咯咯——看看哟——嗤嗤——”
一连串混乱的对白,夹杂着笑声,让父亲浑身起着小米粒般的鸡皮疙瘩。
他也不知道该听那一句,到底是该看还是不看呢?
还没等父亲做出反应,只见,聂三娘捋了捋野鸡脖子上的毛,就像抚摸心爱女子的臂膀,一手握住鸡头,一手抓住鸡翅,一口咬在了鸡脖子上。
“咯——”野鸡无力的挣扎了几下,便没有动静,眼神中流露的绝望与认命。
聂三娘死死咬着手中野鸡的脖子,发出“咕咚咕咚”的吞咽声,就像是在喝水一样。
站在一旁的父亲被眼前的场景深深的震撼了,他偷偷的咽了一口唾沫,胃里翻涌着强烈不适。
“哇——”
他再也忍不住肠胃的抽搐,转身扶着墙大吐特吐,几乎都要把肝给吐出来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吐了多久,就感觉眼冒金星,整个身子像是被掏空了,浑身没有力气,就连腿也变得软软的,像是踩了棉花一般。
“嗤嗤——吐完了——”一声悦耳的笑声,在父亲耳边响起,他扭过头,看到身穿白衣的聂三娘,身上血迹点点,一张樱桃小口,鲜艳的让人炫目,出尘绝艳的俏脸上粘着一根轻飘飘鸡毛,似乎是在提醒着他刚才发生的事情。
“呕——”父亲看见那根刺眼的鸡毛,扭过头去又吐了一阵。
“咯咯——再吐的话,就给本仙滚蛋!!咯咯——”
刺耳尖锐的声音,又从聂三娘口中喊出,在漆黑的夜晚,显得那么突兀与恐怖。
我爸强压住心中的恶心,不住的往肚里咽着唾沫,试图镇压不断翻涌的肠胃。
“咯咯——”聂三娘捏着嗓子,发出刺耳的笑声,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发出一抹淡淡的金光,纤纤玉手,熟练的拔着鸡******刻间,一只野鸡就已经被她撕吧干净,她也不停顿,两根纤细修长的手指,从鸡翅下方伸进野鸡的体内,灵活的翻找着什么。
不一会,她便把手指抽了出来,指间夹着一根完整的翅尖骨。不知为何,在她手中的这根骨头竟是如此的干净,一丝血肉都没有挂在上面。
她笑吟吟的说道:“嗤嗤——算你运气好,一次就成了。嗤嗤——喏,拿回去——”
父亲刚要伸手去接,就看到聂三娘的手,猛地缩了回来,刺耳的嬉笑声再次响起:
“咯咯——等一下——还没差最后一步——咯咯——”说着聂三娘翻弄着被她扒得干净的野鸡。
“嗤嗤——血都被你喝干了,还做什么?”
“咯咯——你懂什么!!”
只见,聂三娘洁白如玉的手掌,伸进野鸡的腹中,拨弄了两下,便扯出一颗紫红色的鸡心。
“咯咯——大冬天还能让我喝到这么新鲜的鸡血,我不为做些什么,感觉好些欠着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