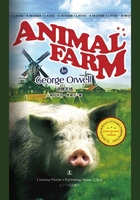苏瓷瓷
苏瓷瓷,女,20世纪80年代出生。医学院毕业,曾在精神病院工作5年。做过护士、宣传干事、迪厅领舞、酒店服务员、报社编辑。曾获得中国作协第五届文学新人奖——“春天文学奖”、《长江文艺》第一届“完美小说奖”;短篇小说《李丽妮,快跑》入围“200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第九夜》和随笔集《一个人的医院》。
多年前,我在风中奔跑。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种感觉。耳边是呼呼啦啦的风声,树木张扬着绿色的枝丫,它们嘶叫着被我抛在脑后。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最后成为一缕细小的布条,脚趾踏在上面,总是软绵绵的。原野里开着红色的野花,奔跑中,它们像火焰在我眼角边跳跃,我听到的任何一种声音,都是含糊不清的,它们在风中被快速地撕成碎片,我被这种急速的破坏感刺激着,身体不停摆动,皮肤被风吹开,五官被拉扯得变形,什么都看不分明,一切具体的事物都变成模糊的色块,在道路的四周上下跳蹿。我开始流汗,但是并不疲惫,这让我坚信我上辈子是一只鸟,有庞大有力的翅膀,实际上在我即将奔向目的地的时候,我确实看见了白色厚重的云朵,以及从云朵的缝隙中投射出的灿烂的阳光,那时候我通体苍白,扑入了同样白茫茫的空气中,我的身体被遮盖,也许我就此消失了。当然,这是错觉。
现在我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双洁白的跑鞋,外面依旧有风,但它不再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我蠢蠢欲动,但是我不能翻出去和它们一起奔跑,因为爸爸妈妈在窗下坐着,他们在谈论我是否应该报考护理本科。这双鞋我已经很多年不穿了,它上面有些补丁,我用粉笔在鞋面上厚厚地涂了一层,但是轻轻拍打一下,白色的粉末落在地上,补丁周围黑色的针脚丑陋地呈现出来。鞋底很薄,因为它跑过太多的路,最终像一个停止生育、腹部干瘪的女人,只剩下一层薄薄的肚皮。我踏着声响巨大的高跟鞋走到抽屉前,把手里的白跑鞋狠狠地塞了进去。爸爸妈妈还在谈论着那件事,我拿起小皮包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他们嗑着瓜子。我去上班了,我盯着皮鞋上一块油垢说。爸爸妈妈叮嘱了几句,我步态婀娜地扭出他们的视线。
来到医院,见到了我的搭档杨虹,她是一个嗓门嘹亮、容易激动的姑娘。我们跟着一个喜欢发牢骚的大嘴巴男医生组成一个医疗小组,负责二十四张病床的治疗工作。我们一直以来配合默契,但是今天她脸色苍白,我问她,出了什么事情吗?她脸上快速涌起一团红潮,杨虹把我拉进治疗室,她靠在墙边,显得神色不定。你怎么了?我问她。
她看着我慌张地说,丽妮,完蛋了!
我弹了弹护士裙上的米粒说,到底怎么回事,别搞得神经兮兮的!
从杨虹颠三倒四的诉说中,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她在中午发药的时候,误把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药发给酒依赖的病人喝了。是哪个酒依赖的病人?我问她。
她瞪了我一眼说,杨振羽啊,我们管的病人你都忘记了?
我也瞪了她一眼说,妈的,我怎么知道,我们的分工不是你管病人,我管病历吗?因为我对病人的厌恶,所以我从来不对病人进行查房,而杨虹又不擅长文字工作,所以我们私下约定由她负责给病人查房、剪指甲、梳头、进行健康宣教等等,而我根据她对病人查房了解到的病情变化来书写护理病历。虽然他们的病情每隔三天都是由我来记录,但实际上我根本对不上号,我连自己管的病人都认不全,只管从杨虹的查房中摘取重要的话,记录下来而已。
看到杨虹恐惧的样子,我宽慰着她,没事的,你先带我去看看病人。
一到走廊上,我就看见一个身形魁梧的男病人在墙壁上摸索,是他吧?杨虹点点头。毫无疑问,这个病人出现了幻视,他看见墙壁上有东西,所以就不停地摸索,这是一种谵妄状态,当原本没有幻觉的人误服了治疗幻觉的药物后,他就会出现幻觉。药理是件玄妙的事情,这个本来只是单纯酒依赖的病人被杨虹的两片药搞出了精神分裂的症状。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杨虹气愤地跺着脚,她已经是满脸通红。
李丽妮!她指着我的鼻子吼道,你笑什么啊,你少幸灾乐祸,你不给我出出主意还看笑话啊!
我强忍笑意对她说,好了,好了,我不笑了,你别激动。好在今天是周末,就我们两个值班,领导都不在,你怕什么啊。喝了就喝了,又不会出人命,过几个小时药物代谢就没事了。
杨虹显然不满意我的回答,她焦急地搓着双手说,可是刚才医生打电话说主任下午要来病区,万一他看见这个病人在走廊上乱摸索就完了。
我说,那只有把他弄到病房里不出来,主任就看不见了。
杨虹沮丧地叹着气说,可是病房里都没有锁,谁管得住他,要是他自己跑出来,主任还不是会看见?又不能把他约束起来。
是啊,我也有点儿发愁了,没有理由把一个酒依赖的病人用绳子约束在病床上,这样要是主任看见了会更加疑心。怎么办呢?
我和杨虹在走廊上来回走了几趟,杨虹突然拽着我的胳膊说,对了,丽妮,我们给他打安定让他镇定下来,那他就不会乱跑了,怎样?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杨虹就跑进了治疗室,她用注射器抽取了2ml安定,然后让我把病人拉进了病室。微微发黄的药液从针头缓缓进入病人的体内,病人起初在床上挣扎着,杨虹半跪在病床上,曲着双腿顶着他的膝盖,我紧紧地箍着他的手腕,他苍白的手掌使劲蜷缩着,青筋暴起,杨虹一只手按着扎在他手背上的针柄,一只手快速地推着注射器的活塞,慢慢地他的手掌松开,像一片干枯的树叶耷拉在白色的床单上。杨虹拔出了针头,用棉签按住了针眼,这个皮肤黝黑的男病人庞大的身躯陷在窄小的病床里,他闭着双眼,无声无息。
我走出了病室,用冰冷的水反复冲刷过双手,然后靠在护理站的窗边等待它晾干。我把双手高高地搭在窗户的铁条上,这些密集的铁条把外面的世界切割成碎片。一个小女孩站在楼下的落叶中,她的母亲粗暴地用手掌拍击着她的小脑袋,女孩的哭声响亮地在医院内回荡。一滴滴冷水从我张开的手指慢慢滑落进袖管里,然后囤积在胸口,逐渐凝结成一块坚硬的冰。
那个病人不会出什么事吧?我的声音像生锈的闹钟,沉闷而又艰涩。
你放心,他不会死的,他会好好睡一觉,醒来什么都过去了。杨虹一边洗手一边头也没回地说。
中途我忐忑不安地去给打了安定的病人测了几次生命体征,还好他的情况稳定。杨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丽妮,别担心。我看着窗外一块块裂开的乌云,它们恍惚而又阴险地飘来飘去,我们会得到报应吗?我突然问了一句。杨虹在我身后冷冷地说,我们早就在承受报应,每个人都在承受报应,这并不可怕。说完,她重重地合上病历,白色的铁皮外壳在桌面上发着光。
我们一直在犯错,发错药、画错了三测单、打破了注射器、一个病人把开水泼到了另一个病人脸上,我们垂头丧气,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护士们个个无精打采,嗓门粗暴地在病区里不耐烦地喊着病人的名字。我们三班倒,没有黑夜白天之分,人人都要依靠安眠药维持正常的生活规律,以便不被病人所影响。
我从来不对父母讲这些事情,我们三个人围坐在饭桌前,热气腾腾的饭菜上漂浮着油腻,我能察觉到一种异味,像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身上散发出的恶臭。我小心地夹起一粒粒米饭咀嚼着,爸爸妈妈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习惯在晚饭时决策我生活中的新计划,比如报考英语补习班、护理本科、职业等级证,或者安排相亲。我偷偷盯着电视,正在举行长跑比赛,选手们像矫健的鹿,结实的肌肉充满韵律地抖动着,她们挥动着手臂,在跑道的白线上像欢快的音符激烈地跃动着。我坚信,如果此刻我在她们之中,那么冠军就是我。这时候,一个女孩已经越过了终点线,周围的观众都起身鼓掌,我疲惫地放下碗站了起来,妈妈说,你再吃点儿饭啊。我摇摇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打开上锁的抽屉,里面除了一双白跑鞋外就是一卷发黄的纸张和笔记本。纸张的边角卷起,上面的字迹已经开始模糊,这一卷都是我的获奖证书,从小学到中学,从校级到省级比赛,有三个字眼在这些证书中是固定的:“李丽妮”、“长跑”、“冠军”。我知道我还会拿到国家级的获奖证书,并且不会只是一张。这虽是意料之中却仍让我兴奋不已,我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跑步,包括在梦里,直到爸爸妈妈强行让我上了医学院。除了跑步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打开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我在医院工作的一年中所出的差错,其中有绝大部分是领导没有察觉,但是同事知道的,因为她们是参与者,我们相互包庇,还有一些是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我既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产生过愧疚,我只能理解这是种习惯,我详细地记录下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吃错药、打安定、像影子一样左右摇晃的病人,然后我合上笔记本把抽屉锁好,关了灯开始睡觉。
在科室里,我是公认做事情最快的护士,我端着注射盘跑着去给病人打针,推着治疗车跑着去拿药,上楼下楼都是我噼噼啪啪的跑步声。护士长和同事们都认为我大可不必这样,精神病科和急诊科不一样,精神病科连空气都是迟滞的,护士长觉得我有点儿精力过剩,所以把带病人活动的任务交给了我。
楼下空旷的水泥场,四周是高耸的围墙,一个护工把守着唯一的出口处,我指挥病人排成一队,场地里一半是阳光,一半是黑影,我站在队伍的前列开始带领他们跑步。一圈、两圈,病人们疲疲沓沓地挪动着脚步,开始逐渐退出队伍。跑到第三圈,我发现一个长头发的女病人一直跟在我身边,她呼吸均匀,毫不吃力地跑动着,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不熟悉任何一个病人,但是她怎么这么轻松地跟在我身边?我下意识地加快了步伐,她没有看我,但是迅速调整了速度,使我没能把她抛之脑后。我暗暗吃惊,然后憋足了一口气,使劲往前冲,耳边开始传来风声,而她的长发飘扬起来,始终在我眼前晃动,我的手臂大幅度地摆动,我看见她的脸庞开始涨红,但是她依然在我的右边跑动。我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劲敌,是的,我已经把她当成对手,在赛场上从来没有人能这样紧紧地咬住我。不知道跑了多少圈,我们始终并肩而行,虽然她的速度和耐力让人吃惊,但是她不可能超越我,她紧紧崩起的身体,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和沉重的脚步声已经传达给了我这样的信息,但是同样,我也不可能超越她,胜负就在一步,可是我已经到达了极限。我从开始的惊讶、不可置信、暗自较量到无奈,最后心里却是一片平静,我们继续跑着,保持着一致,像怀有某种默契,直到护士长在楼上尖叫,李丽妮,你还跑个没完啊,快把病人都带上来吃药!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病人们都坐在台阶上看着我们,我打量着她,她大口喘着气,小眼睛,年龄和我相仿。我冲她笑了笑,她也报之以微笑,然后我带着一群病人重新回到病区。
到护理站后,我翻看了她的病历,昨天晚上入院,是民政局送来的,原因是在街上裸奔。年龄不详,家庭住址不详,只知道自己姓王,病历上写着“王某”。我合上了病历,这个不知来历的女病人居然那么能跑,让我很好奇,我决定找她谈谈。
杨虹把王某带进了病室,我靠在窗边看着她。她一进来就坐在了病床上,双手支着床沿,两只脚不停地相互撞击着,她没有看我,而是四下张望。
你叫什么名字?
她抬头看看我,一脸傻笑。我姓王,她说。
王什么?
我姓王,我姓王。她低下头拨弄着手指,重复着。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
她摇摇头不说话。
我注意到她裸露出的皮肤上有很多深浅不一的伤痕,有的已经结痂,有的还是新鲜的肉红色。你的家人呢?
她再也没有抬头,只是一味地摇头。我开始失去耐心,很明显,她是个思维混乱四处流浪的精神病人。我想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具有擅长跑步的特征,她什么都不清楚,我向门口走去准备结束这次谈话,突然王某从床上跳起来,她在我的身后大喊,我是长跑冠军,我要跑,跑,跑!我转过身,她的身体仿佛被注入某种神秘的力量,两眼变得炯炯有神,紧咬牙关,双脚不停地在原地踏步,双臂摆动,像随时准备起跑的运动员。
我马上跑过去按着她的肩膀,你说什么?王某眼睛越过我的肩膀,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身体还在不断晃动,幅度越来越大。我要跑,跑,跑,他们叫我快跑,别停下,我是长跑冠军,谁都跑不过我,我要跑……她语无伦次,越说越激动。
是谁叫你快跑?你是什么长跑冠军?你往哪儿跑?我的声音和她的重叠在一起,嘈杂而又混乱。王某一边喊着,一边开始迈动脚步,我堵住了她的去路,她弓着身体,肩膀顶在我的胸口,一只腿在前,一只腿在后使劲蹬着,我马上高喊着护工,最后他们跑来把手舞足蹈的王某绑在了病床上。我抚着被顶得隐隐作痛的胸膛走出病室,这是我第一次对病人进行查房,最终在王某凄厉的喊叫声中结束。
入睡前我躺在床上还在回想白天的事情,王某的身影在脑海中浮现,她奔跑时的样子逐渐和我重叠在一起。就算我闭上眼睛,这个画面也固执地延伸到我的梦中。我们并排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奔跑,只有脚步和心跳声在寂静的大地上响起,像两条相互追逐的影子。直到天亮,我从睡梦中醒来还隐隐觉得全身酸痛。
而这一切却又不仅仅存在于梦境之中,白天我依旧带着病人跑步,而最后只剩下我和王某,我们在院子里一次次绕过梧桐树,阳光从树叶中投射下来,斑驳的光影在我们身上打上绿色的烙印。我偷偷注视着她,她跑步时神情专注,目光探向远方,仿佛有什么在召唤着她,让她不知疲惫地跑动。我不知道她此刻是不是出现幻听,而我自己却好几次在跑步的过程中隐约听到有人在说“快跑!”,还夹杂着呐喊声。我没有停下,只是用目光匆忙地扫射了四周,病人们傻笑着坐在台阶上看着我们跑步,没有异常。我和王某已经达成了默契,在跑到第二十圈的时候,我会喊一声停,跑步就会结束。她来医院已经快一个月了,跑步已经成为了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游戏。
护理站里站满了工作人员,但是一片寂静,能清晰地听到窗外大风拍打树枝的声音。主任阴沉着脸说,你们刚才都看到王某的情况了?
是的,我心里传出来一个细小的声音。王某失去血色的右脚放在病床上,像一截腐朽的干树桩,一根肮脏的约束带丢在地上,那是我下班前让护工绑在王某脚上的。她躁动不安在病区里乱跑,医生让我把她约束起来,我又交给了护工去做,但是我不知道约束带会绑那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