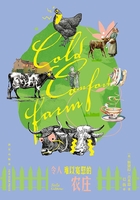王安忆
夏家窑的村长发了大愁。他日想夜想,这事可如何收场呢?
事情要从打井说起。打井又要从夏家窑的那股泉眼说起。那股泉眼是夏家窑的生命之泉,它从山那边淌过来,淌到这山折折里的夏家窑。夏家窑,就好像一只飞得特别高的老鸹,下在山折折里的一个蛋,挤在石头缝里,再也找不着了。可夏家窑却世世代代地生存下来。夏家窑古时是烧炭窑的,那时候,山是青山,树林非常茂密,泉水就从树林里穿行而过。坡坡坎坎里,都是窑眼,烧着木炭。所以,夏家窑就被窑烟蒙了一层白雾,夏家窑又像是天上掉在山折折里的一朵云。从这庄名也可看出窑家是夏姓人,但这只是开始,后来又来了一户孙姓,是沿着挑炭出山的山路找过来的。夏姓人慷慨地收留了孙姓人。反正有着满山的树木,泉眼很旺,日夜不停,从春到秋,从冬到夏。淙淙的水声,是夏家窑的天乐。又是很多代过去,夏姓和孙姓繁衍后代,人丁兴旺,坡坎里的窑眼挤挤挨挨,把山都挖麻了。不知不觉的,树林稀了,土也薄了,接着,泉眼细了。争窑的事端就此开了头。先是来文的,到衙门打官司。其时,夏姓和孙姓都是富户,买得通官,请得起讼师。可官司是个无底洞,扔给架金山也咽下去了。官司打了十几年,夏姓人和孙姓人的钱养肥了几任知县知府,状子就是批不下来。于是,就来武的了。两姓都是旺族,有的是人,前赴后继地打了几年,最后是,孙姓人把夏姓人赶下了山。这也就是,夏家窑里没有一个姓夏人的缘故。再是多少代过去,树木都烧光了,窑呢,一口一口地熄了火,凡是有土的地方,都驴拉屎似的种上了庄稼。夏家窑,如今连个旧窑址都找不着了。泉眼只剩手指头粗,很稀薄地贴着山石,一点一点洇过去。甚至,有那么几次,很危险地断了流。打井的事情,就这么来了。
打井是村长的提议,村委会讨论通过,大家集资,到县农科所请了技术员,买了设备,每户按人口田地摊派义务工。然后,钻机声就在夏家窑寂静的天空中隆隆地响起了。此时,山已经是秃山,山折折里尽是石头基,土坯墙,茅草顶的房屋,挤仄得前檐接后檐,人就在檐下侧着身子走。钻机日夜不停,歇人不歇机,拉了电灯,照得铮明,小孩子在灯下窜来窜去,可真是热闹啊!像过年似的。村长就背着手,走来走去,吩咐这,指示那,哪想得到会出什么事呢?样样看来都是喜庆的迹象,技术员说不两天就可出水,没一个人说过晦气的话,做过有凶兆的梦。天天都是晴天,大好的日头。可是清石头的时候,却把孙惠家的独苗,孙喜喜,埋在井下了。村长恨不得在井底下的是他自己。
孙喜喜今年十八岁,去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准备复习一年,今年再考。他长得清眉朗目,宽肩长身,又爱穿西服,就像电影上的人。初中时,就有女同学给他写信,表达爱意,还有上门来提亲的,但都被他拒绝了。他一心要考大学。他认为,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走出夏家窑。走出夏家窑,是夏家窑这一辈的青年普遍的想法。他们认为上级政府对夏家窑的种种扶贫政策,其实都是白搭。什么送电,拨款,传授养长毛兔的技术,等等,都不是根本的办法。根本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迁徙。丢下这块不毛之地。当他们听说二十年前,政府曾经动员夏家窑,迁到山下平地去,还给了迁移费。可夏家窑就是不走,有人呢,走了,走上个把月,花完了迁移费,又回来了。这一段历史可把他们气炸了。他们甚至还有人动心思,去乡里讨回这个政策。可是乡里回答说,这可不好办了,现在都分地了,二十年来,平地上的人口更稠密了,你们往哪儿插呢?谁能匀出地给外来户呢?这样,走出夏家窑,就只有靠个人奋斗了。像孙喜喜这样有知识、有头脑的青年,走出夏家窑的决心就更比别的青年要坚定、执著。可是,现在,他非但没走出夏家窑,还埋在了夏家窑的山肚里了。
孙喜喜他爹妈只他一个孩子,还是个老来子,四十岁上得的,传宗接代的指望都在他身上。兴许是那遥远年代,孙夏二姓争窑的胜负结局,给后人留下的生存原则,夏家窑特别重子嗣。若不是人多,怎么能打败夏家,占山为王?人嘴能吃穷山,可是没人呢,连穷山都没了。人,是立足之本啊。夏家窑不怕穷,只要有儿子,就是个富户。院子里,爬着带******的,披屋里,草盖着寿材,那么,就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做人的着落就有了,其余都好说了。为了这,夏家窑每年都要欠下大笔的超生罚款,说实在,它的穷,有一半是罚穷的。村长,要不是为超生,部队上带回来的党籍,怎么能丢了。所以,这里的青年,定亲都早,怕人家女儿不肯来这穷地,就下大彩礼,夏家窑的彩礼大是著名的。这一来,又把它那一半,穷掉了。孙喜喜他爹妈,早为孙喜喜积攒下厚厚的彩礼,人民币都掖在炕席底下,就等着定亲那一天。无奈孙喜喜就是不要,硬是要上大学。就这么一个儿子,什么事都指着他,又什么事都由着他,挺不好办的。不过,孙喜喜就这件事上不听大人的,其他地方,都是个好孩子,性格特别绵善,也孝顺。这不,打井派义务工,他爹孙惠一个人就够了,可他偏不,要顶他爹去。孙惠觉得儿子是顶他去死的,心都碎了。
孩子就这么走了,孙惠用年前备下的板子发送了儿子。这板子原先是备给自己打寿材的,备料时怎么想得到睡的会是自己的儿子?孙惠又觉得自己是送儿子去死的,年前就送上路了。真是过不去啊!发送完儿子,老两口拾掇拾掇,就喝了农药。幸好半路被人看见,夺下瓶子,再连夜送到乡卫生院,救下了。人是回来了,可那心却回不来了,只剩一口气罢了。村长看着并排躺在炕上的一对孤老儿,心想,怎么才能救老人的心呢?村长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起了这么一件事。
这事就更远了,要远到打胡宗南的时节,几十年的事情了。村长是五十年代生人,这事也是听老人们说的。说的是,胡宗南进攻陕甘宁的时候,夏家窑跑来一个受伤的小女兵。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叫胡宗南的队伍打散了。小女兵伤在肚子上,沿着一条古时挑炭的旧道,硬是爬到了夏家窑,钻进了孙来家的草堆里。那时,孙来他奶奶还是刚进门的新媳妇,早起抱草烧锅,见那草堆都让血染红了,接着就看见草里窝着个小女兵,小脸苍白,眼闭着。小女兵在孙来家的草堆里,窝了七天七夜,乡亲们都去看她。开始还想搬她进屋,可一动她,肚子上的洞就流血,再不敢挪她了。也不敢喂她吃喝,她一吃喝,肚子上的洞就流脓。她已经说不出话了,问她什么也未必听见。她只是睡着,偶尔睁开眼睛,很安静地看看天,夏家窑被山挤成狭缝的天空。她的眼睛特别黑,特别大,眼毛又长又密。看一会儿天,又合上了。她只剩一口气了,可这一口气就是不散。乡亲们都落泪了,想她实在是舍不得走啊!那么年轻,还没有活过人呢。大家一起相帮着在孙来家草堆上搭了个棚,好替她遮挡夜里的露水。草堆上摞几床被,围住她。小女兵显得更小了,就像个婴儿似的。就这么,第七天傍晚,小女兵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咽气前,她开口了,叫了声“妈”,声音很脆生,就像没受伤的好人似的,可是紧接着就闭了眼。这时候,脸上竟有了丝血色,红润润的。人们听她叫妈,就想她妈在什么地方正牵挂着她呢,哪想得到她是来了夏家窑呢?这一声“妈”,就当是叫夏家窑吧!大家凑了副杂木薄板子,几十年前的夏家窑,虽然不烧窑了,树还是有几棵的。大家凑了副板子,发送了她,将她埋在进村口高岗子坟地里。人小,棺材小,坟也小,像个小土墩子似的。到了清明,自会有人在坟头给她压块土。
这时候,村长就想起了小女兵。在人们的传说中,这是个俊俏的乖女子,有一双大而黑的眼睛,尖下巴颏。村长想,给孙喜喜结个阴亲吧,老人心里好歹有个念想。他又想,孙喜喜一心想考大学,就为了走出夏家窑,走到什么不知名的地方,现在走不成了。可小女兵是从外边不知名的地方来的,兴许是个大码头,当兵嘛,也多半是有文化的人,说给孙喜喜,会称他心的。还有,这两个孩子都走的叫人心疼,前一个遭了老罪,后一个呢,是眨巴眼间没了天日,神都返不过来呢。又都是花骨朵样的年纪,还没活过人呢!村长在想象中看见了小女兵望着夏家窑的天的大眼睛,一点不诉苦,一点不抱怨。这两个苦孩子会互相心疼的。村长的眼眶湿了,心里十分酸楚。停了一时,村长摇摇头,对自己说,你还当真了呢!他虽然丢了党籍,可毕竟是受过教育的,是唯物主义者。此时却想,还是唯心主义好,唯心主义慰人心,让人走到哪一步,心里都存个念想。
夏家窑替孙惠家办了这门阴亲。将小女兵的坟起了,与孙喜喜合了坟,立了夫妻碑。因不知小女兵姓甚名谁,就新起了一个,叫凤凤。是个娇名字,想她这么苦,这么孤,现在有人疼了。纸扎了洞房,贴着白色的喜字,内有床柜被褥、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院子里除了骡马猪羊,还停了辆汽车,和着纸钱,一起烧了。请来一班吹鼓手,吹了大半天。又办了几桌酒水,凡有头有脸的都上了席,包括那名打井来的技术员。酒席上,村长红着眼对孙惠两口子说,往后,你们过你们的日子,孩子过孩子的日子,两下里都要好好的。从此,孙惠家果然安宁了。倒不敢说不伤心,伤心还是伤心,不时也要哭上两把,可到底是把日子过下来了。一日一日,春去冬来,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新坟变成了旧坟。然而,不曾想到的事来了。
这一日,近晌午的时候,夏家窑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开到村口就不得已停了下来,走下三个人。头一个是熟人,王副乡长,来过夏家窑几回。一回是来宣布对村长的处分,二回是来发救济款,三回是通电那晚,还在村长家住了一宿。后两个就眼生了,但一看就是城里的干部模样。一老一少,都穿着黑皮夹克,脸白白的,戴眼镜。王副乡长对看热闹的小孩一挥手,告你们村长去,客来了。于是,一串孩子顺着山坎,一溜烟地跑了。等这里磕磕绊绊,脚高脚低地走近村长家院子,村长家的鸡已经杀了,正等着锅里水滚好拔毛。派去供销社买烟的小孩也回来了,村长则站在院子前迎客。王副乡长向村长介绍那两位,一位是县民政局的老杨,一位是县文化局的小韩,边说边进了屋。初春的日子,还冻得很,屋里生着烟囱炉,炉上坐了茶水,主客围炉坐下。先是一番问暖嘘寒,再是一番秋收春种,然后静场一时,那个民政局的老杨掐了烟,咳一声,说话了。
老杨开口第一句便问村长,今年多大年纪。村长说,比王副乡长虚长一岁,五四年生人,属马。又转而问道,王副乡长可不是属羊吗?老杨又问,家中老人在不在了。村长道,母亲是七岁那年没的,父亲呢,年前也走了。老杨再问,这庄里目前还在的,年纪最长的老人是谁家的。村长就笑了,说老杨您有什么事,尽可问我,只要是夏家窑的,不敢说上下五千年,一百年却是敢讲的。老杨被村长这么一说,脸上便有不悦之色。王副乡长在一边圆场道,这里的老人没大见过外人的,话又说不清,不如先问村长,问不到了再去把老人找来问。这样,老杨才说到了正题:一九四七年春上,夏家窑有没有来过我们的伤兵。村长心里咯噔了一下,嘴里却说,可不,您问的这事我正知道,打小就听老人们讲古,说是胡宗南进犯的时候,跑来过一个伤兵,沿着古时挑炭的旧道爬过来的。老杨和小韩对看一眼,又问,是男还是女?村长心里又咯噔一下,想他们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嘴里就有些含糊,女的吗,女伤兵可不多。老杨说,还是去找个老人吧。村长一听,只得把话说实了,是女的,所以我才记下了呢!老杨这又坐定了,再问,多大年纪。村长说,当兵的年纪总归大不了。这一回,老杨很坚决地站了起来,小韩也站了起来,他们要村长带去找老人家打听。这时候,村长家里的以为他们要走,便上前留饭,说面条都擀好了,鸡也炖烂了,说话就齐,怎么也要吃了饭走。村长就不让走了,王副乡长也帮着说话,说吃过饭再去找老人也不迟。这样,那两个只得坐下来,暂把话题搁一边,说些闲篇。喝着酒,吃着辣子鸡,老杨的脸渐渐红了,眼睛带了些水光,柔和下来,说话也不那么硬了。村长一边劝酒,一边暗地里思忖他们的来意。听他们的问话,句句都是指着那小女兵,不像是胡乱问的。是小女兵她家里人找来了?又为何这多年没音信,这会儿却特地来问?要是她家里的人,就不知是个什么身份,在什么地方,想把她怎么着?倘若知道有孙喜喜这门阴亲,又会是个什么态度呢?村长不敢想,心里很不安。有几次走神,问他话只支吾着,等醒过神来,就想,这样不行,他要争取主动,摸清来人的底,再想对策。这样一径地躲,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
这样,村长就将搁在一边的话题又挑了起来。他从孙来他奶奶在草窝里发现小女兵开头,直讲到第七天傍晚,小女兵终于开口叫了声“妈”,合上了眼。最后,他大有深意地结束道,小女兵这一声“妈”叫的是夏家窑啊,所以这多年来,夏家窑一直把小女兵当成自己的孩子。饭桌上一阵寂静,都有些动情。半晌,老杨才说,看来就是她了。停了一会,村长小心地问,就是谁了?老杨看了他一眼,说:“烈士李书玉。”接着,便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道来。
李书玉,江苏人氏,一九三零年生人,金陵女中学生,在学校时就接近革命,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男友一同赴延安,不久,延安战略撤退,在过黄河时遇敌军追击,受伤掉队,从此没有下落。据最后看见她的同志说,她受伤就在这一带。她的男友一九四九年后便从部队转到了地方,曾在南北数省任领导,现已离休。虽然早已成家生子,但几十年都怀念着他的初恋女友李书玉。尤其是近年来,他开始写作回忆录,往事涌上心头,就生出寻找她下落的念头。早在半年前,就由省民政局发函来问过。这位小韩,是负责撰写这一地区的党史的,凡是当年发生过激烈战事的地点他都去寻访过了,却没有收获。回了上去,这不,前几日又下来一函,让再寻访寻访,说是受了伤掉队的,总走不远,一定是在这一带。于是这一回,无论是有过战事还是没有过战事的地点,都挨个儿走上一回,这才来夏家窑了。是这一乡最远最背的地点,来时是从县上开一辆桑塔纳,到了乡里,因是要去夏家窑,便让派出所出一辆吉普,换了车,一路颠上来,有几处石头滚了坡,还都下车去搬石头,推车,这才到了夏家窑。原是没抱什么指望的,不想倒有了结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老杨一是高兴,二是喝酒,话就滔滔不绝起来。
村长听着这些,心里茫然着,怎么也不能把小女兵和“李书玉”这个名字联系起来。草窝里的小女兵,这个苦妞啊!虽说是几十年过去了,夏家窑少有人见过她,可却是活生生的。再加上和孙喜喜的阴亲,这更是眼一闭就到了眼前。不过,这回不是窝在草堆里了,而是偎在孙喜喜的怀里。可是,“李书玉”是谁呢?“李书玉”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呢?这名字听起来,确实就像老杨说的,一个女烈士,可以上书上报,是个大人物。夏家窑原来还隐姓埋名着个大人物啊!村长就像在做梦似的。他就是趁着这股迷糊劲,应了老杨要去瞻仰烈士墓的要求,将面碗一推,站起身,走出了门。
酒喝的有些上头,脚下微微发飘,身子就很轻快,心里也很轻快。晌午后的太阳明晃晃的,略有些懒,庄子里很静,猪在圈里哼哼,鸡安静地啄食,偶尔的咕一声。村长带着那三个在夏家窑的沟沟缝里走着,还走过了孙惠家院子。院子里没人,晒着一席粮食,门框上挂着一串红辣椒,挺醒目的,日子过得像是返过一点神了。村长心里依旧茫然着,从孙惠家院子前走了过去。渐渐地到了村口那片高岗上,是夏家窑几十辈子的坟头啊!看见坟头,村长脑子清醒了一些,他想,他们这是来做什么呢?脚下却机械地绕着坟头,向孙喜喜那里走去,现在,没有退路了。
这四个人站在了孙喜喜的坟前,是个双坟头,石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孙喜喜,凤凤。村长抬头看看天,天蓝蓝的,远处,山坡上是人家庄里的苹果树,褐色的树枝,矮矮地巴着地。清明没到,已有人赶早来上过坟,有几座坟头上的土坨是新铲的。还有一座新坟,扬着白幡。他向四周望了一遭,转回头看见了那三人疑惑不解的眼睛,他惭愧地笑了一下,低下头去。
村长从此就开始了发愁的日子。开始,没什么动静,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那吉普车一开走,转眼没了影,什么老杨小韩的,也都没了影。再过几天,庄上就有传言起来了。传言说,小女兵的家人寻了过来,要把小女兵接回祖籍去。又说小女兵的家人都很发迹,也有权势,有说在北京的,有说在上海的,还有说在香港台湾的。话传到孙惠两口子耳里,老人就来找村长了,问有没有这回事。村长心想,能瞒一日就瞒一日吧,说不定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不是没动静吗?那老杨小韩兴许在别处找到了真的李书玉,小女兵就还是小女兵了。这么想,便说:“没这回事。”老人却又问:“要真有这事可怎么办?”村长想都没想,脱口就道:“有又如何?咱们给烈士找婆家也没错,孙喜喜是个正派孩子,当年学生下放,不还有找庄里农民成亲扎下的?”老人这才舒了口气,回去了。村长再回头想想自己方才的话,心里好像也有了底。一天一天平静无事地过去,村长就更有底了,心想,没事了,没事了。正这么想的时候,乡邮员却捎来了王副乡长的话,让他明日去一趟乡里,有话同他说。
村长颠颠地骑着自行车,往乡里去,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是什么事情在等着他。沿路常有各庄子派出的义务工在修路,大多是星期天放假回家的学生。脸在学堂里捂得白白的,穿着牛仔裤,或者西服,怕脏了衣裳鞋袜,干活不免就扎手扎脚的,还不时停下来讲国事,说笑话。听见自行车响,就回头看,脸上还带着笑,露出一口白牙。村长心里一惊,他看见了孙喜喜。太阳热辣辣地晒在背上,浑身上下出了点汗。有几段路是要下车推着走,又有几段是要扛着车走。山下平地里的麦子都有一高了,山里就有了些单薄的绿意。村长想着,王副乡长招他去,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上回开除他党籍就是他去乡里说话的。但有几回发放救济款也是招他去乡里说话的。不过他任怎么想,对这一次说话,心里还是有几分知晓的。离乡里近一步,心里的明白劲就强似一分似的。
星期天,乡里的办公室都锁着门。村长沿着砖砌的甬道,穿过办公室,走到后院。后院有两排平房,传来剁馅的锵锵声,还有电视机里的歌曲声。王副乡长就住那里。王副乡长正蹲在地上拾掇自行车,一架车给拆得东一摊,西一摊,一盆水里泡着破旧不堪的一根车胎。村长正要想在王副乡长跟前蹲下,王副乡长却站了起来,着两只大黑手,说,我看你怎么交代,把人家女烈士娶了阴亲。话这么挑开了,村长倒心安了,他耍着油嘴说,我的党籍已经开除了,你就开除我的人籍吧!王副乡长不和他油,盯着他问,你说怎么办?村长又笑,王副乡长就说,人家信都来了,下个月要来看坟呢,你拿什么给人家看?村长笑不下去了,抬眼看着王副乡长,看得他有些心软,说,回去把坟刨开了,另立一块碑。村长一急,说,坟不能刨。王副乡长说,不刨怎么办?村长说,要刨坟,老人又喝农药。王副乡长一听这话就蹲了下去,接着在水盆里洗猪肠似的捏叽那根破车胎。他也是乡里人出身,如何不知道刨坟的事大。村长也蹲了下去,将手插进水盆,帮忙的样子,然后就说了那天和孙惠说的同样的话。王副乡长嘿了一声,道,这阴亲配得也不合适,岁数就不对。村长也嘿了一声,你连这个都不懂吗?人在阴府是不增寿的,否则,为什么要叫阳寿呢。王副乡长说,你同我说这话行,你同人家说行吗?村长腆着脸,那你去说。王副乡长把水盆一拖,背对着他不说话。村长空着两只湿手,脸上十分尴尬。半晌,他慢慢地站起身,说,走了。也没答理,王副乡长生气了。
往后的几天里,村长有几回走到孙惠家院子前了,又折回来。老人家门框上的那串红辣椒,辣着他的眼。这好像是一点过日子的心劲,不是那么旺的,稍不留意就会扑灭了它。还有几回,他走到了那口井边上,往里瞧瞧,黑洞洞的深处,有个人影,远远地望着他,一言不发。村长想,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庄里的谣言传过一阵又平息了,这时倒是格外的安静。只有村长才感觉到不妙。清明到了,村长给老人坟上添土时,看见孙惠家的也在坟地,烧了一叠纸,又烧了一些纸扎的小孩衣裤鞋帽。他装作没看见,不料孙惠家的叫住了他。村长,她说,一边擦着泪眼,这俩孩子也该添人口了吧。村长嘴里敷衍着,那是,那是。脚下快快地挪步,想离她远些。她却也挪快了步子,紧随着他,口里念着,添个闺女,再添个小子。那是啊,村长说。他们一前一后走进庄,终于分了道,各走各的,村长这才放慢了步子。他将手袖在袖筒里,腋下夹着铁锨,慢慢地往家走,心里定下个主意。
清明过去半个月的光景,果真如王副乡长说的,来人了。一个是老头,另一个是老太,都花白着头发,腰板倒挺得很直,是大干部的模样,由县上的干部陪着。王副乡长,还有老杨、小韩,也来了,却到不了跟前,只尾随着。早有人去报告村长,村长一路小跑地迎去,脚下打着绊,几次要摔倒没摔倒。迎到跟前就往兜里摸烟,竟摸不着兜。这时,他才发现他的手在哆嗦。他的嘴也在哆嗦,话都说不成句了。那两个老人却很和蔼,还同他握了手。引去村委会的路上,村长心里颤颤的,但却是另一番心情了。他看见了老人花白的头发,还有脸上的褶子,尤其是那老汉,虽然是干部的装束,可那眼皮下的囊肉,和庄稼老汉差不多。他们的和蔼触动了村长,清明那日定下的主意,在这一时竟动摇了。他想,他们也不容易。走到村委会,门早已打开了,地扫净了,水烧开了,人一到就沏上了茶。坐下,聊了几句闲天,人口啊,提留啊,年收入啊,就学率啊,等等,便言归正传,那老太发言了。
老太操着一口清脆的普通话,听声音就像个年轻妇女,广播电台里的那种。她开门头一句就是,感谢老区的人民,保护了我们的烈士。然后又接着说,李书玉同志是老樊青年时代的朋友,一起参加革命,几十年来,我们没有一天忘记过她。村长的心渐渐静了下来,他忽然明白,这对老人不是小女兵的父母,而是她的同辈人。他这才想起来,这老头原来是小女兵的未婚夫。就是说,小女兵要是活着,就该也像这个老太一样的年纪,一样的装扮,一样的清脆的普通话,称他们为“老区的人民”。村长心里的感动平息了,甚至有些不舒服。他再接着方才的思路想,那么,这老太算什么呢?她不是占了人家李书玉的窝吗?当然,李书玉死了,老樊总归是要娶的,可人家既然旧情还在,她在这里来什么劲呢?照理说,她都不该跟着来的。村长心里的不舒服变成了反感,于是,方才动摇的决心,此时又定了。
老太说完,大家都静着,等村长说话。村长咳了一声,慢慢抬起眼睛,说道,真是对不起首长和领导,事情兴许有些误会了。所有人的眼珠子都瞪起来了,先瞪村长,又转过去瞪王副乡长、老杨和小韩。那三个通红了脸,不约而同要张嘴说话,却被樊老头的一个坚决的手势制止了,示意人们继续听村长说。村长说,昨天夜晚,听说首长要来,就特地把夏家窑七十岁上的老人会齐来问情况,老人们有的说记不清了,有的倒还记得,说孙来家草窝里的小女兵其实不是兵,是不晓得哪个地界上的砍柴的女子,失了脚,掉了崖,挂在树枝上,才留住一条命,然后顺着古时的挑炭的旧道,爬到了夏家窑来了;因为正是胡宗南进兵的当口,人们就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传了;还有,那小女子头几天还能说话,见大爷叫大爷,见大娘叫大娘,好像是山西那边的口音,这就对不上了;因为是烈士的事,政府的事,不能有半点差错的,要不咱们也对不起烈士李书玉啊!老头的脸板着,十分僵硬,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村长发现,至此,老头还只字未语。老太显然不是省油的灯,当即向陪同前来的副县长发难了,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老樊知道找到了李书玉同志的下落,激动得几夜没睡,血压都高了。副县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只能对老杨和小韩责问,老杨小韩再向王副乡长责问,最后是王副乡长望着村长,虽然一言不发,可那眼睛是把村长十八代祖宗都骂到了。村长不接他的茬,把眼睛挪开,看外头。外头地上站着乡亲,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村长将人头看了一遍,没看到孙惠和他家的。
老太又说,老樊也知道你们搞了迷信,结什么阴亲,但老樊并不计较,农民嘛,是需要长期教育的,老樊只是想把李书玉同志的遗骨,送进烈士陵园安葬,也了了几十年的心愿,对后代也是教育,真不知道你们基层的工作是怎么做的,这不是不负责任嘛!村长心里静得很,老太说什么他并没听进去,只是看着她的嘴,想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词这样不间断地从这嘴里吐出来,就像炒锅崩豆子似的。忽然间,那老头又做了个坚决的手势,老太戛然而止。老头站起身,说道,看看那女子的地方吧。他声不高,言语也不多,可村长却震了一下,他不由跟着站起身来。他又在老头那双垂着囊肉的小眼里,看见了一些熟悉的东西。就是这些熟悉的东西,透着一种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了解,厉害着呢!村长又有些不安了。他乖乖地引着人们走出村委会,门前的人群默默地让出一条道来,看他们走过去。
村长带着他们沿了沟坎走,阳光从屋檐上漏下来,一条条的,照着半张脸,都沉默着。离他们一段距离,是夏家窑的乡亲们。屋檐后边是光光的山崖,崖顶是雪亮的太阳,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崖的那边是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人们来到了孙来家院子,孙来和他媳妇还有他爹妈,站在院子里,比画给来人看当年那一堆草垛的地点,又比画给来人看,当年的院子是如何,现今改掉了哪些。南墙朝外推了几步,山墙也撑了出去,所以地形就有些两样了。一边说,一边往四处撵鸡,不让它们到中间那块地面来,鸡就喳喳着。人们围了院中间的空地一圈,想象是当年窝小女兵的草堆的地方。老头沉着脸,听孙来他爹说话,说那小女兵在草堆里度过的七天七夜。孙来也是听他娘说的,他是小女兵来到后的第二年生人。村长蹲在人圈外头,不再说话。孙来爹的声音好像是从很远处传来,漏出好些破绽,他口口声声称她为“小女兵”。老头并没有置疑,村长也不去纠正。他知道没什么能哄住这老头的,他钝钝的,却看得清底细。这老头身上有一种东西,确实打中了他,这也是钝钝的,是钝钝的悲哀。
然后,队伍就由老头带领了。他领头出了孙来家院子,村长不由得随在身后,向村口坟地走去。老头将手背在身后,抬起头四下里打量。看门里的院子,圈里的猪,场地上晒的粮食。有小孩子挤了他的腿,他还摸摸小孩子的头。老头的脸色松开了些,不像方才绷得那么紧了。那种钝钝的东西,似乎变得柔软了,可以流动的了。近午的阳光照着他花白的头顶,村长想,多少日月过去了啊!从这老头的头顶上过去,也从夏家窑过去,可是小女兵还是小女兵。他们来到了高岗上的坟地,站在孙喜喜和凤凤的合坟前头。清明添的土还湿润着,坟头的土坨坨也是新的,土坨坨下压着一张粉红纸,炫目得很。老头对着坟站了一会儿,转过身,看一眼身后围着的乡亲,低下头从兜里摸出一个小钱夹,夹子里摸出张相片,递给人群中一个老汉,说道,您老看着,是这个女子吗?
老汉拿了相片看了半晌,没吭声,传给了另一个比他还老的老老汉。老老汉看了一会儿,也没吭声,再传给一个老婆儿。老婆儿又传给老汉。相片在人群里传了一遭,最后传到了村长手里。这是一张比手指盖略大一点的旧相片,泛黄了,却还是清晰的。照的是半身正面,学生头,齐额的刘海儿,旧式便褂的竖领,嘴抿着,不笑,眼是黑漆漆的。从未谋面的小女兵一下子跳到了眼前,村长觉得已经认识了她几十年似的。几十年,他在娘肚子里从无到有,再从光腚猴长成这么个半老汉,可小女兵却一直是这副面容。就和相片上一样,不笑,不吭声,眼睛黑漆漆的。这个受了伤的小雀儿啊!村长眼睛湿了。他将相片还到老头手里,见几个老婆老汉都在擦泪。停了停,村长使劲将喉咙里哽着的一块东西咽下去,哑着声说,这多年来,夏家窑把她当自家闺女看。老头也哑着声说,她信仰共产主义,是无神论者。老头说过后,就看着地面,一动不动了。这时,村长知道,他到底是输给了这老头,他到底是犟不过这老头的。
这天晚上,村长迈过了孙惠家的门槛。他晓得,今晚他要迈不过这个门槛,老人家一宿不得安泰。他要一直迈不过这个门槛,老人家就一直不得安泰。老两口子见他来,立刻明白了,掉起了眼泪。孙惠家的一把一把地擦泪,眼睛擦得通红,都烂了,那是叫眼泪腌的。哭了一会儿,孙惠家的便起身要去烧茶,被村长拦下了。村长说,这几天,早想来同你老说,可是一直没得闲工夫,说实话,也怕你老哭,就挨着,可不说呢,又老堵在心里,是块病。孙惠就说,村长,大家都知道你也不好办。村长拦住他的话,等等,你老先听我说;有半个月了,还是清明前,我就做了个梦,现在想来,是喜喜那媳妇托给我的;她对我说什么呢?她说,她和喜喜小日子过得不错,和和美美的,可是不期然的,玉皇大帝点了她去投胎;你老知道,她上一世没活够人呢,吃苦比享乐多,尤其是最后那七天七夜,真是煎熬啊,她想活人呢!我就说,那就去呗,你先去,二年把喜喜拉扯去,再做夫妻。她就说,大叔啊,你不知道,夏家窑太背了,挤在山折折里,路又不好走,还没有水,玉皇大帝的船撑不进来接我呢!她说,大叔,你能不能送我出去呢?梦做到此就断了,开始我倒并没有上心,不就是个梦?可是过了一段,这不,来了个首长,专为了认这女子,要把她带到省城的烈士陵园。我心里就不由一惊,这不是应了那日的梦了?是玉皇大帝托人来引路了不成?
第二日,村长就专派人到乡里,给王副乡长捎了信。说是一切都妥帖了,三天后可来人领遗骨,事情由他来操办,请领导和首长放心。
这一天,吉普车先后三辆连成一队,开来了夏家窑。近村口时,就看见高岗上许多人忙碌着,有白烟腾起,被风吹开,夹着些焦黑的纸屑。有指令从最后一辆车传到了第一辆,吉普车停了,停在距村口二百米的地方。没有人下车,就这么等着。高岗上坟地里的人们没注意到吉普车,兀自干着。他们由村长带领,在孙喜喜和他媳妇的坟头四角烧了四堆纸,一边烧,一边念叨,大爷大娘,大叔大婶,我走了,感谢这三年的处处照应,和睦相处,我走了,撇下喜喜和孩子,还请多多相帮。念罢,便开始起坟。铁锨试探着插进土里,辨别着方向,然后才下力一掘。再烧纸,这回是烧给喜喜的,说着劝慰宽心的话,还有大丈夫要自立自强的话,烟裹着烧不尽的焦纸,飞扬着,就像一群黑蝴蝶。经这几番折腾,几十年前的薄板子早已散了,村长将遗骨拾在一口坛子里,又在喜喜的棺木跟前抓了几把土。等他直起身,便看见了村口路上的吉普车。他将坛子捧在手里,想这坛子只装了这些遗骨和土,怎么就突然变沉了。他小声地说了句,凤凤,这就送你出山呢。他下了岗子,走上路。最后一辆吉普车里走下一个人,是那樊老头,手里拿一块红布,等他走过去,便用红布蒙在了坛子上,然后接过了坛子。车上的人纷纷下来了,没有那老太,村长心里感到少许的安慰。而就在这老头接过坛子的那一刻,村长觉得小女兵突然间变老了,也变得像樊老头那样的年纪,头发花白,垂着大眼囊。几十年的日月一下子走了过来,闪忽之间,没有了。
老头上了车,随行的人,王副乡长、老杨、小韩,都纷纷上了车。然后,车就开走了。村长站在路上,望着车沿了山路,慢慢远去。在他身后,人们继续干着活,将孙喜喜的坟重新垒圆,垒高,四周添了新土,又烧了一圈纸。石碑上,凤凤的名字油了红漆,表示人在阳间,留着个寿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