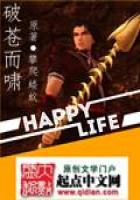然后小伟对我说:“你的这哥们儿今天一直没动手,我也不会动他。”在这么混乱的状态下小伟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令我吃惊。小伟喘了口气继续说:“待会儿你和他先回去,你帮我问问今天西郊这帮人为什么来的,明天我到学校找你,谢了啊。你和六子是一个班吗?”
我告诉小伟我在三班,同时心里忽的一沉:明天才真死定了,他们都认为我和西郊的串通。
我一回头,看见痢疾正朝我开心地笑了一下,我心里更寒了。
“哎,你叫什么来着?叫小哲是吧!”小伟突然说,“痢疾,从现在起,小哲就是我弟弟,你们以后多照顾点。”
痢疾很疑惑地看着小伟,小伟一笑。痢疾转过头,看我的眼神很冰冷。
(2)
回家的路上,我骑车带着阿远,久别重逢的喜悦被惊魂未定的惶恐所取代。我们从没见过这样惨烈的场面,以至于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到了家里已经是晚上八点了,我们俩饥肠辘辘。老爸到工程工地去了,家里就我妈在。一进门,我就强作镇定地开始嚷嚷:“妈,我饿死了!你看谁来了!”
“天天这么晚,天天这么晚!就知道打篮球,我看你期末能排第几!你爸在家的时候你怎么不敢?”妈妈一边唠叨,一边从厨房端出一杯水,突然发现阿远:“哎呀,小远,你怎么今天来了?”
我父母和阿远的父母都是同事,我妈从小就挺喜欢阿远和他妹妹,我想可能是因为她没有女儿吧,她挺羡慕人家又有儿子又有女儿。
妈妈把阿远拉到沙发上坐下,就开始一连串地问东问西:“你爸你妈好不好?你坐什么车来的?你小妹妹上四年级了吧?你吃晚饭了吗?你家是不是下个月就搬来?……咦?你这么晚到南郊来玩明天不上课?”——当教师的老妈终于敏锐地发现了问题。
“啊,啊,张姨,是这样的,明天我们学校老师教师节倒休。”一贯聪明伶俐、讨大人喜欢的阿远终于恢复了常态(多年撒谎的功夫没有落下),既回答了敏感问题又恰如其分地转移了话题。
老妈果然顺着我估计的思路发展下去:“你看西郊的学校就是教学计划做得好,教师节还有倒休。我们这儿毕业班天天加班组织复习,星期****还要到你张阿姨那儿要考试卷子,哪有时间休息。”张阿姨是我妈的同学,在市重点中学教书,我妈经常去找市重点试题给她的学生补课。
“就是,我们老师还发了好些东西呢!”阿远这家伙有点发挥过了,我给他使了个眼色,他这才收住。
“妈,你快点,我们都饿死了!每天不是提考试就是提你的学生。”
不一会儿,饭菜端上了桌,我和阿远狼吞虎咽地吃着,不时互相看着傻乐一下:是呀,能平安回来就不错了。
老妈已经吃过了,在旁边高兴地看着我们吃,一边不停地给阿远夹菜,一边数落我。我老妈有个过人的本领,就是能发现到家里来的我的每个同学身上的优点,然后和我的缺点比较。今天也是如此,尽管好几年没见阿远的,我妈还是有说的:
“你看小远穿衣服多干净,你这么大了也不自己洗衣服,天天像个泥猴,一点也不注意,想让我给你洗到三十岁呀……”
我看了阿远一眼,这小子真是挺干净的,居然还穿了一条白裤子。我心里暗想:我能不脏吗?被人一脚踹到地上,要是仔细看身上还蹭着血呢!一想到身上有血,我马上不想吃了——我得赶快把衣服上的血洗掉,否则被老妈发现就解释不清了。对了,还有那把鲜血淋漓的钥匙。
我急忙回到自己的屋里,以最快的速度换了一条裤子,把脏裤子有血的地方迅速洗净,然后丢到洗衣机里:“妈,我把裤子放到洗衣机里了,你帮我洗一下。”
“今天有点进步,至少知道自己把衣服放洗衣机里。”老妈在外面回答。
晚上,我和阿远睡在我的小屋,聊到深夜。天南地北一通神侃,我也终于明白了今天事情的起因——原来整件事是和一个叫燕子的女孩有关。(为什么大多数打架都是与女孩有关?)
燕子原来在西郊很有名。她高我一届,现在上初三。原来在西郊时见面没说过话,但是有关于她的传言很多,所以我对她也算略知一二。
燕子这种女孩通常被称为“大喇”。其实这个恶毒的词是多指那些风流成性的****,但用在像燕子这样上初中的小女孩来说,也就是因为她们找过几个男朋友,穿着打扮时髦一点而已。按照今天的眼光,他们应该是美丽时尚,敢爱敢恨的可人女子,只是当时人们不懂得欣赏罢了。燕子发育得好像比其他女生早,一张漂亮的瓜子脸,眼睛笑起来是弯弯的,胸脯稍稍鼓起,腿很长,脚踝上还系着两根红线绳。燕子好像还挺能打架,有一次,我看见她打过一个高年级的女生,拽着那人的头发抽嘴巴。
有关燕子传言的最原始资料,我想来自于我们一个同学的母亲。那时,我们的父母经常坐班车上下班,单位的班车有两辆,其中一辆乘客多数为女性,于是这辆女士班车便成为绝大多数小道消息的发源地。有关燕子的传言就是由一个女同学的母亲很严肃、很秘密地透露给另一个女同学的母亲,然后由这位母亲在教育女儿时作为反面教材很严肃地透露出来,继而再由我们这位女同学很严肃、很秘密地告诉别人,进而成为尽人皆知的秘密:
据说是燕子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被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看中,以每次见面给她二十块钱为许诺厮混过一段时间,其中细节如何不得而知,但从我们同学那位年过中年、以“破嘴”著称的母亲嘴里传来,相信一定非常“精彩”。
这次打架是因为六子欺负了燕子的一个姐妹,于是,燕子帮她出头,找了大脑袋和矮个子来教训六子。好像矮个子追了燕子很久(难怪这么卖力气)。据说,六子向这位姐妹吹嘘说自己是南城的老大,非常能打,加上家里很有钱,因此非常有名。他说想和这位姐妹交朋友,还说要带她到上海玩。女孩看他又年轻又有才华,于是芳心暗许,结果被六子给“弄”了。——我不知道阿远为什么要用“弄”这个字眼,让我很难理解确切的含义。当时阿远的口气显得非常老练、还带着几分不屑,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显得非常幼稚地追问下去。于是,六子到底如何“弄”了这位姐妹成了千古之谜。
“那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我非常不解。
“以前有一段时间,燕子是我女朋友。”阿远的声音很轻,但明显很得意。
“还女、女、女朋友?!”我又是惊讶又是钦佩,大感兴趣,一定要问个明白。阿远推三阻四不肯说,不过,奈何不了我死缠烂打终于不情愿地招出几个片断,经过我的整合现归纳如下:
阿远和燕子同属一个学校田径队——阿远百米速度非常快,在学校乃至区里出类拔萃;燕子美腿细长,腰肢婀娜是一名跳高的好手。经常集训让两人有机会在一起,认识两周以后,燕子对阿远渐生情愫,而阿远还蒙在鼓里,浑然不觉。终于有一天,在结束训练后,几个人坐在学校体育室的跳高垫子上休息,燕子紧紧挨着阿远坐着喝水,娇喘吁吁吐气如兰。柔软的海绵垫子和女孩的气息让阿远马上五迷三道。其他同学和阿远一样还是人事不懂的小雏,一帮人在垫子上疯狂打闹,脏话不绝。
阿远正要保持清醒向旁边挪一挪,燕子突然开口:“阿远,如果我说我想‘倒磕’你,你信吗?”(倒磕是那时流行的词,“磕”是指男孩追女孩,“倒磕”则是指女孩追男孩。)
阿远被这样“通俗”的表白惊得手脚冰凉,不知如何回答,稍加思索,阿远非常不解风情地说:“我信。”
不过,这样的答案已经让燕子很满意,燕子嫣然一笑,阿远也僵硬地笑了一下,半晌无语。
再后来就是一天下午没有课,两人约好去铁路边“压镚”。压镚就是把一分、二分和五分的硬币放到铁轨上,等火车碾过去之后再拣出来,硬币已经被挤压成薄薄的铝片。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无聊的游戏。
那天阳光强烈,两人在铁轨边玩了一会儿,觉得索然无趣,燕子提议到处走走。两人像80年代电影中刚刚经人介绍见面的青年男女,尴尬、机械却又强自镇定沿着铁轨旁的小路向前走。
“拉手了吗?拉手了吗?”我有点着急,催促阿远快讲。
“不光拉手,我还摸她来着。你听着听着,激动什么?”
“****……”我惊呼!
那天天气巨热,阿远的塑料凉鞋里进了沙土,加上汗水很快和了泥,阿远越走越别扭,燕子也觉得一点没有想象中的浪漫。终于,前面出现了一条小溪(真他妈太巧了,但确实如此),水深刚没脚踝。两人欢快地走进水里,清凉的感受让燕子对浪漫还有一点信心。头顶上方是通火车的高架钢桥,脚下是潺潺的小河,不时有小蝌蚪在脚上碰来碰去。周围的藤蔓水草和岸边的灌木郁郁青青,还有一轮美丽的……大太阳。
突然,燕子对阿远说了一句话:“我想……”正好一列火车从正上方飞驰而过,淹没了所有声音。
两人又对喊了几句,当然什么也听不到。
燕子突然扑上来,手扶着阿远的肩,结结实实地在阿远的嘴上亲了一下,阿远的脑子“轰”的一下,然后一片空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献出了自己的初吻。后来,燕子还主动要求阿远摸一摸自己的腿,阿远哆哆嗦嗦地摸了两下,当然是隔着裤子摸的,不过在当时也算很牛逼了。
“哎,感觉好吗,好吗?,****,你太牛逼了,特软吧?”我对阿远的风流经历羡慕极了。
“那么回事儿。”阿远轻蔑地说。
(3)
第二天中午,小伟真的到学校来找我了。
六子退学后也经常到学校来,他每次进校园都是一大群人,耀武扬威,有时是来找我们玩,但大多数时间是来打人或跟初一小孩儿要钱。小伟最烦他这一点。
那天,小伟坐在校门的马路对面,左臂上裹着厚厚的绷带,旁边有一辆摩托,前面坐着一个长得很妖冶的女孩。小伟远远地大声叫我。我周围的同学有见过小伟的都觉得挺惊讶,问我怎么认识小伟的。我没时间搭理他们,赶紧穿过马路向小伟走过去。
“昨天谢谢你呀。”小伟很文气地笑着,扔过来一根烟。
“没事儿,他们太欺负人,再说我也没帮上什么忙。”我接过烟,小伟帮我点上。
“我第一次看见有人像你这样和痢疾说话,”小伟说,“痢疾跟我没说的,对别人不太相信,爱翻脸,但是人绝对够意思,你以后跟他混一段就知道了。”
“我没事儿,我这人跟谁都能处好。”我心想只要他不打我就不错了,还跟他混?!
我把昨天晚上了解到的打架的起因跟小伟说了一遍。正说着,学校里几个能打的混混都过来和小伟打招呼。寸头也认识小伟,颠颠地跑过来。小伟笑眯眯的把烟分给大家。听完我的话,小伟点了点头:“我昨天问了几个西郊的朋友,他们和你说得差不多。”
小伟搂着我的肩膀,转向其他人:“哎,哥儿几个,这是小哲,我弟弟,在学校里帮我照顾点儿。他有什么不对的事儿先跟我说,就当给我个面子。”
“小伟哥你都说话了,还能有什么事?”答话的正是寸头,一脸谄媚的笑。
“小哲,六子昨晚上送医院了,待会儿我去看看他,你有什么事儿吗?”
“我没事,你先过去,我今天晚上去看他。那这事儿……就这么完了?”我试探着问小伟。
“再说吧,重要的是看六子有没有事,六子没事就算了,再说这次的事他不占理。”
“那你呢?这几刀白砍了?”
“我没事,你甭管了,走了啊。”小伟说着跨上摩托,向我们几个人打了个招呼。
小伟的车一溜烟开走了。
下午,小伟认我当弟弟的事就在校园里传开了,好多人又惊讶又羡慕,一些在学校里混得很开的高年级学生也过来和我打招呼。当时,我一点都没当回事,因为那时我对自己在学校里牛不牛逼一点也不感兴趣,我的全部心思都放在玩篮球和找女朋友上面。安涛和韩越倒是很高兴,极力怂恿我再把初三的寸头揍一顿,他们说:“现在你还怕什么,除了老师,想打谁就打谁。”
六子出院以后在家里养着,我们经常去看他,可是关系反倒比原来疏远了很多,六子看见我没有以前那么贫了,见我们进来就招呼我们抽烟,然后很少说话。六子刚出院的那一阵子,我有时旷课到六子家看电视,后来也不常去了。那时,上课时间家里的电视不敢白天回去看,容易被大院里老妈的眼线——几个退休的老太太发现。
现在的中学生可能想象不到,那时的电视对我们来说是如何新奇而好看。当时最流行的电视节目就是《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一共三辑,播出时间都在上课时间,所以,很多学生都旷课去看,教室的上座率不到80%,也算对我市的中学教育产生过一点小小的冲击。《潮》是一挡音乐节目,主要以MTV为主。那是我们第一次知道MTV这个词,刚开始没听清,反复听了几次才知道是英文M-T-V,有人唱、有人跳舞还有一点模棱两可的故事情节,再配上一点怀旧的黑白画面,真是让我们如痴如醉。小虎队还是新人组合,穿着当时很时髦,现在大部分酒店服务生都常穿着的那种金色坎肩在舞台上边唱边舞,我们则坐在电视前热血沸腾,大声合唱。如今,很多的天王歌后那时还是歌坛新秀,回想起来实在是我在看着他们成长。
风靡一时的《潮》我只看了两辑,后来,六子伤好了,白天经常不在家,所以第三辑也没看成,成了我一个小小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