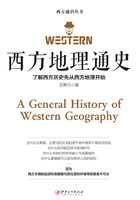[35]一位中国法官可以永久驻守在国际租界内,“根据中国法律审理租界内中国居民间的一切民事和商务诉讼,以及中国人为被告的中外居民间的案件”〔1869年4月20日制定的《上海混合法庭章程》,赫特斯莱特:《条约汇编》第2卷,第129号。见该章程《实施公报》,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163—170页〕。
[36]1867年11月7日文极司脱致阿礼国,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53—55页。
[37]阿礼国的信和恭亲王、文祥关于该问题的照会,见1868年6月19日《北华捷报》。阿礼国的以下判断是正确的:中国保证人们定能履行其条约义务,这一点和其他类似的事实都说明,制定一部中外彼此都能满意的商业法典是可行的。然而,他将中国的习惯法观念等同于英国的不成文法观念,都是全然错误的。二者虽然都不曾编写成法典,但它们是建立在相反的概念基础上的(参看第七章)。
[38]李鸿章提出要授权作为整体的领事团,以审判那些桀骜不驯的外国人。当时在北京的外国公使们坚持,没有一位领事能够逮捕其他国家的侨民(见1864年2月20日、6月30日《北华捷报》)。
[39]见1864年1月9日《北华捷报》。
[40]西华德这样描述阿礼国的意图:“要以某种有效的方式实行调整,以破除目前英、法、美在上海实行的领土主权的伪装”(1866年4月7日西华德致卫三畏,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训令》第1卷,第396—397页)。同时,法国人对修改后的租地章程的指责并没有说服力。他们维护在领事严格控制的自己的租界,并坚持认为,市政府如同不受条约义务约束的寡头政治组织一样,它对中国主权的威胁较之在一位领事统辖下的单一租界远为巨大,〔1866年6月18日德罗伊致伯洛内,见《法国外交事务部外交文件》(1867年)第8期〕。
[41]见1866年8月18日《北华捷报》。
[42]英国条约第二—七款规定,双方互派公使,按西方各国惯例,公使应当受到礼遇。虽然额尔金于1858年10月曾经承诺,在目前情况下英国公使并不坚持要驻节北京,但是后来由于条约的批准必须诉讼于武力,这个承诺被撤销了。1860年《北京条约》第二款确认了驻节权。1861年初,卜鲁斯抵达中国首都,开始了第一次例行的外交使命〔1861年6月6日罗素致卜鲁斯,载《中国事务通信集》(1859—1860年)第116页〕。
[43]“50年代在华欧洲人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一旦我们能够说服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将是治愈我们不得不抱怨的所有病症的灵丹妙药。我们将和皇帝及其朝廷打交道,这样我们就能够迫使那些最顽固的官员接受我们西方的文明了”(密福特:《使馆馆员在北京——书信集》,序言,第44页)。
[44]参看第三章和第十章。
[45]1860年10月21日额尔金致罗素,见《中国事务通讯集》(1859—1860年),第205页;另见1859年6月14日卜鲁斯致马麦斯布尼,载《致卜鲁斯先生通信集》,第8—10页。
[46]1861年1月9日罗素致卜鲁斯,载《中国事务通讯集》(1859—1860年),第16期。
[47]见1861年2月16日《北华捷报》。
[48]《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9卷(1870年),第70页。另见阿礼国:《中华帝国的外交关系》,载《孟买季刊》(1856年4月),第261—275页。威妥玛的观点,见其备忘录(麦里坦版):《威妥玛先生关于修订天津条约的备忘录注》(香港,1871年)。
[49]1869年12月13日克拉伦敦致查理·R.维多利亚主教,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9卷(1870年)。
[50]戈瑞、沙蒙塞特、克拉伦敦,奥特维狄克等人的反传教士的演讲,见《英国议会议事录》第194卷(1869年),第933—946页;第195卷(1869年),第131页;第197卷(1869年),第1797页;第199卷(1870年),第1870—1872页;第200卷(1870年),第71—72页;第205卷(1871年),第562—563页。
[51]1868年5月21日詹美生致阿礼国,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3卷(1869年),第2页。有关福摩萨事件的英国资料见同前;中文资料见《清季教案史料》第1卷,第16—26页。另见第三章。
[52]《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9卷(1870年);第2、3卷(1869年3、7月)。
[53]1868年12月威妥玛备忘录,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附录。
[54]《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9卷(1870年),第10—11页。
[55]阿礼国对上述传教士来信的评论,同上,第29页。
[56]赫德条陈的中文原文,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13—22页。威妥玛条陈的中文原文,见同前,卷40,第24—36页。
[57]1866年4月1日总理衙门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10一12页。
[58]1866年4月15日,刘坤一收到的军机处“字寄”,引自刘的复奏,见同上,卷41,第43页。
[59]同上,卷40,第12—13页。
[60]同上,卷40,第36—37页。
[61]据说1902年皇太后曾对赫德说,她很后悔没有采纳他在19世纪60年代的条陈中所提出的许多建议,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裴丽珠:《赫德爵士传奇》(纽约,1909年),第11页〕。
[62]《北华捷报》讽刺说,牛庄必定是“一个小小的商人乐园”。因为那里的商人们曾有这样的报告:“这里干戈不起,一片宁静,河道设有很好的浮标;入口处的照明设备也很完善;引水员们个个沉着熟练;非法勒索在这里不知为何物;道台办事公正且良善。”
[63]见1868年1月13日《北华捷报》。
[64]1867年11月28日《贾丁、马则逊及其公司请愿书》,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4卷(1870年),第29—31页。
[65]关于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香港的商人最为极端;另一些团体则愿意通过调停来解决问题,以获得在内地的某些有限权利。
[66]1868年2月17日阿礼国致英国驻华各领事公函,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125—130页。原文及评论,见1868年5月4日《北华捷报》。
[67]1867年7月5日《北华捷报》,转载《每日评论》。
[68]1867年8月16日山嘉利致阿礼国,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8页。是时山嘉利得到了德尔比内阁多数成员的支持。
[69]1867年6月16日总理衙门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9,第5—7页。
[70]1867年10月12日总理衙门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第24—28页。
[7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第28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211,第32—34页。
[72]条说原文,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第29—30页。
[73]1868年7月卫三畏致西沃德,载《美国对外关系》(1868年)第1部分,第516—521页。
[74]在蒲安臣使团出使期间,恭亲王曾巧妙地暗示阿礼国:他宁可信赖阿礼国处理中国投诉所具有的公正的判断力,而不愿指令中国使节向英国本国政府或其他外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阿礼国评论说:“很显然,他们在外交教育方面正获得进步。”他进而指出,中国对外派驻使节,“很可能是为抑制任何外国代表或外国政府的不公正行为提供了它所可能获得的最好保证”。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3卷(1869年),第33页、36页〕。
[7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24—25页;卷13,第12页。
[76]1866年1月《帝国政局》,见《法国外交事务部外交文件》(1866年),第228页。
[77]按《北华捷报》说法,“蒲安臣条约”是“正式的但浮夸的和微不足道的”;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使团,现在“由于其首席官员即蒲安臣本人的不明智的主张,正走向毁灭之途”(1868年9月11日、19日)。
在华商人主要的批评意见,是认为蒲安臣正在使有关中国乐于改革的危险幻觉永久化〔1870年1月21日香港商会致克拉伦敦,载《中国》第6卷(1870年),第3号;另见米切:《在华的英国人》第2卷,第212页。〕
以下是反对蒲安臣的极端的观点:“‘蒲安臣使团’最初是由总理衙门的心腹顾问赫德先生提出的,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迷惑欧洲,为中国政府准备以武力抗拒西方的正当要求赢得时间。它极力怂恿中国借助西方进步和文明的精神,并通过伤害英国为中国谋取商业与财政利益的方式,来强化中国僵滞的政策。‘蒲安臣使团’从它一成立,便明显地表现出了一场阴谋反对西方各国的主权尊严和国家独立的外交骗局所具有的特征”(方根拔:《蒲安臣使节真相》,第175页)。
[78]《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40、98页。
[79]“〔中国人的折衷的态度〕足以回答这样一些人:最近他们声称中国将会利用西方各国的对它有利的行为,限制而不是扩大外国人的权益。此种令人满意的结果只是在中国政府充分理解了与美国签订的条约;以及英国政府的行为,即反对其国民的侵略精神——克拉伦敦勋爵严厉谴责了某些在华英国官员在扬州、汕头和尔福摩萨的不公正行为——的全部意义之后,才出现的”(1870年1月4日蒲安臣致璧斯玛,载《美国议会档案》,《中国评论》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