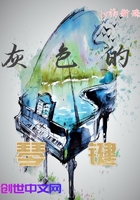顾颉刚从事史学研究70年,在史学界可以说是桃李满门。是他的学术生涯,得益于图书馆甚多。
从小就爱读书目
顾颉刚从小喜欢博览群书,好看杂书,家中的书不满足,还常赴苏州玄妙观市场上看书,久之,就对书目发生了兴趣。他后来回忆:“为的是看了书目就可以知道哪一方面有我所需要的书了”。
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每月免费赠送一册《图书目录》,他是每期必读;报纸上刊登的各家书店出版的新书目录,看了后还把它剪下来贴在本本上保存;还常看以前木刻的书目,其中有三部书目,乃是经常查阅的工具书,那就是《四库提要》、《汇刻书目》和《书目答问》。通过这些书目的指引,他也就学会了需要什么书就到那里去找。当时苏州城里还没有一家图书馆。他后来说:“我所以知道这许多书,就是从这三部书目中看到的。有时我从苏州到上海去,那里《国粹学报》馆中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我就不放过了”。
顾颉刚进北京大学的第二年,就根据《书目答问》末尾的《皇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编成了一部《清代著述考》。
“我最适宜的事情便是图书馆”
顾颉刚北大毕业后的第一个职业便是在该校图书馆担任中文编目员。他在与妻子信中讲到对未来职业选择时说:“我想到我最适宜的事情,便是图书馆。”1920年6月,他上任后与馆主任李大钊讨论了图书馆中文书目的改编事宜,作《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和《图表编目意见书》。认为:“我们校里,图书馆办了十几年,却从来没有一部好的目录。虽然有了十七八万册书,不便参考,也得不到益处。”“我的意思,第一年把所有的丛书拆散,以一种为一单位,先想编书名目录及著者目录二种,用笔画的繁简为次序。此后再编‘待访书目’。‘学派书目’及‘分类书目’等。”此项全面整顿北大图书馆目录系统的计划因时间和经费的关系最终没能够实施。10月,又担任了清查外文书籍、重编西文目录的工作。
顾颉刚在学生时代就是图书馆的常客,对于图书馆的工作常有可行性意见上书校长或图书馆主任。他的建议《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还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也多为学校采纳。他后来回忆说:“我个人对于图书馆最有兴趣,因此,凡是图书馆中一切呆滞停顿的现象,都被我指摘出来,而一经我提出,馆中立刻改变了样子。”1921年,顾颉刚兼任国文学的参考阅览室工作。翌年,着手设立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并从事检书和编目等具体工作。
顾颉刚少年时读书,无意中读到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从而对考订的书报感到兴趣,可是这本书只有寥寥数十页,直到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才找到姚的《九经通论》。在这同时,他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编制了两套对他日后学术生涯起了作用的书目,即《伪书疑书目》和《中国目录书目》。编目,是他能出新见解、新课题的基础工作之一。
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聘顾颉刚前去任教。顾颉刚趁此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书,4个月共购书约12万册。丰富了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他后来评论中山大学图书馆道:“广州中山经费充足而书籍颇少,现派我任购书之事,这件事于我极高兴做的,因为借此可以取得许多材料。”
1927年10月,顾颉刚完成购书任务后,出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又担任该校图书馆委员会委员、图书馆旧书整理部主任,同时主编《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这期间还写了《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所列入要搜集的图书资料有16大类。杜定友在此计划书的《书后》中说:“先生拟的16大类,已经把所有的材料包括殆尽,更不容有所添减。”顾廷龙后来在回忆顾颉刚时也说:“我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购事将五十年,即循此途径为收购目标,颇得文史学者称便。”由此可见他那渊博的知识在图书馆藏书建设上的反映。整个中国图书的范畴,均在其胸中了。
多次无偿地捐书
顾颉刚从事图书馆访书、编目、整理业务经年、也善于利用图书馆。他还把自己数十年收集到的图书,先后捐献给了图书馆。
1945年12月,他向当时的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呈上一份报告,详陈自己的图书、文物和文稿的损失情况。1946年2月,自重庆飞抵北平,查寻劫后所余藏书,并嘱人刻印两方:“颉刚劫后所得”、“晚成堂劫余书”。不久,他赴天津寻找当年存于银行里的文稿,打开木箱,凡日记、笔记、游记、信稿等皆“一一呈于目前,热泪夺眶,若获亡子”。原来,当年抗战形势学张时,是他的从叔、小于他十一岁的顾廷龙为他安顿了书物,一部分安置在燕京大学校园内,一部分存放于城中禹贡学会等处所,而比较整齐的文稿,日记笔记等就带到天津,存人中国银行仓库。及太平洋事变后,日本人进入租界,原安置在燕大的藏书被悉数捆载而去,寄存在天津中国银行的文稿竟被拍卖。幸好拍卖之事被他的好友辜元群得知,为之少数收赎,改存浙江兴业银行内,于抗战胜利后方才得以重览旧物。
1946年5月,顾颉刚回到故乡苏州,在家中整理其父所遗留的图书古物。同年,他任复旦大学教授、福德图书馆馆长、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并在复旦图书馆博物馆系教授“中国目录学”。
1947年,顾颉刚在抗战时期于西南一带收集的图书资料被运回苏州。1949年3月,他将其中凡有史料价值者,捐与合众图书馆。这类近代史料有两万多册。1953年1月,又将苏州家藏碑帖及报刊(以抗战时内地出版者为主)等赠与合众图书馆,此次并将1938年毛泽东寄赠的《论持久战》一书加上题跋,亦赠与该馆。
书至合众图书馆后,顾廷龙即为主编《顾颉刚先生书目》,计得经史子集、子部丛书共860部,共5000余册。
捐书后顾颉刚仍继续搜书,1954年曾去苏州曹元弼(叔彦)家购书5000册,同年赴北京任职时打点行李,仅藏书即达225箱,如平均以400册计,又有9万册矣。
1980年年底,顾颉刚在北京逝世,其家属遵照他生前关于“藏书不分散”的遗愿,将藏书6万余册捐献给了中国社科院图书馆。
(宋路霞)
链接顾颉刚在重庆时写有小册子《晋文公》,梁实秋很欣赏,说:“此为极生动之通俗读物,读之亦觉盎然有味”。此说即为出版该书的书局,用于刊登广告。顾颉刚的《古史辨序》长达10万字。自序内容有童年的回忆、治学的经历等。周作人称它是“很有趣的自叙”。该作被选入《中国文学大系》散文一集。1922年顾颉刚为《教育月刊》作《对于苏州图书馆的一个计划》,指出:“设立图书馆的目的,是给看书的人以便利,不是单单请几个人去守着一座锁闲森严的书库”。
余思顾颉刚在抗战前将其书屋题为“晚成堂”,有何深刻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