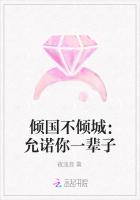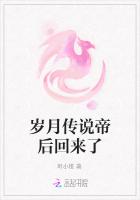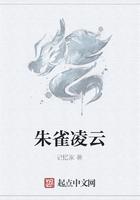为屈原守灵的诗人
乐平里是一个风景绝秀的山间小盆地,盆地的中间是一座山丘,山丘之上是春花秋草和青翠的橘树,这个山丘就是三闾八景之一——伏虎降钟,人们习惯地称之为“钟堡”。“钟堡”上是一座屈原庙,它坐北朝南,飞檐高翘,雄峻壮美。屈原庙屹立于钟堡之上,就像屈原端戴的冠冕。
屈原庙里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屈原(塑像),另一个就是为屈原守灵的老人徐正端。徐正端住在庙里右侧的一间简陋的厢房里。他支了一张铺,立了一个灶,带了一柜子书,就这样安安静静地住下来,这一住恍惚间就有了几十年光景。
徐正端住在庙里,陪伴屈原的孤寂,守护伟大的诗魂。每天早晨当浓浓的草莓汁一样的太阳从窗格子里钻进来的时候,徐正端就起床擦一把脸,走进天井,数一阵空中飘浮的浪漫彩云,然后打开大厅的门锁,开始为洁白的屈原除尘。本来屈原是傲世独立、洁白无瑕的诗人,是不需除尘的,但因为世俗的尘埃总是不会饶过任何一个人,所以徐正端老人便将为屈原除尘、保持洁白的躯体定为每天最主要的功课,他要让这位伟大的诗人放射出永久的、洁白的光芒,让游人瞻仰。
除尘之前,他在诗人的面前,虔诚地点燃一炷香,让这炷香梦幻般悠悠地袅起一缕一缕的诗意之后,便轻拂慢抹,用温暖的孝心擦拭屈原皮肤上的微尘。诗祖啊,这时你的感觉是不是洁白的雪在飘落?是不是有一些细得不能再细的太阳刷在你的身上?
静静地为屈原除尘,默默地在导师面前诵吟《离骚》,这是徐正端最幸福的时刻。徐正端已离不开屈原庙,离不开屈原。这样的幸福时刻他要天天拥有。
除了为屈原除尘,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比如打扫庙宇。他把庙内庙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要把生活中的一些世俗的事情扫到一边,腾出干净的地方让宾客坐下,让洁白的雪落下。
比如培植橘树。屈原不是写过一首诗叫《橘颂》吗?这首诗是颂家乡的橘呢!他不能对橘树马虎,要用尽心思去剪枝、去施肥、去呵护它累累的果实,让这些橘树的根深深地扎在诗的沃土里。他还要去培植兰草兰花,这是屈原最心仪的花草,他也很疼爱,要浇水要去杂草,还要把屈原写兰草的诗句背一背。
比如联络骚坛诗友。老人想念哪位诗友了,就写一首七律或绝句或骚体诗,以表达想念之情,送给友人。诗友的和诗,他耐心玩味,珍藏起来,用毛笔又誊写一遍,编入诗丛。屈原庙是骚坛的笔会中心,老人则是骚坛诗友的轴心,一切联络都自老人始,也自老人终。
徐正端永远不忘一年中的两个日期,一是正月初七屈原的生日,再就是五月初五骚坛笔会诗人节。正月初七,徐正端总要买来一挂鞭炮,在庙里放上一阵子,在屈原的生日里与屈原共度良宵。屈原的生日乐平里的人记得,他记得。五月初五端午节,是屈原投江殉难的日子,同时也是乐平里泥巴腿子诗人们到庙里聚会吟诗的日子。这一天,徐正端要早早起床,在厨房里准备茶饮和酒馔,以迎迓他的诗友们。他看到敞着衣衫、卷着裤管,大口大口吧咂旱烟的诗友们陆陆续续从毛狗子道上走来的时候,就兴奋不已。这种兴奋并不是因为他和这些诗友曾在一起耙过田、栽过橘、砍过柴禾,而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写诗这一特殊的志趣,是“诗”把他和这些农民兄弟紧紧粘在一起。诗会结束后,徐正端就把骚坛诗友们的诗留下来,用毛笔楷书仔细誊写,然后装订成册,他整理的《吊屈原专集》有一千多首。这些专集,每个字、每个标点都凝聚了他的心血。
徐正端自己也写诗。他主要写骚体,他写的骚体诗真是韵味十足呢!
时维五月兮,节届端阳。
蒲艾高悬兮,驱邪迎祥。
楚天默哀兮,素冠素裳。
竞渡龙舟兮,吊古忠良。
争投角黍兮,遍撒江湘。
饫餐水簇兮,圣体勿伤。
年年此日兮,大地茫茫。
骚人墨客兮,萃聚一堂。
笔呼墨号兮,洒洒篇章。
追溯高节兮,爱国之光。
孤忠夙愿兮,美政兴邦。
今世今朝兮,祈公鉴赏。
在庙里读诗与写诗都是非常冷清的事业,尤其是冬天,雪降落到诗人的生活中,诗人就一直在倾听落雪的声音,偶尔远眺一番被雪覆盖的村庄和田野,便又回到暗淡无光的炉边。在炉上烤几个红薯和土豆,黑凳上放上一小碟腌菜和一小碟花生,便悠然喝酒。喝酒时除琢磨一两句诗外,也想一些人和一些事。想得深远的时候,眼角里冷不丁地落下一两滴浊泪来,是不是谭光沛、杜青山两位诗友逝去的身影又在他心里翻滚了?是不是骚坛将面临后继无人的景况令他忧郁和心碎?
尽管庙里是如此的单调乏味和冷清枯寂,但这位八十多岁的老诗人,好像看不出要走的迹象。还在积极地准备柴禾,还是很有规律地开关庙门,也信心十足地观察着日月。他可能最终要老死在这里。
守庙人的心事
徐正端住在屈原庙里,扫庙、写诗、为屈原守灵。这是他为自己晚年选择的事业。
前些年,他悠然自得。天亮打开庙门,傍晚关上庙门,一日之间还做些跑进跑出、迎往送来、抄抄写写的事儿。他不认为这很无聊,他觉得充实,惬意,也是最乐意的事情。有人说:“像个老和尚。”他也懒得去辩驳。
这几年,他有些忧郁了。仅仅把个庙门守住有什么用啊?他要守住的是屈原的灵,是屈原的魂。徐正端最大的心思,就是要将屈原的思想在乐平里传下去。自己已至耄耋,是要入土的人了,还能守几年庙呢?写诗还能写几年呢?灵气已经飞逝,才思也已枯竭,说乌呼哀哉,就是一口气接不上来或眨一下眼睛的事儿。但是屈原的诗作要传下去啊,继承屈子遗风的骚坛要传下去啊!这是大事啊,不能马虎的。要传下去,就是青年人的事了,这让徐正端感到忧虑。当务之急,是要拉携几个青年娃子,传递骚坛的香火。
他的重点不在读诗写诗了,也不是整理骚坛诗集了,而是在寻寻觅觅,找寻能读会写的好苗子。这是火烧眉毛的事儿。
只要是棵苗子,徐老就会去精心地呵护他、浇灌他、亲近他,教他读屈原读楚辞,教他写骚体诗、格律诗。但是现实让他沮丧。一个女孩子,写诗填词已入门,也能在端午诗会上登台亮相了,却走了,到北京去做了保姆。几个后生,徐老手把手地教,都有了长进,写出的诗像模像样了,但也难耐写诗的寂寞和生活的贫困,鸟儿一样扑楞楞飞了。这让徐正端极度的落寞和沮丧。心血白费了!要教一个人由不能读懂《离骚》,到能读会背,由不能写诗到会写,由平平仄仄到上下去入,不知要费多少口舌、耗多少脑筋、熬多少夜。煮熟的鸭子都飞了,他的心是多痛啊!当然,他也明白,乐平里穷,农民最需要的还是糊一口嘴!穿一身衣,需要的还不是写诗,也不是研究屈原。如果他们关心屈原的话,不是关心屈原的本身,也不是屈原的“求索精神”。“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精神世界离他们还是很远很远的。他们真正琢磨的,是屈原故里的旅游会不会火热,乐平里的大规模开发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是说屈原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实在的东西。如果这一切都是虚幻的,青年人还是会走的,会毫不犹豫地丢下楚辞和写的诗稿,会撇下徐老头子的。诗毕竟换不来粮食,更不能鼓起腰包。这些和徐正端的想法都是相去甚远的。
徐正端,心仍然不死。他去叩小学和中学的门了,找校长商量在学校开办“楚辞课”,在老师中结交诗友,在学生里找好苗苗,这是他残存的希望。校长和老师们也还是热情的,也经常请他去讲楚辞讲屈原,也乐意让学生到庙里去听一听、看一看。这让徐正端宽心,打心窝子里高兴。后来,学校对开办“楚辞课”也渐渐冷了,停了。因为楚辞课不能给学校带来教学成绩,也不能给学生带来中考分数,学校得围绕考试的指挥棒转,不转不行,不转学生就得吃亏,误了学生的前程,谁担得了这个责任?徐老又茫然了。如果不找几棵好苗子,骚坛将会倾覆,诗也将是一片废弃的旷地,再也不是一片绿洲了。徐正端是真正在忧虑骚坛的事了。
徐正端在离屈原庙几十步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还买来一些长条板凳,办起了“离骚径院”,讲屈原的作品、屈原的故事,讲三闾八景的传说,也讲骚坛的精神。“离骚径院”是极其简陋的,不像个讲课的地方,但他讲这些东西却是滔滔不绝的。有时学生来听,有时游客来听。只要有人来听,徐正端就来劲、兴奋,口若悬河。他找到了寄托。
“离骚径院”热闹了一阵子,又冷冷清清了。好长时间没有人光临。不过这种景况老徐早就预料到了。
是把“离骚径院”的门关上还是一直就这样开着呢?徐正端有些犹豫了。
小孙子开始读小学,徐正端牵着他的手常在乐平里的沟壑里转,在田畦上遛达,给他讲屈原小时候的故事,背屈原的诗给他听,也常把他留在庙里做伴儿。他对小孙子说:“上不了大学就在村子里待着啊!”
每天关庙门的时候,徐正端总要坐在高高的门坎上看一阵日落,直到另一边升一个弯月。他想:“我死了以后,谁来守庙呢?我的孙子会来吗?”
献给屈原的礼物
屈原庙是座空庙。
一堂一厅,一个天井,两个厢房。除大堂里树立着屈原的塑像外,其余都没有内容。徐正端住进庙里时,觉得不好意思。住进来就是一个家了,这个家空落落的,怎样待人接物?
徐正端是屈原村乐平里人,是村里的小学教师。六十岁退休。退休的当天就进了这座庙,守护屈原和这座庙宇。
其实屈原庙也并不完全是座空庙。晴朗的天气,一炷炷阳光照进来,天井、大堂、大厅和厢房金光闪闪,洁白的屈原塑像也好像抹上了一层金粉,在大堂之上熠熠生辉,这种神韵,显现的是战国时一个志得意满的屈原。阴雨霏霏时,烟雾从大门从天井从格子小窗一起涌入,大庙像一个胀满的气球,雾霭朦胧,屈原像在阴霾中时隐时现,这样的幻影,酷似历史变幻的厚重云块,车马啸啸、硝烟滚滚,屈原振臂、呐喊、问天,他站在时代的尖端拨云驱雾。屈原庙挤得最满的时候是诗会,熙熙攘攘,诗的气息充盈,无处不是飘逸的韵律和平仄。当然,屈原庙里更多的时候是春天飘来的花絮,夏天飞来的蚊虫,秋天弥漫的谷香,冬天落下的雪花。
屈原庙里住进了一个鲜活的人物后,冷清、空洞的屈原庙活泛起来,呆板的屈原塑像生动起来,庙堂内外空灵起来。庙门开与关的吱吱声响传到村头了,比鸡鸣的声音还尖利。炊烟袅袅绕绕地浮起来了,像是插在庙宇上的旗幡。脚步在每个角落踏动,铿铿锵锵,也惊醒了一系列的细小生命。还有了书卷气,墨香盈室、吟诵不断。一个人物的活动是能带动一切的。庙外也进入了四季的正轨,花草该枯时枯,该荣时荣,树木该零落时零落,该繁茂时繁茂。有人能看管这些花红柳绿,收拾残枝败叶,是不一样的。人给这些生命带来更加旺盛的活力。
徐正端自住了进来,就打算不再搬出去,以后几十年的光阴就在这里度过吧!把一切献给这座小庙,献给屈原。他将一颗世俗的心收拢、澄清,静静地放进庙里。过着冷清、孤寂的生活。不是苦读楚辞,就是搜索枯肠写怀念屈原歌颂屈原的诗。他的生命简洁到只剩下关于屈原庙和屈原的事情。
他接待三三两两的游客,殷勤讲述屈原的诗篇和事迹。曾经来了一位博士,和徐老谈论“屈原否定论”,一时徐正端勃然变色,怒不可遏。屈原就出生在我们村里,怎么可以否定?博士没想到徐正端反应是这样义愤填膺,顿时噤若寒蝉,再不理论。徐正端是屈原庙里的守护神,是屈原最忠诚的卫士。他不能让任何人玷污屈原,也不让任何人否定屈原。屈原庙有了徐正端这个人,是屈原的福气,他是献给屈原的礼物呢!
我去庙里看徐正端的时候,他已经待了二十年,八十高龄,头发稀落花白,眼球浑浊目光暗淡。但一说到屈原,他的思维清晰缜密,没有半句废话。他炒了几个菜,请我喝酒。一个平时不常喝酒的人,突然邀人喝酒,兴致极浓,心中肯定有什么话题。喝着喝着,徐正端悲从中来,感觉大限不久将至一般。对我吐露了心思:人已八十,离天远,离地近,守这庙也守不到几个时日了,一生清贫,仅两万多块钱的积蓄,想用这些给庙里留下点什么。我一时无语,默默喝酒。
他退休后的工资很低,老婆也是个农民,儿孙绕膝,这两万多块钱不知是怎样积存下来的。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颈椎、腰椎也有毛病,需要钱。
他要用这一生的积蓄去做什么?
他已着手去做一件事情。
先花了几个月的光阴,用楷书将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二十五首诗歌书写下来,然后请人在外县拖回一车石料,用半年的时间请匠人们铭刻,打成一块块石碑,将诗碑镶嵌在屈原庙的大堂,还买回一块块大玻璃将这些碑罩住,让诗碑永远陪伴着诗人。碑林环绕着屈原塑像,就像忠实的守护者。屈原低头沉吟,迎风徐步。这些碑林就像书简,一一翻开。千古诗篇焕发出光辉。一座空庙顿时变得阔大而充盈。徐正端完成了这桩大事,感觉像完成了整个人生。这可能是他献给屈原的最后的礼物。
每次我走进这座庙,都要在诗碑前踱来踱去走两趟,透过玻璃,诵读屈原的诗句,屈原的忧愤、高洁感染着我,徐正端的义举也感动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