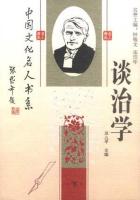因此,义务的概念,客观地说,在行动方面,要求符合于法则,而主观地说,在行动的格言方面,则要求:尊敬法则将是“意志所依以为这法则所决定”的那惟一模式。而“依照义务”而行的意识与“由义务”而行,即“由尊敬法则”而行的意识问的区别即基于上句所说。“依照义务而行”,纵使爱好已成为意志的决定原则,它也是可能的;但是“由义务而行”,或道德价值,则只能置于此,即:行动作成是由义务而作成,即是说,只为法则之故而作成。
在一切道德判断中,以极度的精确性或严格性去注意一切格言的主观原则,这样,则一切行动的道德性可以置于“由义务而行”以及由尊敬法则而行,而不是由对于那“行动所要去产生”的东西的“喜爱或爱好而行”的必然性中。就人以及一切被造的理性存有而言,道德的必然性便是强制,就是说,是责成,而每一基于这必然性上的行动是要被思议为是一义务,而不是被思议为是一种属于我们自愿的,那先在的、早已喜悦于我们者,或是好像要喜悦于我们者是我们能把行动没有尊敬法则而即能作成之,我们自己,好像独立不依神体一样,可进而具有意志的神圣性,通过我们的意志与纯粹道德法则的不可争辨的一致而具有意志的这种神圣性,这纯粹的道德法则好像是要成为我们自己的本性的一部分,而且决不会被摇动。
道德法则对一圆满的存有的意志来说,事实上,是一神圣性的法则,但是对每一有限的理性存有来说,则是一义务的法则,即道德强制的法则,以及此存有的行动的决定的法则(此存有的行动的决定是通过尊敬这法则以及崇敬此存有的义务而成的决定,道德法则就是关于此存有的行动之如此决定成的法则)。没有其他主观原则必须被预定为一动力,因为不然的话,虽然这行动或偶然发生或出现,因为它不是由义务而行,(只是依照义务而行),所以这(去作这行动的)意向却并不是道德的,而正是这意向恰当地说才是在这立法中成为问题的事。
由爱人以及由一同情的善意而去对人们作善事,或由爱秩序而去作正义的事,这自然是一种十分美好的事。但是,当我们以幻想式的骄傲,像志愿军那样,假想去把我们自己置于义务的思想之上,而且好像我们是独立不依于命令似的,只出于我们自己的快乐意愿去作那 “我们认为不需要命令去作”的事,上面所说的“由爱人以及由一同情的善意而去对人作善事”,这不是我们的行为真正道德格言,即,适合于我们在理性的存有间作为人的地位的真正道德格言。
我们是处于理性的训练之下的,而在一切我们的格言之中,我们必不要忘记我们之隶属于这理性的训练,也不要从这理性的训练中撤销任何事,或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专断而减低或忽视法则的威权,以至于去把意志的决定原则置于任何其他处,而不置于法则本身中,也不置于尊敬法则中。义务与责成是我们所必须给与“我们之对于道德法则的关系”的惟一名字。我们实是道德王国的立法分子;但是我们又是这王国中的公民,而不是统治者,而去把我们是为被造物的卑微地位弄错了,而且专横地去否决道德法则的威权,这在精神上便早已是背叛了这道德法则,纵然这法则文貌是被充尽了
“爱上帝越过一切,爱邻人如爱你自己”像这样的命令可能是完全与以上所说的相契合的。
因为当作一命令看,它需要尊敬一个法则,即“命令你去爱”的一个法则,此法则不是把爱留给我们自己的随意的选择,爱上帝,若视作是一种爱好,这却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不是感取的一个对象。朝向人而发这爱好的爱,无疑是可能的。但这却不能被命令,因为依命令(感性地)去喜爱任何人,这不是在“任何人”的力量之中的。因此,那只是实践的爱它才是一切法则的精髓,从这个意义上说“去爱上帝”就是意谓:愿意去实行他的诫命;“去爱一个人的邻居”意谓:愿意去实践对于邻居的一切义务。但是这命令不能命令我们去拥有这种习性,只能命令我们去努力追求。因为命令你喜欢去作某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如果我们早已知道我们所不得不去作的是什么,而且进而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喜欢去作它,则一个命令必完全是不需要的;而如果我们去作它,不是情愿地去作它,只是出自于对法则尊敬,那么,命令,必直接与它所命令的习性相对抗。因此,那法则,就像福音书中的那一切道德的箴言,即展示这道德习性于极其圆满之境,在这极其圆满之境中,这种道德的习性,自其为一“神圣理想”而看它,它不是可为任何被造物所能得到的,但它却是我们要努力去求接近的一个模型。
事实上,如果一个理性的被造物实曾达到这一点,即:他彻头彻尾喜欢去履行一切道德法则,这必意谓在他身上,不存有任何“足以引诱他去违背道德法则”的欲望,甚至这样一个欲望的可能也不存有;因为要去克服这样一个欲望,这主体总赔上某种牺牲,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所不十分喜欢去作”的某事总需要有自我强迫,而也没有一个被造物能达到“彻头彻尾喜欢去实行一切道德法则”这种道德习性的阶段。由于他是一个被造物,是有依待的,所以他从不能完全脱离他的欲望与爱好,而因为这些欲望与爱好都基于物理的原因,所以它们从不能以其自身即与道德法则相一致,这道德法则的来源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这些欲望与爱好使“去把一个人的格言的‘心灵意向’基于道德的责成上,不基于早已有之的爱好上,基于尊敬上,而不基于喜爱上”这一点成为必然的,纵然如此,此后者即喜爱法则也必须是他的努力的方向,但却是不可得到的目标。因为在“我们所高度尊崇的东西,而因为意识到我们的弱点的原因,却又是我们所高度恐惧的东西”的情形中,“满足于这所尊敬与所恐惧的东西”的满足之更加容易,必把这最可尊敬的戒惧(敬畏)变成爱好,把尊敬变成喜爱:这种变成爱好,变成喜爱,至少也应是“忠于法则”的一种习性的圆满,如果“去达到这种习性的圆满”对于一被造物真是可能的时。
以上的反省尚不太重在想去理清所引的福音书中的命令,以便去阻止关于“爱上帝”方面的宗教的狂热,但勿宁是在想直接就我们对于他人的义务,准确地去界定这道德的习性,并且去抑制,去阻止纯然的道德的狂热,此道德的狂热感染了许多人。人所处的道德阶段是尊敬道德法则。“在服从法则中他所应当去有之”的那习性是从义务去服从它,不是从自发的爱好去服从它,或者说,不是从一种由喜欢与自愿而扬起的努力去服从它;而他总是能够存在于其中的那恰当的道德情况就是德性,即在奋斗中的道德习性,而不是神圣性,那“通过激励为高贵的、庄严的、豪迈的,而被注入于心中”者没有别的,不过就是吼叫的道德的狂热与夸奢的自满自大,通过这种激励,人们被导入于幻像,即:那“构成他们的行动的决定原则”者并不是义务,即,并不是尊敬法则人们遂幻想那些行动从他们身上被期待,并不是从义务而被期待,只是当作纯粹的功绩而被期待。因为在依据这样的一种原则以模仿这样的行为中,不只是他们不曾丝毫充尽了法则的精神,不只是他们使动力成为感性的,而不是道德的,而是在这一种路数里,他们产生了一种徒然无益的、高度飞扬的、幻想的思路,以心的自发的善性来谄媚他们自己,因而忘记了他们的义务,即此义务才是他们所应当想到的,并不是功绩是他们所应当想到的。实在说来,所有的那些行动,自“以伟大的牺牲而作成,而且只为义务之故而作成”的那些行动,可以被称赞为高贵而庄严的,但也只当有一些迹象足以暗示这些行动被作成完全是由于尊敬义务而被作成,而不是从激发起的情感而被作成,它们才可这样被称赞。但是,如果这些行动置于任何人面前,以为须被仿效的范例,则“尊敬义务”必须被用来作为动力,它决不允许我们的徒然无益的以感性的冲动去在功绩性的价值中骄傲。现在,只要我们探求我们将可对于一切值得称赞的行动找到一个义务的法则,此义务法则在命令着,而且它不听任我们去选取那“可以对于我们的爱好为可愉悦的”东西。这是表现那“能给灵魂一道德训练”的东西惟一的道路,因为只有这道路才可容许有坚实的而又准确地界定了的原则。
如果狂热的说,是对于人类理性的限制的有意的越过,则道德的狂热便是对于实践的纯粹理性,置于人类身上的限制的有意的越过,依这限制,纯粹实践理性禁止我们去把正确行为的主观决定原则,置于任何别的东西上,但却不置于法则本身上,或去把那“通过正确行动主观决定原则——道德动力而被带入于格言中”的意向,置于任何别的东西上,但却不置于“尊敬法则”处;而因此禁止,纯粹实践理性命令我们去把义务的思想,取来作为人们中一切道德的最高的、有生命的原则,这义务思想击灭了一切傲慢自大,以及徒然无益的自我贪婪。
如果这意思没有错误,则不但是小说家或热情的教育家甚至是最严格的哲学家,如斯多噶,也曾被带进道德的狂热中,但却未被带进一种清醒而明智的道德训练中,虽然斯多噶的狂热是比较更为英雄气,而小说家以及热情的教育家的狂热则是枯燥乏味,柔弱而无丈夫气;而我们如果没有伪善,那么对于福音书道德教训可以这样说,即:它首先通过它的道德原则纯净性,而同时它的原则适宜于有限存有的限制,把人们的善行置于一种“明显地摆在人们眼前”的义务训练之下,这种义务不允许他们放纵于想像的道德圆满梦想中;而且我们对这也可这样说此自大与自我贪婪两者很易于去错乱人们的限度。
义务!你这庄严而伟大的名字!你这名字并不拥有什么妩媚或谄媚性的东西,但只要求服从,然而你却又不想去通过那“必会引起自然的厌恶或恐怖”的什么威吓性的东西来动摇意志,你只紧握着一个法则,此法则即以其自身找到进入心中之路,而且又得到不情愿的尊敬——这一个法则,在它之前,一切爱好黯淡无光,如聋如哑,纵使这些爱好暗地在反抗它或阻碍它,它们也仍是黯淡无光,如聋如哑:值得称义务这个名字有什么根源?你的这高贵家世,从你的高贵家世而被引生出的一个根,即是“人们所能给与于自己”的惟一价值不可缺少的条件,你这样的高贵家世之根从那里得见?
这根或根源不啻是这样一种力量,即“把人升举在他自己之上”的这样一种力量,此一力量把人连系到一种“只有知性才能思议之”的事物秩序,把人连系到这样一个世界,与此全部感触世界连同在一起的时间中,人经验地可决定的存在与一切目的之总合。这个力量没有别的,不过就是人格性,即是说,不过就是自由与“独立不依于自然机械性”的独立性,但此自由与独立性却又须被看作一个“服从特殊法则,即服从那‘为其自己的理性所给与’的纯粹实践法则”的存有机能;这样,就如属于感触世界的个人,由于其属于智思界,他隶属于他自己的人格性。人,由于属于两个世界,也必须只以敬意来顾看他自己的本性,在关涉于其第二而又是最高的品质中,并且以最高的尊敬来顾看这最高品质法则,这是不须惊异的。
那“依照道德理念而指表对象之价值”的许多表示基于这个根源上。道德法则是神圣的。而人是很不神圣的,但也必须视其自己人格中人性人义为神圣的。在万事万物中,一个人所选取的每一东西,以及一个人有任何力量所能控制的每一个东西,可用来作工具,只有人,以及跟人一起的每一有理性的被造物,是在其自身即是一目的。通过他的自由的自律性,他是神圣的道德法则的义体。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每一意志,甚至每一个人的个人意志,在关联于自己中,它是被限制于“与理性的存有的自律性相契合”这条件的,那就是说,它不是要被隶属于任何一个“不能与法则相一致”的目的的,目的须与相一致的法则可从“被动的主体自己”的意志而生出,依此,此被动的主体从不能被用来只当作工具,但也同时须被用来当作其自身即是一目的。我们甚至很正当地也可以把上句所说的条件归属给神性的意志,就着世界中的各种理性存有,即作为神创造物的各种理性存有,而把这条件归属于神性的意志,因为这条件是基于各种理性存有的人格性上的,只通过这人格性,各种理性存有才能在其自身即是一目的。
这种鼓舞起尊敬的人格性之理念,即“它把我们的本性的庄严置于我们眼前,而同时它又把‘我们的行为的缺乏与它相一致’表示给我们,因而它击灭了我们的自大”这种鼓舞起尊敬的人格性理念,甚至对于最普通的理性也是很自然的,而且也是很容易被观察出的。
甚至每一普通的君子也有时见到:虽通过在其他方面无害的谎言,他可以使他自己脱离不愉快的事,或甚至可以为心爱而又值得受奖的朋友获致某种利益,然而他却避免了这谎言,他之所以避免这谎言,只是为的怕他在自己眼中秘密地轻视他自己:有时还见到这一点吗?
当一个正直的人处在极度困穷中,只要他忽视义务,他就可以避免这种困穷,可是他岂不是通过以下所说的意识而强忍着吗?即:他已在自己的人格中以人性的尊严而维持了“人”义,因此,他没有理由羞辱自己,或去担心或恐惧自我反省,他岂不是通过这意识而强忍着吗?
这种慰藉并非幸福,它甚至不是幸福的一最小部分,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有致此慰藉机缘,甚至或许也没有人愿望一个在这样境况中的生命。但是他活着,而他也不能忍受他在自己眼光中为不值得活着。因此,这种内部的安和,就那“能使生命愉快”的东西说,只是消极的。事实上,它只是避免人格价值方面沉没的危险,它是对于“某种‘完全不同于生命’的东西”的尊敬结果,这某种东西即是“在与之相比较并相对比中,生命连同生命的一切享受显得全无价值”的某种东西。他仍然活着,这只因为“活着”是他的义务,并不是因为他在生活中找到了任何愉快的东西。
以上所说即是纯粹实践理性的真正动力的本性;它没有别的,它不过就是纯粹道德法则本身,因为此道德法则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超感触的存在之庄严而且主观地说,它在“人们也觉识到他们的感触性的存在,以及因此感触性的存在而来的那‘感性地很易感染的本性’的依存性”这样的人们中,产生了对于人们的较高本性的尊敬。
现在,如此多的妩媚以及生活的满足可与这动力相结合,以至于单为此种妩媚与满足之故,甚至是一合理的伊壁鸠鲁派的人之最慎审的选择,也必然会宣称他自己是站在道德行为一边,而同时去把这生活愉快享受景色,连系于那“早已其自身即是充足的”最高动力上,这甚至也是明智的;但是这情形只可当作一种均衡看,也就是对于“恶行在反对面所能去展现之”的吸引、诱惑而起一种均衡作用以抵制之,而不是想去把这真正的动力,即使是这动力最小部分,置于这生活享受景色中,当论及义务时。因为若真是想把这真正的动力置于这景色中,那也就是等于想去染污道德意向在其根源方面纯净性。义务的崇高无所事事于生活的享受;它有它的特殊法则以及它的特殊法庭,虽然义务的崇高与生活享受这两者聚在一起,混合得十分好,就像一对药剂一样,以之给于病人,这从未很容易地被摇动过,然而它们双方不久就要各自分开;如果它们不分开,则义务的崇高将不起作用;虽然物理生命可以在强力方面得到一点什么事,然而道德生命则必不可挽回地枯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