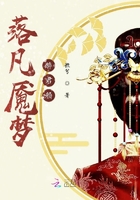栖国国君的话头,倒是跟安国国君一路来的。
小熊不管这些权衡,他就认定了身为军人,为国杀贼占地是本分。身在圣人强行确定的所谓和平盛世,没得正经战打,占座山也是好的。
小刀她们回到白龙山,就见那些官兵东一个、西一个的站着。
小刀低下头:“走吧。”
黑狐刚教训了少章戏班,把他打了一顿,脑袋肿得像个猪头,被自己的裤腰带反绑着浸在河里,淹死算客气的!
他看了小刀的低落表情,更开心,悄悄来跟阿星说风凉话:“哟,那边凤还巢,凤没了,占了一伙什么东西,我看着都怪可怜见的!”
这时候阿星跟洪缣他们已经近海了,黑狐是隐身来说的。特意隐身来说这个?阿星翻个白眼,暗骂:你太闲!
黑狐其实是对阿星好。看白顶天追过阿星,再看小刀是白顶天的儿子,所以嘲弄小刀,是给阿星开心。谁知阿星还不领情。
她就算不领情,眼神也这么冷、这么丽,如华国冬天拿河冰削成的灯,似乎天然就该这么凛滟滟的逼人。
黑狐就发不出火来。
阿星等方便了,剜他一记眼刀:还不回去坐镇?!
黑狐就勾着头回去了,顺便悄悄对阿星道:“给你一件礼物,别客气。”
阿星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是洪缣忽然发现地上有个……
玩具盒子?
盒子是用整只珠母做成的。
洪缣眼神当场就变了。
他识货!
珠母本身并不贵——无非是产珠的蚌,里层也有珠光,拿来将外壳黑灰都打磨尽,只剩下珠光层,也能当装饰品,价值说起来还不如玳瑁。
但这只盒子,保留了整个贝壳的形状,没有任何拼接,也没有任何破损。
这只贝壳有一尺长、七寸宽,珠光层肥而不腻、艳而不妖,比起有的珍珠来都更美,阿鸠也一眼认出,它是青衣贝。
青衣贝珠光层诚然质量好,但很少有大的,而且在磨制时也很容易破损。这一整只青衣贝珠母盒,相当罕见。
打开盒子,便见一个盆景。
芳草如织、花树掩映,花树中有小小红楼,红楼上坐着美丽的少女,楼前一弯流水,照她终日凝眸。
少女轻纱覆面,不见容颜。云轩去采了松针来,以松针挑起面纱。
那面纱只有指甲大,上面刺绣有百鸟朝凤,诸鸟儿身上的羽毛,都纤微可辨。那绣线的粗线,约是一根头发再劈成十三份。
这样的刺绣技术,唯安北的春城才有。而绣线的劈染,非京城宝箴坊不能办。
面纱挑起来,少女眉睫细若蚊足,仍然清丽毕呈。阿星与洪缣等人,一个都不认识她。
这工艺水准未免太高了!像那草地、还有树叶和树皮的处理,体现了安国纺织业最高水准;而花雕之生动明丽,艺术价值远在宝石价值之上;至于象牙雕的塔,玲珑细腻,剔透稳健,恐怕要未城的顶级工匠才做得出来。
它怎么会在这里呢?
阿星立刻想起了黑狐的礼物。
这家伙不知是何居心!
却也只好先收着再说了。
阿星倒是若有所思:“好像……”
“怎么?!”
“像个故事。故事里说有位少姬住在花丛中的红楼上,等着她喜欢的男孩子去接她出来,你们听说过没有?”阿星问。
“嗐!”洪缣与阿鸠人大失所望。这明显没帮助嘛!
“不管怎么说。”洪缣合起盒子。
“送它来的人必有深意,我们先留着吧。”阿鸠抚摸着珠盒。
其实这盒子是安伯少君洪综的未婚妻华媛慧的订婚礼物。
华媛慧新近失踪,于是洪综的亲信,小熊侍卫长,也不得不离京,出现在了这一带。
小熊侍卫长经常哀叹所谓的和平时期,军人的职业变得多么猥琐而悲哀哪。
连*都不如!
*在城邑中骚扰平民,只要别抱着威胁国君及其直系血亲的念头,圣人的诅咒就不会危及他们。而军人呢?稍微动作大点儿、有抱负一点儿,就很容易触发诅咒,搞得出师未捷身先死,死无葬身之地。
在这种有志者受打击、摸鱼的没处罚的情况下,军人*到可耻可怜的地步,最大的功能是替君家充当仪仗,其次是帮商家当保镖,之后包括帮官府镇压一下暴民、帮老爷们追一下逃妾逃奴什么的。有些军人很喜欢接最后一项任务,因为报酬优厚、又没风险,比较起来性价比最高。小熊侍卫长则像害牙疼一般托着腮,把手一挥,坚决拒绝这种侮辱性的委托。
什么?又来一个任务,不是追踪逃妾,是追逃妻?小熊用牙疼姿势一挥手,照例不接。
什么?是秘密任务?即使如此也…伯少君的未婚妻?!那就不一样了!
年后,右夫人终于给洪综订下了妻室。对方是位贵媛,名慧,父系为华国公子,母系为觉国少姬,再往上数八代,有安、栖、画等各国贵族,无直接的平民祖先。血统优良。
华媛慧童年时期有一段在觉国度过,现在也时不时过去度假,跟女君裳关系很好。华国君对她也印象不错,君夫人更是*爱她,特在华君宫殿边赐她一座府邸,好让她进出宫廷更方便。其他城池的不少贵族子女也跟她关系良好。她人际关系过关。
她的父亲,公子达,手底下掌握着大量矿山。华国拳头产业本就是武器、以及由此衍发的一切金属冶炼锻造。公子达名下不知多少炼金炉、打金铺——这里的“金”泛指一切金属。铁铜银金,华国都有丰富矿产。尤其是铁矿,十二城里要推华国为首。
公子达的富裕可想而知。
华媛慧身为公子达的掌上明珠,嫁妆丰富也可想而知。
右夫人当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南边知国的二少姬,地位比华媛慧更高贵,只是母系的血统弱些,嫁妆也比华媛慧少些,也算过得去了,生得倒是比华媛慧更美,人又活泼、肯逗老人开心,而且对洪综明显更为倾心。优缺点彼此对应,右夫人长久在她和华媛慧之间举棋不定。
年后一场宴会,帮助右夫人下定了决心。
那是一场私宴,在座的都是自己人,饮了些春酒,渐渐不拘形迹起来,又是推叶子牌,又是约好拿到鬼牌的人都得说个笑话。
知国那位二少姬,恰拿到鬼牌,毫不忸怩,便笑道:“说起来真有个笑话!便是前些时的事,我们那儿有位御史,跟朋友一起设宴饮酒吃河豚——正好我们那儿河豚初上,肥美得很,就是有毒,非得好厨师把毒收拾干净,不然哪里能吃——蒋御史爱美食,当季弄到尾肥大河豚,又借了个好厨师,当宴做了,跟朋友一起吃。那些客人贪河豚美味,大吃一气,忽然就见一个人倒地口吐白沫,话都说不出来了。一席人都吓坏了。古法粪清能解河豚毒。他们连忙弄了粪清来,给这倒地的灌下。倒地的一时还没有醒。同席人都胆战心惊,说自己也吃过河豚了,迟早也要毒发,不如等没发作前先吃药吧!于是蒋御史为首,都喝了一杯粪清,果然没有出现中毒症状。过了会儿,最先倒地的那个醒来了,一听刚才发生的事,跌足说:‘哎呀!我一直有羊癫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发作。刚才是我发了旧病,不是中河豚毒啊!’”
她声音本就娇啭,南边口音又俏丽,学了那人模样,把最后这句话一抖擞,在座的都大笑!右夫人也笑得不行了,几乎喘不过来气。洪综替她抚背,知国二少姬也在前头照顾右夫人。洪综目光投在她身上,她也正抬睫看洪综。两人离得既近,灯光又正好在她脸上,映得人比花娇,洪综明明情系傅琪,至此也不如心头微微一荡,暗忖:若傅老板肯这样看我一眼,实在是……
右夫人笑声渐歇,望了他们两个一眼,满脸慈祥暖意。
洪综以为,这般一来,婚事就该定给二少姬了。
谁知席散之后,右夫人对洪综道:“儿啊,你若对她们两个实在没好恶,娘作主,就定了华媛如何?”
华国,贵媛,方慧。并非那娇丽动人的南边二少姬。
洪综怔了怔,忙笑道:“实在并无偏倚,全凭母亲决定——然则何以是华媛?儿子还当母亲更中意二少姬。”
右夫人点头叹道:“若以私人交情论,为娘委实偏爱二少姬。能生她这么个女儿,为娘必定高兴。要做媳妇么,依今天席上看,为娘恐怕,她不如华媛更助得上你。”
席上二少姬说得那个笑话,好笑固然好笑,在长辈面前说,却嫌太轻佻了。拿自己城池里御史开涮,又是指名了姓氏,也未免有失国体。
而华媛慧后来也拿到了鬼牌,微一凝思,轻笑道:“也是件实事。就是前几天,我随父亲待客。他们说要钓鱼玩儿。我没那能耐,陪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起来走动,见一个小孩子,乳臭未干,也学大人,举了枝花,像模像样在水边举着呢。我见了好笑,问他:‘你钓什么?’他‘嘘’了一声。我立在旁边一会儿,便见只蝴蝶飞来,盘旋一圈,落在枝上。他这才对我说:‘我拿花儿钓蝴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