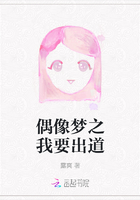历来解“学而”这段语录,都是把这一段语录打成三节。“学而时习之”一节,“有朋自远方来”一节,“人不知而不愠”又一节,各作各解释。最后,这三条都变成了中国人熟知的道德原则,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被无数的中国人随意引用。
在这里,我们的南先生想象力最为丰富,在一个“远”字上大做文章,从空间上的远,说到了时间上的“远”,孔子在五百年后,才得到了董仲舒、汉武帝这样的“知己”,所以孔子是“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按南先生的意思是,有朋自五百年后来,不亦乐乎?
我们真不知这是哪儿跟哪儿!
解孔子的语录,多发挥一点没有什么坏处,但首先要把原文的意思搞懂,不要连原文原句都理解得稀里糊涂,便随意发挥,不着边际,那就惨了。
这一段语录是非常连贯的。第一句,讲“明”、“明德”之学,是我们每日每时都该也必须进行的“习之”,时刻也不会中断的一种生命体验、生命审美。我们会时时刻刻看到我们的生命在奥妙无穷地运动着,创造着各色各样的生命奇迹。这种体验,每个人和每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一个事件,在有的人眼中是啼笑皆非的闹剧,在有的人眼中则可能是崇高高雅的悲剧,在有的人眼中则又可能是嬉笑怒骂的喜剧……正是由于此,才有各自不同的“人”,但大家都在观赏着“宇宙—生命”系统的运动,这运动是我演的,也是我欣赏的。这样的“学”的过程,用老子的话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儒家的话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近道”之观是“无欲”之观,正好得其“妙”,正是其“静”。
“能得”之观是“有欲”之观,正好得其“徼”,正是其“动”。
静动相得,正有生命之妙,玄而又玄,众妙之门。无量生命运动之门,正是我这颗“心”。一切生命活动,正在我“心”上表现着、表演着。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反映”。
既然是如此,有朋自远方来,大家乐一乐,探讨也罢,不探讨也罢,都是十分快乐的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反过来,没有人来,甚至没有人知道我这“心”中的无穷乐趣,我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人不知而愠”。识了道的人,自然而然便有了君子坦荡荡的气质。
一个真正悟得了生命本体的人,无时不是快乐的,时时都在体验着生命的快乐。悟不得的人,便恰恰相反,怎么也快乐不了。
诸君,不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