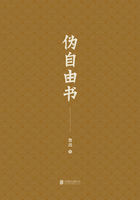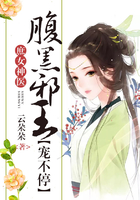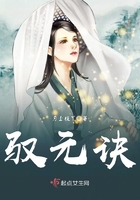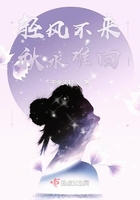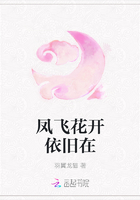子张问崇德、辨惑。
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这一段让南先生一讲,便全是外求的对人处事的道德了。请看南先生是如何讲的:
“‘忠’的意义是直心直肠,心境很直,对人对事绝没有歪曲。另一意义就是非常尽心,不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为国家大事也好,为个人私事也好,绝对尽我的心,尽我的力,乃至赔上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惜,譬如对于思想的信仰绝对忠实,也就是‘忠’。‘信’,我们解释过了,就是自信、信人。对自己要有自信。对人能够厚道,因此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言而有信’的关系。为了使自己的人格更见崇高,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忠’、‘信’。‘徙义’是应该做的事就去做。‘义’者宜也,合情合理应做的去做,就是徙义。”
中国人对这一套太熟悉了,中国古代的忠臣烈士皆是这么做的。如果说有谁不这样做,那就只有孔子一个人。他没有去为鲁国殉葬,鲁国不能用他,他便到各国去找出路。
真正的“忠信”不是外在的道德,如果只是外在的道德,便是愚忠、愚信,便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中国近一千年的衰落,其主要的原因便在这里。
外在的忠信是根本不存在的,让人求外在的“忠信”是骗人骗己的鬼话,真正的忠信就是“不欺骗自己”。人类的“惑”全在于不由自主地欺骗自己。“爱者欲其生”,是有一个“他是我爱的人”的观念先入为主在作怪,正是这个观念骗了人,而忽略了当下的真实,人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被观念歪曲了,推致极端便是“爱者欲其生”。外在的一切事物永远是多重的、复杂的、多义的,只要人们一被观念所骗,为观念而活,那便是“惑”。如何辨惑?非常简单,层层剥离迷惑自己的观念,不许它欺骗自己,不管它是多么美妙、美好的东西。剥到一定的时候,剥不下去了,自认为不受自己的观念欺骗了,自信心起来了,这便是该你去做的。但是,注意,这并不能保证这次的做法就是绝对真理,明天你还可能对此彻底后悔,认为昨天自己欺骗了自己,那就“直下承当”这个错误,坚决改正,绝不掩饰,待你再剥离到自己信心升起时,又是该你去做的,只要自己不怀疑,便直下承当这个责任,“徙义”,毫不含糊地做下去,这便是你该赴之义。
这个过程永无完结,永远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寻找的过程,人的“明明德”,正是在这个发现自我、寻找自我的过程中,逐渐明白的。
客观变我也变,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是“德”,尊崇它便是辨惑。
人无所谓富,也无所谓穷,得到了这样的用心方法,便无异于大富(“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这样做下去,久而久之,一切智、无师智、自然智自然显现,你还不是宇宙中最大的富翁吗?
我们虽这样反复讲,但由于它太简单,未必会有人信,未必会有人如此直下承当。真要懂了这一点,便找到什么叫“良知”了。这“良知”和主观唯心主义毫不搭界,“真心”是没有的,“良知”也是没有的,只有人找寻“真心”、“良知”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真心”,就是“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