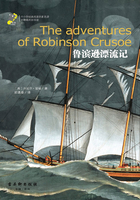邻班的女孩,依旧会丁香一般地飘向我,投下淡淡的、一直渗进眼眸的微笑。只是,她身上的光环,被永久地、永久地遗失在叮某个阴暗的旮旯里。
我第一次被邻班女孩周身散发的光环所迷惑,是在浴室。
那天下午我去得很迟。到浴室的时候,所有的水龙头下都已塞满了人。其实我是个很羞怯的女孩儿,不敢去和别人争什么东西,尤其害怕拥挤。我孤零零地站在浴室门口,看着腾腾的蒸气悄悄地向四周弥散……
这时,我看到有人向我招手。我定了定神,走过去。邻班的女孩微微笑着腾出一块地方。
几点水珠嵌在她的笑靥上,晶莹夺目。或许是灯光被雾气裹着的缘故,她湿漉漉的黑发泛着银亮的光泽,衬着大理石一般光洁的额头,美得炫目。
邻班的女孩就这样走进了我的故事。
那年我刚十六岁,喜欢读一些韵味深长的含蓄诗篇,也常常做些自以为朦胧或不俗的事,譬如将邻班看来成熟的女孩引为知己,尽管我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她的名字。每次,她像丁香花一般轻轻悄悄地飘走,留下一束淡淡的微笑,沁入我的心脾。其时我刚经历了一场大的变故,是个忧郁的、喜欢盲目地依赖一种思想的小可怜。而邻班女孩月亮一般恬静而深远的笑容就在此时映入我的眼眸,它柔柔地抚摩着我受伤的心。我一厢情愿地以为邻班女孩与我有着两颗“相融而不相交的灵魂”,所以这世上也只有我,才能看清她身上的光环。
邻班的女孩是一篇写景散文,清新而又隽永。我这样告诉我的好友,一个很理智、很活泼的女孩。她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瞪了我半晌,然后将手按在我的额头上,再摇了摇头,说你吃错药了?你不懂。我一边说,一边将她的手送回她的口袋。从此,我与好友之间,也被一砖一瓦地竖起了厚厚的墙。不要紧。我在惋惜的同时这样安慰自己:有邻班的女孩这样的朋友,我也该知足了。
然而那件事终于还是发生了。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正坐在报告厅里,听那位眼睛不大好,脾气又太好的领导的讲座。我的周围坐着全年级三百多号人。邻班女孩坐在我的前面第四排。当那位领导背转身板书的时候,右边靠墙的部位有人低叫了一声,一架纸飞机摇摇晃晃地斜冲了下来(报告厅是楼梯式的座位)。这大概是哪位学兄闲得无聊时突发的灵感。这个举动激发了许多同学的“创作热情”,有几架飞到了我的桌上。我下意识地皱了眉,一片一片地撕碎它们,再塞进抽屉里。这时候,我看见有一架飞机从邻班女孩的头顶飞过。邻班女孩伸出手,用一种极其优雅的姿态截住了它。她在纸上添了些东西,然后回转身,微微笑着,随手将纸飞机掷向了我所在的方位。我的心跳得厉害,有一种冷飕飕的感觉,手心里攥满了汗水,然而我还存在着希望。纸飞机掉在我前面那位男生的肩膀上。几乎同时,我从座位上弹起,将纸飞机“抢”了过来。那个男孩诧异地望着我,而我已顾不得自己的失态,很毛躁地将飞机展开。上面属于她的字有两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的脑袋“轰”的一声炸裂了。所有的希望化成了一氧化碳,灌进我自己的腹中。这就是那个古井般的邻班女孩吗?这就是那个完美的代名词吗?这就是我倚靠了整整半年的支柱吗?我眼见着邻班女孩在报告厅淡绿的灯光下展现着从未有过的谄笑和旁若无人,眼见着她的笔记纸化作的飞机散往四面八方,一时竟冷得发不出声。
那件事后,我原先摇摇欲坠,因了她才勉强撑住的信仰之柱彻底坍塌了。可是怀疑和否定自己毕竟是一段艰难的历程,我时刻徘徊在自强和破罐破摔的边缘。为了自己能够坚强地、自信地走完余下的人生道路,我借走了图书馆中跋涉者的传记。在苦苦挣扎了铅灰色的雨季之后,我终于走出了那个病区,踏上了健康的道路。
而邻班的女孩,依旧会丁香一般地飘向我,投下淡淡的、一直渗进眼眸的微笑。只是,她身上的光环,被永久地、永久地遗失在了某个阴暗的旮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