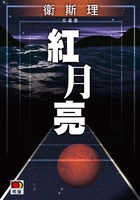有时,对人类社会及闲言碎语感到厌倦,对所有乡村的友人们也烦透了,我便越过惯常起居的那些地方向西漫游,进入到这个乡镇的更无人迹的地方,来到“新的森林和牧场”上;或者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到费尔港山上,大嚼黑越橘和草莓,再储存一些,以备几天内的食用。水果可是不会把它真正的香味献给购买它的人去享受的,也不会献给为了市场而栽培它的人去享受的。要获得那种真正的香味只有一个办法,不过很少人采用这个办法。如果你要知道黑越橘的香味,你得请问牧童和鹧鸪。一个从来不采黑越橘的人,却以为已经尝全了它的香味,这是一个庸俗的谬见。从来没有一只黑越橘到过波士顿,它们虽然在波士顿的三座山上长满了,却从不为人所知。水果的美味和它精华的部分,在装上了火车运往市场去的时候连同它的鲜丽一起给磨损了,它变成了仅仅是一种食物。只要永恒的正义还在统治宇宙,就不会有一只纯真的黑越橘能够从城外的山上运到城里来的。
在我干完了一天的锄地劳动之后,偶尔我凑到一个没耐性的伙伴跟前,他从早晨起就在湖上钓鱼,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的像一只鸭子,或一片漂浮的落叶,在实践各种各样的哲学之后,在我来到之前他大致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是属于修道院僧中的古老派别了。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是个很不错的渔夫,尤擅长各种木工,他非常高兴地把我的房屋看作是为方便渔民而建的;当他坐在我的屋门口整理钓丝,我也同样很高兴。我们偶尔一起泛舟湖上,他坐在船的这头,我在船的另一头;但是我们之间并没有多少交谈,因为他近年来耳朵变聋了,偶尔他会哼起一首赞美诗,这和我的哲学异常地和谐。我们之间的交流全部都是和谐的,回想起来十分愉快,比我们用谈话交流要有意思得多。当我找不到人谈话了,我常常用桨敲打我的船舷,激起回声,使周围的森林响起一圈圈扩散着的声浪,像动物园中的管理员激起了兽群的咆哮那样,我一直敲打,直到每一片山林和青翠的峡谷最后都发出了咆哮之声。
在温和的黄昏时分,我经常坐在船里弄笛,看鲈鱼在我的四周游移,似乎是被我的笛音给迷住了,而月光在棱纹似的湖底旅行,上面还零乱地散布着森林的破碎残枝。很早以前,在一些夏天的黑夜里,我时常跟一个同伴探险似的来到这个湖上;在水边生了一堆火,我们认为这样可以吸引鱼群,又把蚯蚓缚在钩上作鱼饵,钓起一条条鳕鱼;这样我们一直忙到夜深以后,才把燃烧的火棒高高地抛到空中,它们像放烟火一样,木头又从空中落进湖,发出一些响亮的咝咝声,便熄灭了。于是我们就突然坠入在完全的黑暗之中摸索的境地。我用口哨吹曲子,穿过黑暗,又上路重新回到到人们的聚居处。不过现在我已经在湖岸上有了自己的家。
有时,在乡村的一个起居室里,一直待到他们一家子都要休息时,我这才回到森林里。然后,多少是为了第二天的伙食,我用子夜的时辰在月光之下的划船垂钓,听枭鸟和狐狸为我唱它们的小夜曲,不时还听到附近的一只不知名的鸟雀发出吱吱的叫声。对我来说,这些经验是很难忘和珍贵的。我在水深40英尺的地方抛了锚,离岸约二三十杆远,四周有时环绕着大约有几千条小鲈鱼和银鱼,月光下,它们的尾巴在水面上点出了无数的水涡;我用了一根细长的麻绳,和生活在40英尺深的水下那些神秘的夜间的鱼打交道;有时在柔和的夜风中,我拖着长60英尺的钓丝在湖上漂荡,不时感到了钩丝上有微弱的震动,说明有一个生物正在钓丝的另一端觅食,却又笨头笨脑地不知道对这盲目撞上的东西怎样办,还没有完全下决心呢。到后来,你一手又一手慢慢地拉起钓丝,而一条角鲶被拉到了空中,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尤其在黑夜,当你的思想在其他天体中宇宙起源的主题上遨游的时候,你感觉到了这微弱的震动,打断了你的遐思,重新把你和大自然联系起来,这种感觉十分奇怪。接下来,我似乎会把钓丝甩到天空里去,正如我把钓丝垂入到这密度未必更大的水的元素中去一样。这样我仿佛用一根钩丝钓到了两条鱼。
瓦尔登湖的景色属于卑微之列,虽然很美,却还不够宏伟壮丽,对于那些不常去游玩的人或不在湖边住的人不具有什么吸引力。但是这一个湖以深邃和清澈著称,值得详细描写。这是一个既清又深的碧潭,长半英里,周长约1又3/4英里,面积约61英亩半。它是松树和橡树林中央常年清冽的老湖,除了雨水和蒸发之外,并没有明显的出入口。四周的山峰突然地从水上拔地而起,高度达到40英尺至80英尺,但在东南面高到100英尺,而东边更高到150英尺,都位于方圆1/4英里及1/3英里的范围内。山上覆盖的全都是森林。整个我们康科德地方的水波至少呈现出两种颜色,一种是站在远处看到的,另一种更接近本来的颜色,是站在近处看见的。第一种更多地取决于光线,根据天空的颜色而变化。在夏季晴朗的天气里,从稍远的地方望去,水呈现出蔚蓝色,特别在水波荡漾的时候,但从很远的地方望去,却是一片深蓝。在暴风雨的天气里,水有时呈现出深石板色。然而据说海水的颜色有时是蓝色的,有时又是绿色的,尽管天气却没有发生任何可感知的变化。当白雪覆盖这一片风景时,我看到我们这里的水系中,水和冰几乎都是碧绿色的。有人认为,蓝色“乃是纯净的水的颜色,无论水是液态还是固态”。可是,直接从船上俯瞰近处的湖水,水的颜色又非常之不同。甚至从同一个视点看过去,瓦尔登湖是一会儿是蓝色,一会儿是绿色。湖横亘于天地之间,所以这两种颜色兼而有之。从山顶上眺望,它倒映出天空的颜色,可是走近了看,在你能看到近岸的细砂的地方,湖水却是淡黄色,接着便呈现出淡绿色,然后逐渐地加深起来,直到湖的中间部分全部呈现出单一的深绿色。在某种光线的照射下,即便是从山顶上望去,靠近湖岸的呈现出的碧绿水色也是生动异常。有人说,这是绿原的反射;可是在铁路轨道这儿的黄沙地带的衬托下,也同样是碧绿的,而且,在春天,树叶还没有展开的时候亦是如此,湖水的颜色也许是太空中的蔚蓝和黄沙经过调和以后的效果。这是它的湖水虹膜的颜色。正是在这一个地方,春天一来,湖底反射上来的太阳的热量让冰雪开始增温,这里首先溶解成一条狭窄的河道的样子,湖中央的冻冰仍未化开。在晴朗的天气里,像这里其他的河湖激湍地流动时,波平面正好和天空形成90度直角的反射,或者因为太多的光线混合在湖水中,从较远处望去,湖水呈现出比天空更蓝的颜色;而在这种时候,我泛舟湖上,四处眺望倒影反射,我发现了一种无可比拟、难以描述的淡蓝色,像波纹丝绸或闪光丝绸以及青锋宝剑让人产生的联想,比天空本身还更接近天蓝色,它和波光另一面原来的深绿色轮番地闪现,那深绿色与之相比似乎显得更混浊。这是一个透明的蓝中带绿的颜色,在我的印象中,它仿佛是冬天里太阳落山之前,云缝隙中露出的一角晴天。可是你用玻璃杯举起一杯水拿到亮处看,它却如同装了一杯空气一样毫无颜色。众所周知,一大块厚玻璃板便呈现了微绿的颜色,据制造玻璃的人说,那是因为玻璃“体积”的关系,而很小一块同样的玻璃就不会有颜色。瓦尔登湖需要有多少的水量才能泛出这样的绿色呢,我从来都没有验证过。这里的水色在我们直接朝下望着时候看到的是黑色,或深棕色,一个人到河水中游泳,如同所有的湖一样,河水会给他染上一种黄颜色;但是这个湖水却是这样地清澈透明,游泳者身体呈现出大理石一样的白色,而更为奇怪的是,在这水中四肢给放大、扭曲了,呈现出一种非常夸张的形态,很值得让米开朗琪罗来做一番研究。
水是如此的透明,25英尺至30英尺以下的水底都可以很容易地看清楚。在湖上泛舟,你可以看到在水面许多英尺的下方有成群的鲈鱼和银鱼,大约只一英寸长,然而很容易由横行的花纹将前者区分出来,你会认为这种鱼也是为了逃离红尘,才到这里来生存的。有一次,在许多年前的一个冬天里,为了钓几条狗鱼,我在冰上挖了几个洞。上岸之后,我把一柄斧头向后扔在冰上,可是好像有什么魔鬼故意要开玩笑似的,斧头在冰上滑过了四五杆远,直接掉进了一个窟窿中,那里的水深25英尺。出于好奇,我趴在冰上往那窟窿里望,终于看到了那柄斧头,它偏在一侧,头向下直立着,斧柄竖直向上,随着湖水的荡漾轻轻摇摆;如果不是我打断它,它可能就会这样一直立下去,直到木柄腐烂为止。我用带来凿冰的凿子在斧头的正上方凿了一个洞,又用刀子割下了我看到的附近最长的一条赤杨树枝,做了一个活结的套绳,绑在树枝的一头,小心地放下去,套住了斧柄凸出的地方,然后用赤杨枝旁边的绳子一拉,这样又把那柄斧头吊上来了。
湖岸是由一长溜像铺路石那样的光滑的白卵石铺就的;除一两处短短的沙滩之外。湖岸陡立着,许多地方只要纵身一跃便可以跳到一个人深的水中;要不是湖水出奇的明净,你绝不可能看到这个湖的水底,只看到它在对岸又升起来。有人认为它深得没有底。它没有一处是浑浊的,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或许还会说,它里面连一根水草也没有;至于可以见到的植物,除了最近给上涨了的水淹没的,严格来说并不属于这个湖的草地以外,就是仔细观察也不会发现菖蒲和芦苇,甚至没有水莲花,不管是黄色的还是白色的,有的只是一些心形叶子和河蓼草,也许还有一两根眼子菜;然而,除了游泳者之外不可能看到它们;这些水草明亮而清澈,也像它们生长于其中的水一样。卵石伸展入水中只有一二杆远,再远点,水底已是纯净的细沙,只有最深的部分通常有一点沉积物,或许是多少个秋天以来,落叶被刮到湖上腐朽以后形成的;另外还有一些光亮的绿色水苔,甚至在深冬时节也会随着铁锚而被拔上来。
我们还有另一个这样的湖,白湖,位于偏西两英里半处的九亩角那里;在以这里为中心的方圆12英里的半径之内,虽然还有许多的湖沼是我熟悉的,我却找不出第三个湖有这样纯洁得如泉水般的特性。大约历来有许多民族都饮用过这湖水,赞美它并测量过它的深度,而后他们渐渐地都消逝了,湖水却依然像当初那样澄清、碧绿。没有一个春天间断过!说不定远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乐园的那个春天的早晨,瓦尔登湖就已经存在了,甚至在那个时候,伴随着轻雾和一阵阵的南风,一阵柔和的春雨飘洒下来,湖面荡起了层层涟漪,数不清的野鸭和天鹅在湖上游弋,它们对被逐出乐园这回事一无所知,这片纯粹的湖水足够让他们心满意足啦。甚至就在那时,它已经开始涨潮,落潮,让水色纯清,还染上了它现在所有的色泽,并且得到了天堂的特许,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瓦尔登湖,它是天上露珠的蒸馏器。谁知道在多少篇已被人忘记的民族文学中,这个湖曾被誉为灵感之泉呢?而在黄金时代里,又有多少山林水泽的精灵曾在这里居住?这是在康科德的冠冕上的一颗明珠。
然而,也许第一批来到这个湖边的人留下过他们的一些足迹。我曾经很惊异地发现,沿湖周边,甚至在一片被砍伐了浓密的森林的岸上,在一条绕湖一匝峻削而狭窄的小径上,这些足迹一会儿上升,一忽儿下降,一会儿靠近湖,一忽儿又远离了,它大概和生活于此的人类同样悠久,是土著的猎者用脚步走出来的,现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居住者仍然不知不觉地用脚踩踏着。冬天站在湖中央看得更加清楚,特别在下了一阵小雪之后,山路看上去就成了一条连绵起伏的波浪线,没有被败草和枯枝掩蔽,许多地方在1/4英里以外还能看得十分清楚,但在夏天里,便是走近去看,也是看不出来。似乎是雪花用清晰的白色的浮雕又重新把它刻印出来了。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在这里建造一些别墅,装饰的庭园或许还能保留它的一些残迹。
湖水时涨时落,但是否有规律,又遵循怎样的周期,没人知道,虽然有不少人照常要不懂装懂。通常情况下冬天的水位要高些,夏天的低些,但水位与天气的潮湿干燥却没有关系。我还记得与我住在湖畔时相比,何时水低了一两英尺,何时又至少涨高了5英尺。有一个狭长的沙洲延伸到湖中,它的一侧是深水,距离主岸大约6杆,那大约是1942年,我曾在沙洲上煮开过一锅杂烩,可是一连25年都无法再去那里煮东西了;另一方面,当我告诉我的朋友们说,几年之后,我会经常在森林中的那个僻静的山坳里垂钓,在距离他们现在看得见的湖岸约15杆的地方驾一叶扁舟,现在那里早已成为一片草地了,他们听后常常露出不相信的神情。可是,这两年来湖的水位一直在涨高,现在,1852年的夏天,比我在那儿居住的时候已经高出5英尺,与30年前的高度相当,又可以在那片草地上垂钓了。从表面上看,水位已涨了六七英尺,但是实际上只有很少的水量从周围的山上流下来,湖水涨溢一定是由于影响它深处的泉源造成的。同一个夏天,湖水又开始下降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这种涨落有否周期,却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我曾观察到一次涨和两次部分地退,我估计在12或15年后,水位又要降落到我曾经见过的地方。位于偏东一英里的弗林特湖有泉水注入和流出,是激荡涨落的,而其间一些较小的湖沼都与瓦尔登湖同升降,最近也涨到了它们的最高的水位。根据我的观察所及,白湖的情况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