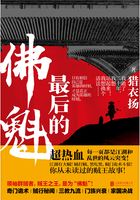现在,他们又坐在一起吃中饭了。里畈路太远,船在路上光是单趟就得花两三个钟头。桑怀仁中午是不会回来的,还是那张桌面跟铜板一样木沉的八仙桌,还是那么几个人。早上她坐在朝西那边,这回她故意选择面北,可是他跟着选择在朝南位置上,那是他父亲的座位。她忽然变得跟少女一样羞怯、文静,然而又抑制不住地心跳、脸红。
她吸引了他!她居然把他也给吸引了!
她的心里又一阵狂跳,然后是骄傲和感激。双方目光再次相遇的时候,他们已经像情人一样互相交换着盛夏里的太阳光一样的灼热。尽管他们之间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过。高潮紧接着出现在他们用完膳后一起从偏院里出来的时候,他们本来朝着同一个方向往正屋那边走过去的,她忽然记得自己把一块披巾丢在饭堂里了,一转身想回去拿,却忘了背后还紧紧跟着他。于是他们撞在了一起,她撞在了他的怀里。这时候她才发现他的高大和他这个年龄具有的强壮结实。他们虽然很快就分开,但两个人都知道自己故意拖延了几秒钟。就在这几秒钟里,她闻到了他身上那股淡淡的香胰子味儿。这种气味使她以后沉浸在对往事的美好回忆或者充满向往和渴望时,总会长久地出现在她的鼻子里。
她该和往日一样进行她的午睡了。当她轻轻合上眼的时候,就听见桑怀仁走进房里来的脚步声。“老爷你回来了?”她躺在那里闭着眼问。可是老爷没有答应她。她睁了下眼皮,却意外发现竟是他,正站在她的床边默默地望着她。她忽然冲动着想要不顾一切地冒一次险。她闭上了眼睛,等待着那股淡雅的香胰子味儿的逼近,渐渐包围住她整个呼吸。跟随而来的将会是那种早已在桑怀仁身上失去了的雄性的强壮和霸道,她微微仰起了她的吻部,翕动了嘴唇,似乎渴望接住什么。
他也跟着她往那个地方滑过去。可是她并没有他想像中的那么无所顾忌,当他怀着一种得逞后的喜悦剥去她的衣服的时候,甚至还带着那么一丝羞涩。
事后,她又觉得不可思议和懊悔,这个简直可以做她儿子的年轻人——岂止是“简直”,而是完全可以!她怎么会和他这样?!她仔细回忆了整个过程,一切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她甚至想不起来他们之间都说过些什么话,直到现在她还没有听到过他唤过自己一声什么。桑怀仁绝不会想到他才出去了短短大半天时间,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背叛了他!她在傍晚看到老爷满脸疲惫地回来时,心里内疚得想哭。她想起五年前当她还在“满楼春”里揽镜自照,为自己日渐憔悴的花容黯然神伤的时候,是老爷花了五百块大洋,然后用一顶小轿把她抬到一艘乌篷船上,亲自吱嘎吱嘎地摇着橹把她接到了这条小镇上。入寝的时候,她把所有的愧疚和感激都在老爷身上化作了温柔和爱抚,她柔软得像只猫,又像米糕一样充满了粘性。但老爷不想,老爷叹息了一声说:“我累了,睡吧!”
老爷的家产越来越丰,身子却越来越瘦。老爷很多时候都会犯风湿病,天一冷或一湿闷,晚上睡时两条腿就没地方去放了。那是老爷年轻时累撑下的。老爷十八岁时为逃壮丁,从浙西的一个山窝窝里逃到里畈,一开始就专在那些有钱人家的乌篷船上摇橹拉纤,走过无数水路。无论寒冬酷暑,都在无数河滩上留下了脚印子,钻过无数芦苇荡和茅草丛,穿着破草鞋的双脚喀刺喀刺地踏碎过多少冰碴子,又在饥饿时生生地抓吃过多少扬在河边的麦穗和豆荚。老爷晚上和她做完那事,一时还没有睡意的时候,就常常会跟她讲他年轻时的这些经历。当然老爷也不会把一切都讲出来,老爷也有老爷的秘密。
于是她枕着老爷的呼噜声入眠了。梦却还没有完全进入,就又像小鱼一样扑嗤一声轻轻跃出了记忆的水面。她抚摸着老爷瘦骨嶙峋的背,她还在为自己刚才的激情所深深感动着,她渴望着他能突然转过身来,哪怕粗暴如二十多年前那个强暴她的歹徒也好。
他们又坐在一起吃早饭了。现在他只低着头吃自己的早饭,他没有再看她一眼,她知道那是老爷坐在自己旁边的缘故。他真谨慎,她想,他平时很少说话也正是出于谨慎吧。
再吃中饭的时候,桑怀仁又跑到里畈去了。她们仍然对着面,这回他比她落座得要早。可是他仍然跟吃早饭时一样,再也没有看她一眼。她一次又一次地抬起头来看到的是跟过去一样冷漠、毫无表情的面孔时,心里忽然觉得非常难受和委屈。一顿饭她都不知道自己吃了些什么,只是费劲地想着他又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这样。
他们一起从饭桌旁站起身来的时候,他忽然轻轻踩了她一脚,然后默默地看了她一眼,就那么一脚和一眼,一下子又把她从冰天雪地里拯救了出来,使她重新感受到阳光的灼烈,和在蓬勃的情欲照耀下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无比。
她像得到暗示似地赶紧回到了她的床上。他仍然一句话也不说地轻轻进来了,然后又是一句话也不说地干完了那事就匆匆离去。
后来他变得越来越胆大,他每天都会开车回来。只要有机会,只要想着那事儿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他都会把那些佣人打发干净,然后迫不及待地上她这儿来。片刻的欢愉对他们来说已经像小孩子口里的零食一样不可或缺。她知道自己更离不开他,就像那些吸食鸦片的人再也离不了那根烟枪一样。偶尔他一连有几天没回来,便会瞧着什么都觉没兴致,心里像只空口袋。
终于有一天,他再也不上她这里来了,甚至他又跟一开始那样每次都只是低着头进出,不再看她一眼。她像一只小花猫一样可怜地跟在他后面一起进饭堂,又跟着一起从饭堂里出来,甚至还不顾一切地跟着他在院子里走动,他连回过头来看她一眼都没有。她怎么都想不起来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竟受到他如此惩罚。
她眼睁睁地看着他站在阳光下的院子里洗凉水澡,他把仆人们给他从井里提上来的一桶桶凉水哗哗地往自己身上浇,远远地正对着她这边的窗户。阳光抚摸着他那些闪闪发光而又起伏不平的肌肤。她的双唇和指头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游弋在这些一块块隆起了的肌肉里,但现在竟是这样可望而不可及!若是能再让她拥有一次——哪怕仅仅一次,那么即使等待她的会是什么也都会不顾一切!可是他洗完澡就开着车子走了。
她紧紧地抓着那一根根冰凉的窗栓,像一滴被凝固在玻璃窗上的水珠,久久地站在那里瞪眼望着这个被桑祖辉随意扔下的空得让人心里发慌的大宅院。被抛弃的痛苦折磨得她快要疯啦!
黄昏的时候,院门口忽然又传来了汽车喇叭声,她几乎要失态地从老爷身边站起来奔跑着迎出去。
她醒来过好几次,好几次躺在她身边的桑祖辉又变成了呼噜声特别响的桑怀仁。就这一个晚上她再也无法熬过去了!她看看挂在床头的那口自鸣钟,都已经三更了,旁边的桑怀仁呼噜声打得比雷还响。她趿一双软底拖鞋,像幽灵一样下床离去。
她又站在他的房间门外了。她摸了摸胸口,仿佛里面那颗心会跳出来。接着她又定了定神,不顾一切地用手轻轻剥啄那扇门。当那条窄窄的门缝终于出现时,她不顾一切地挤了进去。可是她期待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温热的空气里,她听见的却是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你不是跟我爹睡在一起?”他把“我爹” 两个字说得特别重。
她几乎颤抖着身子紧紧地抱住了他,眼泪成了乞求的一部分——“你带我走吧,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无论把我带到哪里……”
他又一声不吭了,只冷漠地挖开了自己身上的那双手,使劲儿把她推出了门外,她扑在那扇随即被重重关上的房门上,慢慢地蹲下来,坐在那里哭泣了一会儿,咬着自己的手。终于还是收拾了脸上的泪水,往自己的卧室门口走去。她听到了里面桑怀仁的咳嗽声,怔了一怔,接着继续恍恍惚惚地向门内走去。
“去哪儿了?”黑暗里,桑怀仁半倚半躺在床上。
她窒息般地沉默了好会儿,低声答道:“出去解了个手。”
“解手解到……”桑怀仁忽然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好容易抑制住了,他说:“你过来。”她机械地绕着床沿走过去。他说:“再过来些。”于是她又走近了一些。他便伸出那只宽大的手掌试着摸了摸她的脸,干净利落地给了她两个耳光,然后身子像面条一样往被窝里一溜,说:“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