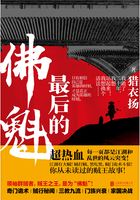桑怀仁在后来结束他那并不漫长的一生之前,又悄悄回过草荡镇一次。当时他就已经预感到知道自己手里所有的地契都将成为一刀废纸。他回到草荡镇上并不是为了想再从家里带走什么,只为了再去看看那个曾跟他一起生活了五年、也给了他五年慰藉的小妾月月怎么样了。
家里已只剩了一个看门兼管牲口的长工。他跟着这个忠实的长工一直走到草荡上最为荒凉的五锄头。在一条鼓凸着一个个土包子、已被废弃了的堤埂旁,他先是看到了一个用几根毛竹搭撑起来的草棚,然后又看见卜荣拄着根拐棍,端了个粗大的饭碗一瘸一瘸地从远处荒草丛里钻出来,走向那个草棚。他们跟了过去,在快走到草棚门口的时候,长工忽然看见东家站住了脚,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凝神谛听着——
风云易测人心难信,寸寸相思化灰尘。海神爷啊,对神灵不由我珠泪滚滚,尊一声海神爷细听分明……
宛转、甜糯的越剧这会儿显得如泣如诉。长工扭头看看老爷,老爷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着,直到里面女人的唱词被卜荣的声音打断——“好了好了,先吃饭吧,吃完了可以再唱的。”老爷忽然微微抖动了嘴唇,好会子才喃喃出声道:“白牡丹……白牡丹……”但他迟疑着没有再向那草棚跨一步过去。长工跟着他在那里站着。东风很大,苏醒了的麦苗和青草油绿绿地从远处一浪一浪地翻滚过来,经过他们身边之后,又毫不迟疑地一浪一浪继续往前传递。随即背后又有一浪一浪翻涌上来。
长工肚子已经饿了,可老爷还在那里站着,长衫在大东风里旗帜一样呼呼啦啦地扯动着,长工看着老爷的身子似乎也在那里哆嗦着。又过了许久,才看见他慢慢地转过身来,微驼着背往回走了。走了十来步路,忽又站住了,从鞋底里挖出一张银票递给他说:“给她送去吧。”
后来桑怀仁就带着五岁的桑宝根离开了小镇。临走时,他还亲自和那长工一起把整个院子都一丝不苟地打扫了一遍。这是他积多年来的心血,完全靠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家产,每一块砖瓦都渗透了他的感情和心血。他自然不会想到两天后卧室里的那些宝贝古董都会被草荡游击小分队里的人砸得粉碎。
他带着幼儿又重新回到了王母山上的旧居。那里也许是个韬光养晦的好地方。这些年来他对桑家故居的那种眷恋早已荡然无存,他几乎已经不能再接受那种檀香与腐木等混杂在一起的陈腐气息。事实上,就在从这个旧居里搬迁出来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对它产生了厌恶,一次都没有带月月母子俩来过这儿——总觉得这里似乎不是自己真正的家。
当那个哑巴老头来给他开门时,他心里忽然一阵感动。入夜,远远地又传来那女人的尖叫声、跟西北风一样呜呜的吼啸声和呼嗤呼嗤的粗喘声。他悄悄地从床上坐起身来。牲口棚里的那盏马灯还点着,哑巴老头还在那搓草绳,看见他忽然唤了声“老爷”。桑怀仁并不感到奇怪——桑家也只有他听到哑巴会说话不会感到奇怪。他第一次跟自己的下人像兄弟一样平等地亲切地挨坐在一块儿。那老头儿忽地放下手里正在搓着的草绳,说:“不知老爷喜不喜欢听二胡,小人给老爷拉一段解解闷儿。”便去取了把二胡来。桑怀仁听着那咿咿呀呀声,顿觉内心里全是那股翻山倒海的滋味,仿佛又置身在那些凄凉心酸的往事中,鼻子里一阵阵地涌过酸楚,感到眼前一下子变得十分模糊,忙摆了摆手说:“别拉了,别拉了!”
老头儿没理他。老头儿微闭着眼睛,完全沉浸在那种境界里了。一曲终了,桑怀仁早已是泪流满面。老头儿却抱着那二胡一动不动木讷地坐在那里。桑怀仁抹了把脸问:“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没想到你还会这个——你到桑家来之前到底是做什么的?”老头儿把那二胡横放在膝盖上,过了会子说:“不瞒老爷小人以前就在一个戏班子里的。当初骗老爷说是逃荒过来,那是小人迫不得已编的。”桑怀仁便又问:“祖辉的身世是不是你告诉他的?”老头摇头说:“大少爷到这会儿还不知道我这哑巴是装的呢。”过了一会儿老头儿又说:“小人还有一事瞒着老爷,大少爷其实不是小人从路上捡来的,而是小人的亲外孙。
“小人有两个女儿,都跟着小人夫妇在一个戏班子里唱戏。大女儿艺名叫红牡丹,小女儿叫白牡丹。一年正月初一,戏班子进城演戏,夜里戏演完后就睡在那大户人家的祠堂里。不料深夜祠堂里突然失火,全班二十来个人最后只侥幸逃得小人跟小女白牡丹两条命。小人也受了重伤,一根椽子掉下来正压在小人背上,成了现如今这副模样,再也未能上台唱戏。白牡丹又入了另一戏班子,忽有一日,那班主抱着个婴儿来寻小人,说是白牡丹遭一歹徒强暴,并怀上了身孕,自觉从此无颜再见人。待那孩儿出世后,即含恨自杀。小人便抱了孩子寻到小女当初遭强暴的沥水县金家庄,四出打听那强徒消息。奈何除了小女自己外,谁也未亲眼见过那强徒,小人心也灰了,又怕孩子依旧跟着小人一起吃苦,幸亏遇上老爷老太爷收留。小人当初既已答应过老爷和老太爷,就定会一直装聋作哑下去,决不把真相告诉大少爷,请老爷放一百个心!”
老头儿话音一落,整个院子里即一片死寂。桑怀仁坐在那里仿佛睡着了一般,再也未说一句话,也未扭过头来看他一眼。
后院那边忽然又传来几声凄厉的尖叫声和桌椅的摔打声。桑怀仁忽然跳起来,也跟着怪叫一声,疾步朝那正屋走去。一直走到一堵墙跟前了,老头儿眼睁睁地看着他往那墙上撞过去。
桑祖辉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父亲喉咙里像在抽大烟似地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却面色红润地微笑着对他说:“好儿子,你把你亲娘给……睡啦!”快要咽下那口气的时候,他又重复了一遍:“把你亲娘……月月……睡……了。”
就在章一天辞职的那个月底,上任还不到半年的县党部书记长谷彦木烧毁了县党部全部档案后,也跟冯根生一样不知了去向。沥水游击支队进驻县城那会儿,桑祖辉带着残剩的三十来名队员往草荡仓皇而逃。
有关桑祖辉的溃逃故事,数十年之后还在草荡上流传——
沥水支队在接到草荡小分队的报告后,立即追击到草荡,在方圆数十里宽广的五锄头拉开了大网,把那一块块荒草和芦苇荡都细细地篦了一遍,却连一个匪影子都没见着,只在一个用两三支毛竹搭撑着的草棚里见到了桑怀仁的小妾,倚着支毛竹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面色苍白而又宁静。成群结队的蚂蚁围着她的脖子欢快地奔跑着。一条门栓杠粗的火炼蛇盘旋在两三步路远的另一支毛竹上,虎视眈眈地望着她。
他们又迅速向那王母山上追击过去,却还未到山脚下就远远望见桑家旧居的那面山坡上空腾起一团一团浓烟,浓烟下面不断地有淡黄色的美丽的火信子蹿起来舞蹈着。
他们最后在那些灰烬里只找到了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没有桑祖辉。桑祖辉的最后被抓获,有着卜荣的功劳。他们躲在王母山上的一个地道里负隅顽抗,就在沥水支队里的数名队员先后被击倒,其余的人都无法再上前一步的同时,章觉民在卜荣的引领下,率着小分队里的人悄悄摸到了还未被里面的人发现的那地道的第二个出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