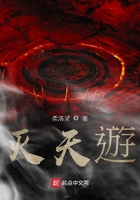“无异议便好。”说到这里,慈禧太后不无得意地冷哼了声,端杯微呷了口。满殿鸦雀无声,良久,但见她环视周匝,干咳两声道,“当初皇上年幼,为了保住祖宗留下的这份基业,应诸臣工坚请,我方挂了这帘子临朝听政,一眨眼十几年便过去了。想想这些年,虽不敢说有什么功劳,却也好歹没出什么岔子。如今皇上年岁也不小了,我寻思着过阵子便将这帘子撤了。”
寥寥几句话,却无异于平静的湖面上投下块千斤巨石。一时间乾清宫内直如开锅稀粥般热闹,有的凝眉深思,有的自言自语,亦有的两三人凑在一处窃窃私语,只光绪一人端坐在须弥座上,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喜悦之色。盏茶工夫,只见庆郡王奕劻、军机孙毓汶等人一甩马蹄袖,跪地叩头道:“臣等恭请老佛爷收回成命。”
慈禧太后微微点了点头,开口道:“都起来吧。我一个女人家十几年来独撑这么大个局面,身子骨实在是乏透了,总不成你们愿意看见我累死在这椅子上吧?话说回来,这帘子不撤,于理也不合。更何况还有人整日价背地里嚼舌根子!”说着,慈禧太后下死眼望了下光绪皇帝和醇亲王奕譞。奕譞不知是气的还是紧张,苍白的脸颊青一阵紫一阵。
“这事就这样了。还有什么要奏的吗?”说着慈禧太后扫了眼周匝,复道,“既没什么,军机们留着,其他臣工都跪安吧。”
“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官兀自窃窃私语,闻听忙跪地高呼退了出去。眼见众官退出,慈禧太后起身离座,来回踱着碎步,花盆底鞋橐橐响着,似乎对人,又似乎自语:“这下算是要轻松了——”
“老佛爷,”孙毓汶犹豫了下,上前一步躬身道,“奴才愚见,皇上虽已近成年,终不曾亲身涉猎政务,仓促间撤帘,只恐——奴才恳请老佛爷再行垂帘数载,待皇上谙于政务之时再行撤帘。”
“这阵子皇上不也看折子了吗?”
“折子皇上是看的,不过拿主意还得老佛爷您呀。”
“奴才……”奕譞双脚一软跪在地上,叩头泣声说道,“奴才恳请老佛爷看在列祖列宗的份儿上,就……就收回成命吧。”
“你果真这般想的?”慈禧太后停步,望着兀自颤抖不已的奕譞。
“臣若言不由衷,愿……愿遭天谴。”
“这说哪儿的话了。”慈禧太后说着移眼望向光绪。眼见父亲这般样子,光绪先时的喜悦早已掀至九霄云外,违心道:“儿臣恳请亲爸爸收回成命。”“既如此,那我这老婆子就好歹再撑阵子,待皇上大婚后再行撤帘吧。对了,皇上的婚事现在也该想着了,回头拟个旨传下去,凡王公贵戚、督抚将帅有德容兼备女子者,都到内务府报个名。另外,还有件事与你们说说。”慈禧太后说着顿了一下,“我想趁这阵子将清漪园修修,总不成撤帘子后还让我老婆子待在宫里吧。你们说呢?”
劳军拿不出银子,却原来为的是修园子,众人听罢,心中登时雪一般亮堂,只眼见得这般光景,皆默默不语。慈禧太后稍顿了阵,径自开口道:“既然都没什么说的,那下去就让奕劻和杨立山他们几个去看看,估个数出来。”说罢,转身脚步橐橐而去。
望着那远去的背影,光绪只觉心中打翻了五味瓶般不是滋味,正欲吩咐退朝,兀自跪在地上的醇亲王奕譞面部突然痛苦地抽搐了下,一口鲜血从口中狂喷而出!光绪怔怔望着,一动不动,只用惊恐的目光看着。待太监们一拥而上时方回过神来,忙迭声催促:“快!快唤李玉和来!”
李玉和一早起来,正抽空睡回笼觉,听得传唤忙火烧屁股般奔来,又是把脉又是掐人中,足足忙活了顿饭工夫,方道:“万岁爷不必担心,醇王爷只不过是身子虚弱,加之急火攻心,过会儿便会没事的。”
“皇上——”奕譞半晌方睁开眼睛,见光绪众人俯身看着自己,使劲动弹了一下,勉强笑道,“奴才惊了圣驾,实在……实在是……”光绪容色惨淡,眼中已是泪花闪烁,哽咽道:“不要说了,都怪朕。王福,你和李玉和一道送醇王爷回府去吧。”说着,泪水已掉线风筝般滚落了下来。
回到养心殿,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越想越觉万绪纷杂,无以自解,光绪犹豫下起身出了殿:“小寇子!”
“寇公公方才出去了,万岁爷有什么事?”一个宫女疾步上前,欠身答道。光绪没有言语,沉吟片刻,抬脚下阶径自奔了御花园。
初春时节,花神用她特有的手段,将御花园装饰得嫣红柔绿。信步其间,光绪直觉得心旷神怡,好不惬意。忽的,不远处传来一阵女子咯咯的笑声,光绪皱了皱眉,循声而去,待至跟前,却原来是师傅翁同龢和两个与自己年岁相仿的少女:“何人如此大胆,竟敢私自进入御园嬉闹?!”
“嗯──”翁同龢背对着光绪,闻声懵懂了阵,忙转身跪倒在地,道,“臣翁同龢不知圣上驾到,失仪之处还请皇上恕罪。”
“哟,原来是翁师傅呀。朕说呢,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私闯御园?”光绪故意绷着面孔冷哼一声。
“臣──”
“哈哈哈……”望着翁同龢满脸惶恐的神色,光绪忍不住笑出了声,“师傅快快起来,朕与你说笑来着。对了,这都谁家女子?”说着,光绪移眼细观二女子:大的口如樱桃,腮似桃花,俊秀的面庞上嵌着一对甜甜的酒窝。那小的也长得如花似玉、明眸皓齿的,身穿红色牡丹花上衣,腰扎粉红色的凤尾裙,但最使人动心的,还不在她这出尘脱俗、美逾天仙的容貌,而是她那一种内在的气质:娇憨天真,毫无一点心机;纯洁善良,宛若瑶池仙女。
“回皇上,此二女皆为侍郎长叙之女。”翁同龢起身道,“因听着御园风景瑰丽,故求臣带她们进来瞅瞅,不想扰了皇上雅兴,还请皇上恕罪。”说着话,翁同龢向着兀自呆立一旁的姐妹俩一努嘴。
“奴婢给万岁爷请安。”
长叙,已故陕甘总督裕泰之子。光绪三年官至侍郎。光绪六年与山西藩司何葆亨结成儿女亲家,可好日子偏定在十一月十三日(圣祖仁皇帝宾天之日),此日国忌,连作乐也不准,更何况这等事?当下御史邓承修便上折弹劾,遂被罢官,此后一直郁郁不得志,直至前阵子慈禧太后五旬万寿时,方蒙恩开复原职。光绪听罢,脑海中兀自搜索了阵,方点头道:“朕想起来了,便是那个在圣祖爷宾天之日给儿子办喜事的长叙吧。”
“是。”
“阿玛一时疏忽,错选了日子,难不成万岁爷便将这帽子永远扣在他头上吗?”那年纪小的女子听得光绪言语,樱桃小嘴立时撅了起来,不快道,“再说……再说阿玛为这事也受过了呀。”
“放肆!”不待光绪言语,翁同龢已断喝一声,厉声斥道,“没看这是什么地方?你在对谁说话?”
“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你──”
“师傅不必责怪她了。没看出一向迂讷的长叙竟会养出这么个伶牙俐齿的女儿,有骨气,有胆魄!”光绪又看了眼那女子,眼中满是赞赏神色,“这点朕便不如她。”
那女子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微微笑了笑。她本就天生丽质,笑将起来更有如百合初放,端的是国色天香。光绪目光动处,一时之间,不觉看得呆了。良晌,方发觉自己失态,轻咳两声掩饰道:“好了,你姐妹二人别处转转,朕这尚有话要与师傅说。”
“哎。”二女轻应一声,起身又道了个万福方轻移莲步而去。
若得此女长相厮守,也不枉来世一遭了。光绪寻思着仰天长吁了口气,定神道:“方才老佛爷提出撤帘一事,不想众臣工皆云不可,不知师傅怎生想法?”“臣方才也细细寻思了这事。”翁同龢拈须沉吟道,“依臣看来,此时确不宜撤帘。”
“什么?你也这般看法?”光绪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两眼睁得铜铃般大,道,“你不也希望朕早日执掌朝柄,一改眼下这等局面吗?”
“臣是如此想着。不过,以皇上目下之阅历,似仍无独立处置政务之能力。此时撤帘归政,万一有甚曲折,诸臣工一奏请,老佛爷还不是——与其如此,皇上倒不如再挨个把年头,多长些见识,到时名正言顺,别人也没甚可说的。”翁同龢说着顿了一下,接着道,“话说回来,目下朝中多是老佛爷的人,皇上年幼,能支得动他们吗?”
“支不动便罢了他!”
“这非治世之良策,不到万不得已不可用的。”翁同龢苦笑了下,“罢一两个可以,总不成将他们都罢了吧?如此朝里朝外一大摊子事,谁去处置?”
“师傅所言也有理。只……只看着祖宗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社稷日渐衰微,朕这心里急呀。”光绪无奈地摇了摇头,喟然道,“你晓得吗?方才老佛爷又想重修清漪园呢,这一动少说也得数百上千万两银子!如果将这些银子用在正处,又能办多少实事呀。”
“皇上如何作答?”翁同龢皱了皱眉。
“气氛不对,朕什么也没说。”
“没说什么便好。”翁同龢点了点头,道,“依臣意思,眼下老佛爷想做什么便由她去。皇上呢,最好是金口紧闭。”
“你让朕睁一眼闭一眼?”
“正是。说也是徒劳,倒不如不说,免得惹老佛爷不快。皇上眼下只将心思用在熟谙政务上便是了。”
光绪仰脸望天久久没有说话,良晌方道:“师傅所言不无道理。只恐依着朕这性子,怕很难做到。”“那便请皇上勉为其难吧。”翁同龢两眼闪着坚定的目光,侃侃道,“唯有如此,皇上亲政方可少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也唯有如此,我大清重现昔日辉煌方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