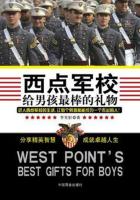奕譞点了点头,说道:“你知自己难免有力不从心之时,却敢于说出口来,只此一点我便放心了。”
“七爷待卑职礼遇有加,然卑职却——”李鸿章说着起身深深鞠了个躬,“卑职实感汗颜,还望七爷多多谅囿。”
“坐,坐着。我去后,六爷必会被上边重新启用,我前阵子也曾说与他,许是怕露了风声,他没多言语。不过,他与我终是亲兄弟,手足之情他是绝不会忘的。里边有他我也就放心了。外边呢,只你举足轻重,若你——我便可放心地去了。”
“七爷如此抬爱,卑职真惭愧万分。”李鸿章细碎白牙咬着下嘴唇,抬眼望着奕譞拱手道,“但只要上边有六爷,七爷您放心,卑职定竭忠尽力,辅佐圣上。”
“少荃——”奕譞满脸激动之色呼了声,泪水忍将不住断线风筝般掉了下来。李鸿章见状,喉头亦是一阵哽咽,亲自拧了块热毛巾递与奕譞,声音略带嘶哑道:“时候也不早了,七爷若再没什么吩咐,卑职先行告退。”
“那……那好吧。这事你可……”
“卑职晓得,绝不敢泄露丝毫。卑职告退。”
“何玉柱,送送李制台。”奕譞吩咐了句,仰脸躺在椅子上,摇曳不定的烛光映在他那绯红的面颊上,是那么的安详,隐隐还透出丝笑意。这时间,叶赫那拉氏已疾步行了进来,蹲了万福便道:“老爷,您……您怎样?先时李玉和那奴才说你——”
“我这不好好的吗?都是那奴才大惊小怪的。”奕譞微笑着道,“你回去歇着吧,让我一个人再待会儿。”叶赫那拉氏不放心地细望了眼奕譞,开口道:“我还……还是陪着老爷吧。天凉了,老爷还回炕上躺着吧。”说罢,她径自搀了奕譞斜倚在大迎枕上,转身出屋就屋外炉子端药进来,边吹吁着边望着奕譞不安道,“老爷,我来有一阵子了,见你与李鸿章言语也没进来。听你方才言语,我这心里总——”
“怎这么苦呀?”奕譞端药微呷了口,平直的“一”字眉顿时紧皱了起来,道。“这什么药?”叶赫那拉氏忙不迭端了杯白水上前:“这那奴才自己新调制的药,试了效用还真不错。但愿能医好老爷您的病。”奕譞脸上不易察觉地掠过一丝苦笑,欲放碗却见妻子满是期待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终拧眉饮了,复漱了漱口,方道:“我知你心思,你但放心便是了。不是妥帖的人,我敢那般说?”
“就他也妥帖?”叶赫那拉氏盘腿坐在炕上,轻轻为奕譞揉捏着道。
“他虽跟我时日短些,可却是六哥使唤多年了的。你不要疑神疑鬼的。我以后不能为皇上做什么了,如今不趁着光景给他做些事,我真到那边了也不会安心的。”奕譞说着,发泄胸中堆积已久的郁闷般长长吁了口气。叶赫那拉氏听罢,强自忍着没让泪珠儿掉将下来,轻咳两声掩饰道:“我晓得的。只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总怕这万一要是处理不好——孙毓汶随老爷你时日也不短,若没老爷您提携,又怎有的他今日?可却还不是——”
“他怎样?”
“听说他与李莲英这阵子走得挺近的。”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古来就这个理。”奕譞转身望着窗外的瓢泼大雨,冷笑着道,“他另找门路就随他去吧。你放心,少荃即便真不如先时言语去做,也绝不会泄了出去的。他不掂量我尚可,但他却不能不虑着六哥的。”叶赫那拉氏嘴唇翕动着似还想言语,但见奕譞满脸怅然失神的表情,终止住了口。一时间书房沉寂了下来,只外边翻江倒海般的雨声和雷声不时传入耳中。
一夜无话,次日辰初时分李莲英乍然而醒,埋怨着金凤没有叫他,忙忙用青盐擦了牙,胡乱用了两块点心,连轿也不用,便打马急匆匆赶往紫禁城。
天上兀自飘洒着小雨,紫禁城临清砖上一汪汪积水上起着连阴泡儿。李莲英穿着油衣,刚过乾清门,便见醇亲王奕譞和孙毓汶、翁同龢一干军机自军机房出来,最后一人,簇新的仙鹤补服外套黄马褂,一条油光水滑的长辫直垂腰间,却是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李莲英怔了下,忙不迭紧赶几步上前,打千儿赔笑道:“咱家给七爷、各位爷请安了。”说着眼中亮光一闪,望着李鸿章道,“哟,这不是李制台吗?您甚时回的京呀?”
“昨儿个夜里。”李鸿章干咳两声。
“爷儿们慢走,咱家先行一步了。”李莲英笑着点头道了句,回头就走,不防一脚踩在青苔上,踉跄一步竟歪倒在水洼里,弄得淋淋漓漓浑身都是泥水。一个苏拉太监忙上前扶起,小心道:“总管,您没事吧?”
眼见众人皆禁不住偷嘴儿乐,李莲英榆树老脸顿时又青又黄,勉强笑道:“不打紧。你快回屋找身干衣裳送老佛爷那边。”说着也不脱外面袍子便急急而去。在慈宁宫外换了衣裳,李莲英三步并两步进来,却见四周死一般静寂,几个小太监清扫着积水,却亦是蹑手蹑脚,李莲英一颗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上,摆手招了个小太监一问,方知是园子银两告紧,慈禧太后心情烦闷,偏巧崔玉贵侍奉慈禧太后梳妆,竟将她乌发给梳落了几根。犹豫片刻,李莲英抬脚直奔西厢房,甫过宫院天井,便听西厢房“咣”的一声,似乎房内掼碎了什么,轻手轻脚至廊下细听时,却听慈禧太后正大声训斥着崔玉贵:“狗东西,有朝一日我这命也会送你手上!说,你究竟安的什么心思?!”
“奴才……奴才走神……老佛爷您就恕了奴才这遭,奴才再……再也不敢……”崔玉贵语声颤抖如秋风中的落叶,道。
“已经敢了,还‘再’?整日里宠着你们,你们便连差使也不晓得怎生去做了?!去,自己到内务府领三十棍子!”
“老佛爷,奴才——”
“滚!”
“嗻。”崔玉贵颤声答句退了出来,却已是脸色煞白、满头细汗,经过李莲英身边时,只向他打了一躬便匆匆离去。李莲英身子颤抖了下,仰天吁口气强自定神踱进屋,只见慈禧太后背着手在木隔子前来回踱步,兀自满脸怒色,几个宫女蹲在地下正收拾着摔碎了的瓷碗片。李莲英抿了下嘴唇,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叩着响头道:“奴才李莲英给老佛爷请安。”
“安你个头!”慈禧太后怒目扫了眼李莲英,回身坐在炕上,端杯欲饮却不想是空的,遂又放下。李莲英偷眼瞅着忙爬起身斟了杯奶子,复跪倒在地,小心道:“老佛爷息怒,千错万错皆奴才的错。奴才回头一定好生教教这些不长进的东西。”“他们不长进,那你呢?”慈禧太后呷了口奶子,犹自怒气未消道,“说,你昨儿个夜里去哪儿了?!”李莲英身子一激灵,沉吟道:“昨夜里家中奴才传话说奴才母亲告急,想着老佛爷已歇息,奴才便——”
“甚时的事?”
“戌时。不不不,亥时,是亥时。”李莲英微皱了下眉,忙道,“那奴才来时自鸣钟正敲十下呢。”
“你倒数得还蛮清楚呀?!”慈禧太后冷哼了声,转脸向垂手侧立一旁的小太监吩咐道,“去,将昨夜里当差的奴才唤来!”见那太监躬身便欲出屋,李莲英脸色顿时变得月光下的窗户纸一般,磕头如捣蒜般道:“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
“不拘紧些你便真不知天高地厚了!”慈禧太后冷笑两声,道,“去,唤皇上他们过来议事。回头你便待廊下雨地里,好好清醒一下!”说罢,径自案上捡了折子信手翻着。不大工夫,便听外间廊下传来纷杂的脚步声,慈禧太后放了折子,轻咳了声道:“都进来吧。”
“儿臣给亲爸爸请安。”光绪显得有点忧郁,进屋躬身道。
“臣——给老佛爷请安。”
“嗯。皇上,你坐炕边,你们几个坐那边杌子上。”慈禧太后点头应了句,瞅着奕譞亦在其中,眉头轻皱接着道,“你怎也来了?身子骨好些了吗?”
奕譞方自拿捏着身子坐了,闻听忙躬身道:“托老佛爷福,奴才较先时好多了。”
“这便好,这便好。来呀,与你七爷端碗参汤。对了,吩咐芬儿在外候着。”慈禧太后吩咐了句,抿口奶子轻咳道,“早起李鸿藻递折子进来,说是已修复的堤坝再次出现决口。既已言修复,又何以会再决口?我看还是这些奴才们不尽心做差!奕譞,你回头让拟旨,李鸿藻、倪文蔚贻误河工,着即革职,仍留原任;李鹤年、成孚并戍军台。”
“嗻。”
“离皇上大婚的日子这也不远了,我呢,也该撤帘子了——”似乎不胜感慨,慈禧太后仰脸长长透了口气。
“老佛爷——”孙毓汶眉棱骨抖落着,翕动嘴唇刚开口,只却被慈禧太后摆手止住:“此事就这样了。园子那边呢——叔平,你估摸着还得多少银子?”
“回老佛爷,照眼下这样子,只怕少说还得三四百万呢。”翁同龢拧眉小心道。
“是吗?”慈禧太后轻吟了句,道,“回头抓紧着些,总须在明年夏日前完工的。”
“奴才定会尽力。只如此数额,怕……怕砸锅卖铁、敲骨熬油也……也凑不起来。”
“凑不起来也得凑!”慈禧太后哼了一声,“谁误了差事到时我便唯他是问!”一句话说得众人目瞪口呆,仿佛把西厢房的空气压得紧紧的,人人都透不过气来。光绪咽了一口唾沫,细碎白牙咬着下嘴唇忍不住开口说道:“库里就那点银钱,却这也需那也要,翁师傅也确有难言的苦衷,亲爸爸便……便先缓过这阵吧,儿臣婚事可往后——”
“他有苦衷,难道我便没苦衷?”慈禧太后转身两眼盯着光绪,“莫不成你愿满天下都怪罪我这老婆子?!”
“亲爸爸,儿臣怎敢存这等大逆不道的心思?”光绪身子哆嗦了下,定神道,“只挤不出银子又有什么法子?”眼见慈禧太后额头青筋暴突,奕譞身子激灵一个寒战,不安地挪动了下,忙起身躬身道:“皇上大婚之日已诏告天下,是万万改不得的。园子那边也迟不得,我煌煌天朝却不能为老佛爷置个颐养之所,传扬出去颜面何存?老佛爷放心,奴才们定会尽力想法子的。”慈禧太后冷笑道:“不是尽力,是非得想出法子来!”说着,她冷眼瞥了下光绪,复坐了道,“十五那夜你们都见了你们未来的主子娘娘,只口头上说的,今日借着醇王爷也在,便都正式行个礼吧。芬儿──”她扬起脸朝外喊了一声。
静芬早就侍候在门口,忙进来蹲身道了万福请安道:“芬儿与老佛爷、万岁爷请安。”
“皇上。”慈禧太后摆手示意静芬坐了,说道,“你将这如意送与芬儿,也算正式定了这回事。”说罢,慈禧太后自袖中取了把攒着颗红宝石的翡翠如意递与光绪。光绪颤抖着手接了,忽电击般松开了手,“砰──”的一声响,翡翠如意已是一分为二。
“皇上,你好大的胆子?!”慈禧太后腮边肌肉急促抽动着。
“儿臣——”
“不乐意?!”
……
光绪没有言语,只眼中已噙满了泪花,移眼望眼奕譞,额头上由于紧张不安早已布满了密密的细汗。不知过了多久,光绪终闭目仰天暗吁了口气,点头哽咽道:“儿臣不是……儿臣乐意。”
慈禧太后扫眼奕譞,望着光绪冷哼道:“乐意便好。如意碎了,便将你贴身的那卧龙袋送与芬儿吧。”光绪转身颤抖着双手解了系在腰间的明黄卧龙袋丢与静芬,旋即转身向着屋外,泪水再也忍将不住走线儿般淌了下来。
眼瞅着众人跪地与静芬行了大礼,慈禧太后方长吁了口气:“好了,都跪安吧。”
奕譞偷手拭了拭颊上的泪水,嘴唇嗫嚅着道:“老佛爷,李鸿章奏称我北洋水师——”“这事我已晓得了,这一日咱盼了多少日子了,不容易呐!”慈禧太后脸上不易察觉地掠过一丝冷笑,旋即敛了干咳两声道,“派人自是应该的,而且应该派个有头有脸的过去。你的意思呢?”
“臣督着海军衙门,自当臣去方为妥当。”
众人一听,皆是一怔,光绪兀自懵懂间,忙侧身对着慈禧太后道:“亲爸爸,醇王爷虽说这阵子身子骨似好转了些,然终是虚着呢。儿臣恳请亲爸爸另委他人办这趟差使吧。”
“这——”慈禧太后深邃的眸子眨了眨,“醇王爷督着海军衙门,于事熟悉,若派他人,只恐不大合适。便李鸿章那奴才作假,亦不会晓得的。这可是件大事,丝毫马虎不得的。”
见光绪嘴唇翕动着还欲言语,奕譞急道:“老佛爷所言甚是。奴才定悉心用命,做好这趟差事。”
“你──”
“皇上关爱,奴才感恩不尽。奴才自服了李玉和药后,身子已是日见硬朗——”
“既如此,就这样吧。甚日子去,你与李鸿章商量着定。”慈禧太后不耐烦地打断了奕譞话头。
“嗻。老佛爷,李鸿章现……现已在外候着,可要宣他进来?”
慈禧太后眉头微皱,道:“他甚时回的京?”奕譞身子哆嗦了下,暗吁口气定了定神:“昨儿个夜里。奴才因水师有些事需与他商议,书信往来恐泄了消息,故让他来京一议。”
“甚事?”
“刘公岛水师炮台选址,奴才寻思多处不甚妥帖,故而让他——”
“嗯。”慈禧太后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我这会儿困了,回头再说吧。道乏吧。”
“嗻。”
待众人躬身退了出去,慈禧太后张胳膊舒心地伸了个懒腰,上炕斜倚在大迎枕上,任静芬为自己揉捏着,她的脸上,充满了得意的笑容。想想光绪方时那般作难情景,静芬眉头微皱,心里直塞了团破棉絮般纷乱如麻,不觉手上已用了力。慈禧太后不堪疼痛价挪了下身子,开口道:“用那多力做甚?”
“老佛爷。”静芬收神道,“我……我这心里总……总觉着不踏实,万岁爷他待我似乎压根便没有——”
“放心,但有我在,你便不会吃亏的。”慈禧太后冷哼了句,转脸向着屋外喊道,“进来吧。”瓢泼大雨直浇得李莲英落汤鸡一般,兀自懊悔不迭间,忽听得慈禧太后声音,忙应声跑了进来,扫了眼就窗前银舆中净了手,复换了身衣裳,忙上前换了静芬。
“晓得日后怎生做事了?”慈禧太后舒心地轻哼了声,冷冷道句,语气已较先时和缓了许多。“晓得了、晓得了。奴才定刻在心里。”李莲英暗吁口气,任雨水顺脸颊肆意向下淌着也不去拭,赔笑道,“奴才若是再犯了,老佛爷便将奴才这脑袋摘了做夜壶使。”
静芬见他这般奴颜,心中只觉一阵恶心,道:“要你那脑袋做甚?脏兮兮的!依我看,你这奴才若再犯了过错,直接去菜市口得了,那样老佛爷也省心些。”“是是,主子娘娘说得甚是。”李莲英打了个寒战,强自定神赔着笑脸道,“若奴才再有过失,便将奴才凌迟了。”
“女孩子家年纪小小的怎可说出这种话来?”慈禧太后笑着嗔怒了句,“日后做了皇后,一举一动都有着规矩的,若犯了,便我也会照规矩办的。”静芬听着,半惧半羞垂下了头,两只小手反反复复揉搓着衣角,不知如何是好。李莲英唔嘴轻咳两声讨好道:“主子娘娘端庄贤惠,绝不会犯过失的,便真——那也是奴才们的错。”
“就你嘴甜。芬儿,这奴才没甚别的,就一样,会服侍人。日后你也留心挑个可意的奴才,这样在宫里时日久了便不会觉着寂寞。”慈禧太后笑望着静芬。
静芬斜眼李莲英,哼了声:“芬儿服侍老佛爷、万岁爷,不会觉着寂寞的。要那奴才做甚?看着都让人觉着腻味。”
“是是,主子娘娘蕙质兰心,要咱这些下三滥的奴才们有什么用?”李莲英脸上不易察觉地掠过一丝冷笑,旋即敛了,满脸堆笑道了句。慈禧太后似察觉般哼了声,说道:“别说得那般动听,你那点花花肠子最好与我收在肚子里别往外显摆,知道吗?”
“奴才不敢,奴才不敢。”李莲英连不迭应声,咬嘴唇沉吟片刻,开口小心道,“老佛爷,奴才方外边听着园子那边又——不知可是真的?”“可不是嘛。”慈禧太后脸上掠过一丝不快,道,“唉,看来明年想住进园子是难了。”说着,慈禧太后端杯呷了口奶子,忽地,只见她眉头微皱,接口问道,“前阵子说修哪了?”
李莲英犹豫了下:“回老佛爷,是排云门。”
“排云门?上去便是排云殿了。”慈禧太后拧眉沉吟了句,眼中忽然掠过一丝寒光,阴森森道,“那么多银子修了个排云殿,立山这奴才——”
“老佛爷是怀疑那奴才做手脚?”
“嗯!”
“这——许有可能。不过这奴才是老佛爷您一手扶持上来的,想他还不至胆大如此吧。排云殿一处乃园子主体,花费比别处多些也是难免的。”李莲英抿嘴良晌,方干咳两声沉吟道,“老佛爷若真信不过,不如奴才明儿个去查查,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