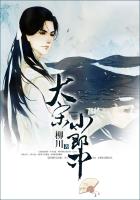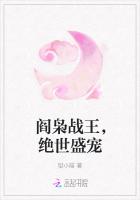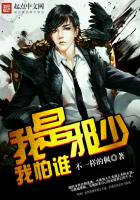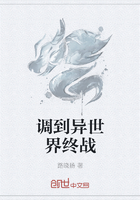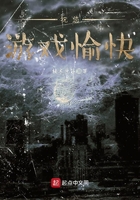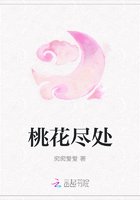(31)译《安贵王子歌一首并序》,《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三号,1943年。
(32)译《伊势物语》,连载于《艺文杂志》,第一卷一期、第一卷三期、第二卷十期。(其中第二卷第十期名《伊势习译》)1943年、1944年。
(33)《不如归剧本》(用日本德富芦花小说原作意),《同声月刊》,第三卷第三号,1943年。
(34)《樱花国歌话序》,《同声月刊》,第三卷第四号,1943年。
(35)《日本诗歌选:大伴卿赞酒歌、歌谣》,《东西》,1943年创刊号。
(36)译《水江浦岛子歌》,《北大文学》,第一辑,1943年6月。
(37)《怎样学日文》、《怎样学日文》(续),《中大周刊》,107、108期,1943年。
(38)译《寄居蟹》,志贺直哉着,《日本研究》,第一卷第一期,1943年。
(39)《新刊“日本美术之特质”》(一)(二),连载于《日本研究》,第一卷第二期、第三期,1943年。
(40)《万叶一叶》,连载于《日本研究》,第一卷第四期,第二卷第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第四卷第二期,1943年-1945年。
(41)译《城濠居》,志贺直哉着,《艺文杂志》,第一卷五期,1943年。
(42)译《崖》,白川渥着,《艺文杂志》,第二卷一期,1944年。
(43)译《谣曲“养老泉”韵调译》,《艺文杂志》,第二卷四期,1944年。
(44)《万叶集》(选译),《译文》,1957年8月。
(45)《源氏物语》(第一贴,《桐壶》),《译文》,1957年8月。
(46)《板车之歌》(节译),《世界文学》,1959年1月。
(47)译《谈花》,《世界文学》,1961年3月。
(48)译《金兵卫老爹》,《世界文学》,1963年3月。
(49)译《寄月》,《世界文学》,1963年11月。
(50)译《螃蟹的故事》,木下顺二着,《世界文学》,1964年第6期。
(51)译《飞鸟川》,世阿弥着,《世界文学》,1996年第6期。
3.钱稻孙的翻译
钱稻孙的翻译特点鲜明。其翻译每一个作品,都会想方设法找到一种中文的本土文体来传达其意境。从骚体、到骈体、到元杂剧、到明清话本、到昆曲、到白话。如此费劲心思、机杼自出,近代以来的翻译家鲜出其右者。
1941年钱译《万叶集》在《中和月刊》发表时,编者在介绍完万叶集之后,只一语概括了钱稻孙的翻译,“以中土之韵文,传彼邦之伟作。字斟名酌,鞮寄所难。读者必能知其用心之苦焉。”这种编者按,看似无所用心的客套语,不过确实也传出钱稻孙翻译的特点。钱稻孙的每篇翻译都在竭力追求原着的风格,他翻译的“信”,不仅是文字间的“信”,而且包括风格上的“信”。译《神曲》时用骚体,而《东亚乐器考》,由于是学术着作,钱译笔间有文言,严谨典雅。近松的净琉璃,用类似元曲的笔调,但又有区别,保持了日本的特色。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语调则类似明清话本。文洁若曾引钱译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鸳鸯殉情》中的一段来说明问题:
露华浓,夏虫清瘦;
情真处,配偶相求。
好不俊俏也风流!
粉蝶儿双飞双逗,
这搭那搭,旖旎温柔;
东风里,翩翩悠悠。
人家彩染的春衫袖,却当作花枝招诱;
并起双翅,悄立上肩头,
恰好似,仙蝶家纹天生就。
文洁若感叹:“译文韵字的安排,长短句形式的结构,以及化俗为雅、俗中有雅的风格,不禁令人联想到我国的元杂剧、明清传奇。”
钱稻孙的学生茅盾在《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神韵”与“形貌”未能两全的时候,到底应该重“神韵”呢,还是重“形貌”呢?在钱稻孙的翻译当中,以不同“形貎”来翻译不同作品,但“神韵”并未因此消失,反而相得益彰。不同的“形貎”正是由于对“神韵”的深刻把握而得来的。比如钱稻孙深入地领会了近松的净琉璃剧本的内涵和语言特征,才恰当地为其选择了每行字数不严格的文白结合类似元曲的韵文。钱氏对待这两种不同文体的译文,又不是像有的翻译家那样,一味地追求在字面上接近古代的杂剧或小说,而是先从容地吃透原作的旨意和精神,通过体会和领悟,化其为自己头脑中的思想和情感,再以退居次要的某种文体译述之。钱稻孙理解原文的层次,达到了心领神会。不仅对中日两国文字能融会贯通,更凭借卓绝的中文功力,以外就中,化为我有,却绝对不是生搬死套的硬译,而是作者理想的代言人。
相比于不少翻译大家,钱稻孙译着的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少而精;通观他的全部文字着作,10万字以上的不过《万叶集精选》、《东亚乐器考》和《近松门左卫门 井原西鹤选集》3部;其中《万叶集精选》是解放之前就开始动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用慢工夫细磨出来的,《东亚乐器考》则是受人委托,在极其困难和委屈的条件下经过一丝不苟地查资料,在1年多的时间中完成的,《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更是凝聚了钱氏生命最后8年的几乎全部心血而产生的经典之作。他的译着所以每出辄成为难以超越的传世精品,原因正在于,采用通过反复深入研习把原作的精神和气质化成自己头脑中的主导灵魂而后译述之的方法。从作品的选择上来看,钱译的作品和他个人的精神心智有相当大的契合性,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是“形貎”和“神韵”的合而为一,更重要的是译者个人的精神气质已经融化在其中。而钱稻孙的博学、多闻、能容,正是成就一个翻译大家所必需的素质。
钱稻孙以译古典见长,从《神曲》到《源氏物语》,其背后就在于其深博的知识和文化修养,是典型的学者型翻译。比如《源氏物语》在钱稻孙的翻译之后,丰子恺、林文月等均有全译本。试将《源氏物语》的《桐壶》一帖钱稻孙的译文和丰子恺的译文进行比较阅读,可以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钱译更求准确,对行文风格也刻意讲求。《源氏物语》被目为日本文学史上的《红楼梦》,钱译即以《红楼梦》的笔调出之。相对来说丰子恺的译文则更加符合现代白话阅读的习惯,明白易晓但少了些味道。如下面一段,钱译为“多管前世的恩情也不浅,早诞生了一位人间少有、清秀如玉的皇子。皇上计朝数日地等待已久,催着叫抱进来一看,好个清奇的孩儿相貌。”而丰译为“敢是宿世因缘吧,这更衣生下了一个容华如玉、盖世无双的皇子。皇上急欲看看这婴儿,赶快教人抱进宫来。一看,果然是一个异常清秀可爱的小皇子。”1964年,周作人被要求鉴定丰子恺的《源氏物语》译稿,结果将丰译稿为“恶俗”、“根本不可用”,在日记中记下“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文洁若予以校正,但恨欠少其实,此译本根本不可用”。周作人的评语可能多少有些意气成分,不过当事人之一文洁若事过境迁后仍然认为,“林、丰的译文水平相当高,但均未能超过钱稻孙”。翻译的高下是一个容易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非常明白的是,钱稻孙对他的翻译更加斟字酌句、精雕细琢,这也是当年出版社等不及他的速度,而将《源氏物语》交给丰子恺翻译的原因。
和一般的想象略有差异的是,钱稻孙最为丰产的时期是在1949年以后,翻译成为基本谋生和取得有限的社会地位的阶段。
怎样来估价这一情况呢?一方面1949年以后的工作保留了他的不少翻译作品,同时也使他的翻译思想和技术通过文洁若等继续传延。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些工作并不是他自由选择的。钱稻孙虽非治汉学出身,从骨子里对汉学传统有相当认同,在他的心目中,评价一个学者的学问怎么样,多数时候是看肚子里装了多少书,而不是看写了多少东西。所以他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但他这样的传统治学思路在五四以后即迅速边缘化。而且在政治波澜中,这样的作法也很难坚持,日据时期,他的不少翻译即是应景之作。虽然钱稻孙自己说《樱花国歌话》的翻译是出于自己的“一时兴致”,但这样的日本爱国诗歌集子的翻译总还能让人充分联想起当时是处于日本占领这样的大背景之下。1949年以后的诸如《板车之歌》、《民间故事剧》也明显和钱稻孙的兴趣略有差异。
从总的趋势上看,钱稻孙1949年以后的翻译风格也渐从古雅趋向通俗。在白话文当道的时代,钱稻孙的古雅化的翻译虽然可以让识者击节再三,但对一般的受众来说,难免曲高和寡。这既是钱稻孙的难题,也是翻译这门技艺的难题。
4.钱稻孙的日本认知
对于中国人来说,近代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史,首先是充满屈辱、痛苦和抗争的历史。从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卢沟桥事变,这一列的名词代表的是近代以来两个民族的特异关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其中经验更为复杂。单从数量上来讲,近代留学生以赴日本的最多,但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留日反日”。“虽然,留学日本的,一大批又是一大批,观光日本的,一船又是一船,学习日本语文的,一群又是一群,最近什么‘速成学校’啦,‘补习学校’啦,‘短期学校’啦,‘函授学校’啦,更是热闹的听听也要五花六花的。”但这众多的留学生中,在日本获得正面经验的是少数。加之中日之间连续不断的纠葛,“政治上反日”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和“留美亲美”、“留俄亲俄”形成明显对照。但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象是,有过留日经历的知识分子中,对日本文化持欣赏态度的也不乏其人。从早期的黄遵宪、夏曾佑,到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均可为代表。这方面知识分子的分量很可能是被低估的。钱稻孙的日本观在其中即有相当的典型性。
和多数留日学生稍有差异的是,钱稻孙赴日时年龄较小,就学从小学开始。且“日本以本国学生相待,不以中国学生相待”。
因为父亲是外交官,在日本时所处多为礼遇。钱稻孙对于留日学生受到的如周作人所说的“遇见公寓老板或警察的欺侮”那样的歧视和刺激感受相对不深。这都为钱稻孙培养出对日本的正面情感奠定了基础。
钱稻孙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与认同,首先在强调中国和日本需沟通了解而平心静气地看待对方。钱稻孙曾说:“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知识,魏志以后,直待奝然始一进,待倭寇而又一进,其所以不进者,自大思想之为害。”他一面批判着日本学者的“皇国口气”,一面则强调“我们对于日本确是太没研究了,此其原因,恐怕与其说是自大之故,毋宁说是太懒惰了。”如下文字虽非出自钱稻孙的手笔,但应当代表了钱稻孙面对国人的日本认识时的一个基本焦虑。“我国民众对日本,个个是盲目的:他们心目中的日本,不是‘日本小鬼子’,便是‘中国人一个人吐一口吐沫就可以把日本人都淹死’,总之是浪漫式的轻视日本,及至日本的大炮飞机打入长城,这种心理便一变而成浪漫式的恐惧日本了。”轻视和恐惧都是因为知之甚浅。1933年钱稻孙率清华大学日本旅行团的时候他就曾告诫团员:“不要以为日本什么东西都模仿别人,所以就看不起日本,要知道日本人的模仿往往是一种创造:什么东西,一经日本模仿,后来常常成为日本自己的东西了。”
在钱稻孙看来,了解日本当从文化入手。“了解文化是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彻底的、最直接的,而且最有趣味的途径。”钱稻孙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性,就是由于其关于吸收外来文化而为我所用。稻孙对此多有评论。“日本民族之克享今日地位与其过去奋斗实一脉相承”,“此四百年(指平安朝),最使吾人感兴趣者:一切摄自大陆之文明制度,无不逐渐向日本化走云,虽细微处,都可见此趋势”,“凡事皆见消化外来之文化,不甘于模仿,此一点,最为平安朝之特色。”“日本文化原有他的固有文化,而中间吸收、消化、调和了中国印度的文化,最近吸收、调和了袭来的文化。因此,日本今日实在有他的卓然的文化。”钱稻孙的期待是通过学习日本文化,从而借鉴吸收调和外来的文化而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
实际上,钱稻孙本人在为文和气质上已经体现了很多日本文化的影响。在译志贺直哉的《城濠居》的赘言中,钱稻孙如是说:“我译这一篇,出于一时的高兴,并无什么深义,但觉得我们的文艺青少年,很少写生物。这里一些景象,谁都日常观察到、经验到的,我们何妨也在描写方面,来多辟些门径?这于文艺的发展上,一定有所贡献。外行人话,不知专家以为何如,至于这一篇所写的主题,所寓的意思何在,我们从中又可以得到何等教训,读者明眼自能洞鉴,不用我这非文人来胡说一气。”这种故意把文意写淡的方法,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气质。完全找得到周作人的影子。在一篇描述日本香道文章的结尾,钱稻孙又写道:“一个清晨,消磨净尽。书非了不得的大着,却觉得很投我的兴趣。我并不懂香道,也并不想钻进里面去,也就未必再去细读了。”这里面体现了是与“茶道”、“花道”相通的日本文化中恬淡优雅的生活情趣,从容不迫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