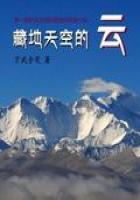当他又一次来看那堆土坟的时候,终于忍不住用锄头或铁锹挖开了坟墓,他拿着斧头的手在颤抖,棺材里有什么?是一具他的尸体?还是一具插满了缝衣针的桃木偶?或者别的意想不到的事物?他克服恐惧,挥动斧头劈开棺木,然而里面空无一物。胡枋坐在泥堆上,抱着头,苦苦思索。村长胡东诺家里的那只大黑狗,不知从哪儿蹿出来,毛发倒竖,冲着他吠叫不止。胡枋心想,总有一天,不是他砸烂它的狗头,就是被它咬掉卵袋。
一阵淡淡而奇特的香气飘入胡枋的鼻孔,这种香气既非草木所发,又迥异于野花,胡枋闭着眼睛,使劲吸了吸,这让他醺然欲醉。香气愈加浓烈了,香气的源头就在他的面前,结实、具体而不可摧毁。他一张开眼睛,就看到了胡小菊。他心里掠过一阵狂喜,他很久没有见过的、一直无法想起来的东西或事物原来是一个人,就是她——村长的女儿,未满十九岁的胡小菊,使全村男人神魂颠倒的天生尤物。胡枋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的一双手已冲动地抓住胡小菊的手,她就是解开这个巨大迷津的钥匙,尽管他一时无法将这位美丽的姑娘跟任何一把钥匙联系起来。
胡小菊任由他抓着,并没有把手缩回。她的眼睛仿佛笼罩着一层水雾,她美丽的脸庞,夹杂着震惊、迷惘、焦急之类的丰富表情。但胡枋无暇解读这些丰富的信息,胡小菊已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使他如受雷击:“胡枋哥,你真的疯了吗?我爸说你疯了,这是真的?你还认得我吗?”一个声音在胡枋的心底狂喊:“我没消失,我也不是透明人,我更没死——胡小菊现在就能看见我,并且能感觉到我的触摸——也许,我只不过是疯了——”这一股强烈的喜悦像洪水涌入他的头脑,在激荡,在咆哮,使他的思绪纷乱之至,但他还是松开了胡小菊的手。这是一双柔软纤巧的手,非常白,非常美。刹那间,他有点出神。胡小菊注意到胡枋在凝视她的手,脸颊微微涨红。
胡枋按捺内心倒海翻江的激动,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小菊,你能看见我?你能听见我说话?”由于多日没有开口,他的声音有点结巴而干涩,犹如晒干的鱼肉。
“我为什么不能看见你?你怎么啦?你的声音很奇怪。”
“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
“胡说!”
“没有一个人能听见我说话!”
“瞎扯!”
“这段时间你跑到哪儿去了?一直见不到你。”
“端午节一过,我就进城打工去了。我临走前不是跟你讲过吗?你一点死记性也没有!”
胡枋在发愣,他搜索枯肠,但怎么也想不起胡小菊跟他讲过这件事。但他想起了一个场景,当时太阳高悬,太阳很大,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太阳,明晃晃的,几乎撑满了整个天空。瓦蓝瓦蓝的天空被挤迫得只剩下一些边边角角。但阳光并不猛烈,阳光就像水汽在弥漫,胡枋感到全身凉飕飕的。他持着锄头在黄豆地里锄草,胡小菊忽然跑过来,撅嘴往胡枋的脸上亲了一口,吃吃笑着跑了。她就像树林里跳跃的一匹小鹿,稍纵即逝。胡枋抚摸着脸颊,怅然若失。这个场景就像一个梦幻,难怪他多日无从想起。现在,他望着胡小菊摇了摇头,脸上充满迷惘。
胡小菊仰着脸,问:“你想我吗?”
胡枋点了点头,但他马上觉察到胡小菊这句话的含义,赶紧又摇了摇头。
胡小菊叹息,幽幽地说:“在城里打工的日子,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但要到过年了,我才能回来。”
“要过年啦?”这段日子来,胡枋被卷入了迷津之中,时间对于他一片模糊,有时他感到时间停滞不前,有时又有时光倒流之感。
“再过三天就过年了,你挖别人的坟墓干什么?”
“我挖的是我的坟墓,我想看看自己是否躺在棺材里。”
“胡枋你真的疯啦。我爸爸说你疯了,我还不相信,原来你真的疯啦,可怜的胡枋——”胡小菊哭出声来,扑入胡枋的怀里。
胡枋感觉胡小菊的身体暖烘烘,但奇怪的是自己并无非分之想。与其说小菊对他的关切和亲昵让他深感意外,毋宁说他为另一个线索所吸引。他牢牢抓住了这一根线索:“小菊,你说胡东诺说我疯了,他是什么时候说的?”
小菊说:“昨天,我一回来他就说了,我还不相信。你瞧瞧你的样子——”她掏出一个镶嵌着小镜子的化妆盒,胡枋在镜子中看到一个头发蓬松、胡髭拉碴的头像,嘴唇焦干,大眼无神,颧骨高耸,瘦得像猴子的标本。这就曾经是生龙活虎的他吗?黄昏的暮色逐渐笼罩下来,并聚集在细小的镜面,胡枋忽然冲着小镜子咧嘴一笑。他一把将胡小菊推开,疯狂地往山坡下奔去,嘴里在叫道:“我是疯子,我是疯子,哈哈哈——”
当天晚上,胡枋兴奋得彻夜未眠,他感到原来那个无隙可击的谜团终于出现了漏洞,至少,他从千头万绪的乱麻中,理出了一条线索。原来他在村庄的消失或隐形,只是一个假象。他一时无法弄清楚更多情况。但他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针对他本人的陷阱或阴谋,那太怪异了,他怎么想也想不通,而他如果是一个疯子,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也许,胡东诺跟女儿说他是疯子,是为了向胡小菊解释胡枋的存在。也许,那个精密设计的陷阱,就是为了使他走向疯狂而最终毁灭。但设计这个阴谋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阴谋?尽管胡枋一时无法想清楚,但他总算对如何应对有了一些眉目。他不禁嘘了一口长气。他知道,只要他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子,很多事情就会像煮烂的饺子露出馅来。于是,他疯了。
除夕夜到了,他像一个幽灵在村巷上游荡。别人杀鸡买香烛去祭拜土地神,但胡枋却混在一群孩子当中抢夺哑掉的鞭炮。他衣衫褴褛,有时像鬼魂一样爬上土地庙的屋脊,土地庙上落满薄霜似的月光,他的脸在月光下苍白如纸。有时,他在相思树上跳跃攀爬,捷如猿猴,迅疾如飞。“胡枋疯了——”人们终于开了口,仿佛如释重负。一帮孩子跟在胡枋的后头,往他身上扔石头、烂泥和枯枝,嘻嘻大笑。胡枋冲着孩子,龇牙咧嘴,举起双手,乱挥乱舞,像被激怒的黑猩猩那样咆哮。孩子们“轰”一声四散而逃,犹如被驱赶的麻雀,但很快又聚拢过来了。在胡枋有如常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感知他的存在,但等到他“疯”了,却连小孩子也能看见他,并准确地朝他掷出石头。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胡枋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盲目的、悲伤的猎物,正在被一步步往林中设置好的陷阱或罗网走去,在劫难逃。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设置这个陷阱的动机以及设计手段,至今是一个谜。胡枋必须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倘稍有不慎,就会坠入万劫不复之境。他开始在头脑里像放电影一样,一个个过滤他可疑的仇家或他曾经冒犯过的人,但一无所获,他向来是善良之辈,从不好勇斗狠,亦非贪得无厌,相反还助人为乐,帮过别人不少忙。
他能预感到胡小菊是一个很有用的线索。他暂时未能获取更多有用的东西,胡枋一遍遍地掏捞有关胡小菊的事情,惟恐错过了一处细枝末节。他对胡小菊所知甚少,除了那天在山坡上,在那个大太阳之下,她羞红脸亲了他一下,他平时跟胡小菊可没怎么打交道。胡小菊是村长胡东诺的独生女儿,在十五岁之前,跟别的乡村少女也没什么两样。但十五岁一到,却出落得楚楚动人,那耸挺的乳房,细小的腰肢,丰满的臀部,尤其是那花骨朵似的俏脸,使全村的男人垂涎欲滴,几近疯狂。只有他胡枋没有胡思乱想,也许是胡小菊太美了,反倒让他生出敬畏之感。有时他注视着胡小菊,眼神里一片澄澈,跟他在夏日黄昏观看山冈上灿烂之极的云霞没有两样,或在林间跟一只五彩斑斓羽毛辉煌的大鸟遭遇相仿佛。这全无亵渎之意,纯粹是对美的欣赏、惊奇和沉醉。他联想起过年前和胡小菊在山坡上的遭遇,悚然一惊:莫非胡小菊爱上了他?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一度以为有了眉目的事情,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自从上次见到胡小菊,一连多日过去,他没再见过她。这些日子,他无时不刻都守在村口,如果胡小菊离开村庄,他肯定会看到的。
月黑风高。他知道现在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得见他(而以前的看不见恐怕是一种居心叵测的假象),所以大意不得。他像壁虎一样,贴着胡东诺的围墙翻越,潜入胡东诺的庭院,只见东厢房灯光闪烁,窗格子上摇曳着三个长短不一的黑影。他像狸猫一样灵巧,在地面上一个翻滚,到了窗前,窥见房间里胡小菊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犹如泥塑木雕。胡东诺老婆捧着一盘饭菜,不断地说:“闺女,吃吧,闺女,吃吧——你一天一夜滴粒米未进了——”胡小菊毫不理睬。胡东诺双手负背,绕着四墙踱来踱去,显得焦躁不安,而又束手无策。
胡小菊娘劝道:“过元宵你就是镇长家的人了,吃吧,吃点吧,饿坏了怎么办?”
胡小菊说:“我不吃,放我出去!”
胡东诺说:“现在还不行,到元宵节吧,李镇长家的小轿车就到家门口接你来了。现在你还不能出去,一放你还不是要往那个疯子家里走?”
胡小菊说:“胡枋去年端午节还好端端的,怎么我一回来倒疯了?”
“这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胡东诺说,“他失踪了几个月,一出现就疯了。也不知道他去过哪里,撞了什么邪。”
“你撒谎!我知道他哪儿也没去,一直呆在村子里。”胡小菊嚷道。
“他是不在呀,否则大伙儿怎么没见过他?”胡小菊娘嗫嚅着说。
“那好,胡枋为什么要挖自己的坟墓?”
“他挖的不是自己的坟,而是我的坟,长生坟。长生坟你懂不懂,就是生者预先觅好一块风水宝地,先修好坟堆,待百年归老后再入土为安。”
“长生坟怎么会有棺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在你的主持下,你为胡枋出了殡。而他根本就没有死,也没有失踪!”胡小菊冷笑道,“他就是被你逼疯的,对不对?尽管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居然可以让全村的男女老幼装出看不见他的假象!”
胡小菊娘说:“小菊,瞧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胡小菊痛哭失声:“都是我害了他。如果我不是喜欢他。你们就不会下这样的毒手。你们聪明过头了,如果他没疯,我肯定会屈服。但他既然疯了,我就要照顾他一辈子!想想看,这大半年来,他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呀。”
胡东诺说:“他疯是活该!谁叫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坏了脑子,跟任何人没有关系!但我要提醒你,还有比疯掉更可怕的事。”
胡小菊凄然一笑:“你们在谋杀!你们尽管去整死他吧,他死了,我也不会再多活一天。”
胡小菊娘喃喃自语:“吃吧,吃吧!”
胡小菊说:“放我出去!娘,放我出去吧。”
胡小菊娘捧着饭盆靠过来,说:“吃吧,吃一口吧。”
胡小菊站起来,她竭尽全力,想扑过来,将小菊娘手上的饭菜打掉。但由于她委实太过虚弱,她的手明明触及饭盆,但没有一丝力气。她闭上眼,泪水滚落腮边。
胡东诺两口子出去了,胡东诺反手关上房门,并挂上一把碗口大的大铁锁。刚才三人的说话,一句不漏全进入了胡枋的耳朵,他果然是落入了别人设计好的圈套。尽管疑窦丛生,他还无法理出一个头绪。但他对自己有了信心。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而他其实是在装疯,这一点很重要。只要他有足够的耐心,就可以揭开真相并反败为胜。当务之急是必须让胡小菊活下来,并重获自由。他望着灯泡昏黄光线下胡小菊凄婉而憔悴的脸容,一股热浪涌上喉头。他几乎要哽咽失声了。这是一种十分陌生而奇特的情感,他从来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