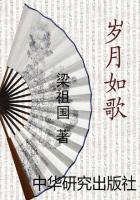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我想到了《金日成将军之歌》,我十分喜爱这个富有东方情调的歌曲:“长白山一条条,染遍血的足迹,鸭绿江水曲曲弯弯,飘着血痕……密密林中漫漫长夜……不朽的游击队长你说是哪一个?英雄的爱国军人你说是哪一个?啊,金日成将军的名字……”
我也喜爱我国作曲家吕骥写的“朝鲜人民从血泊中站立起来,再也不能回到血泊……再也不能重新做奴隶……当心烧死……自取灭亡……”而且我始终感到这首歌的旋律与《金日成将军》之歌非常靠近,是后者的一首姊妹曲。
我每天都研究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捷克年产多少钢材,比利时年产多少,我都注意,更不要说顿巴斯煤矿和德聂伯水电站了。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斯大林在二战胜利后的演说,他许诺,十五年后苏联的年钢产量是六千万吨,听众是暴风雨般的掌声。我祝祷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早日灭亡,社会主义的早日胜利。顺便说一下,当笔者写下这一切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钢产量已经是两亿吨以上了。
我看了朝鲜拍的纪录片《给世界有良心的人们》,看到穿着白色长衫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活动家朴正爱女士的讲演,我认定了美国是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深对于美国的认识,改变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我很高兴我对美国从来没有好感,早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美国大兵皮尔逊在东单广场上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的事件以后,我就视美国为敌人了。我读到过一篇文章里的数字,说是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援助了蒋多少多少颗子弹,一人一颗,足够把全中国人民杀光。
随着形势的发展,青年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每天都有青年写血书要求上前线支援朝鲜人民军的。志愿军过江后我们组织发动大家写慰问信,我们区里的干部星夜也做过炒面粉,供给朝鲜战场的人民志愿军食用。各单位的团支部纷纷上街宣传,二十三中(原新知中学,是庄则栋的母校)的团总支干部到街头演小歌剧《渔夫恨》,是说美军的飞机炸死了我国的渔夫的,感动得围观者痛哭流涕。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聆听赴朝慰问团的来自朝鲜前线的报告,我们充溢着类似《英雄儿女》中王成的那种“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准备与老美同归于尽的情绪。我们在学习会上朗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高唱《白云山》。我们传诵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全市的中学生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集会听杨作家的报告,他的声音低沉,听众根本听不清楚,主持会议的人出来给大家讲,由于杨朔同志感情丰富,不能大声讲话,请大家注意听。
这个期间我还兴奋地参加了从大中学中招收军事干部学校学员的工作,领导上给我们讲授了国防建设的前景,通过我们的手,把最优秀的青年男女输送给了解放军。
如此这般,度过了一九五○与一九五一年,仍然是轰轰烈烈,仍然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一九五二年与一九五三年,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不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一九五二年伊始,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河北高中新派来的校长被说成“大老虎”,在大会上宣布逮捕。数月后无罪释放。各单位都有指标,要揪出多少多少万元的贪污犯来。这种搞运动的方略开人眼界,带有一种农民的简单易行与毫无科学性法制性可言的原始天真色彩。我们熟悉的团市委一位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党员出身的同志,在南方搞土改,因涉嫌三反中的问题被上了铐子押送回京。还有一件事令人无奈,团市委一位男同志被揪了出来,其妻是一位皮肤白皙,脸颊绯红,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同志,立即与他离了婚并与另一位比她年轻不少的人结了婚,不久,原丈夫吗事没有了,但是老婆已经丢啦。
我的注意力并不在运动的搞法、得失与后果,我深深为运动所吸引和激动,是为了一种气氛和一种信念,只要有这种气氛和信念,运动无论怎样搞,发生什么偏差,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对的,至少是值得的。区里的干部到各单位坐镇和督战,老百姓对于国民党的贪官污吏的反感记忆犹新,共产党能够这样大张旗鼓地肃贪,无不额手称颂。区三反五反办公室常常是彻夜不眠地整理各单位开展运动的情况与战果。到处都是庄严的战斗气氛。
我们的区委位于东四十一条39号,是一个三进的大院子原来的敌产。团委与妇联位于前院的一排南房,区委位于主院,中间是美丽的垂花门,高高的台阶。主院西房是组织部,东房是宣传部,正房是书记与办公室。后院是集体宿舍,通向一个后门,十二条。三五反办就设在正房的办公室。恰值寒假,一些学生党员调入区委搞运动,其中就有女二中的崔瑞芳。我曾经在午夜到她们的办公室去,我很感动。我一直想写一个话剧,一处大大的办公室,冬天,巨大的火炉,午夜,挂钟敲响了十二点,传来了新的消息,领导运筹帷幄,荡涤着旧社会遗下的污泥浊水。年轻人幻想着一个新的水晶一样的光明世界。有同志间的深情与恋情,有敌人的千奇百怪的手段企图腐蚀革命,扭曲革命。有自己人的掉队,颓废和自私;有青年人的好奇与天真;有天使一样的献身热情与对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的追求,生活充满希望……
当我想到崔瑞芳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呼啸和旋转。当我想到她与我都生活战斗在这一个大院里的时候我觉得十分温暖。我当然找得到一种适当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情。我与她说话,我借给她书看,我找她散步,我给她写了极其美丽动人的信。
……我记得这一年的三月六日晚饭后我们去贡院西街市委党校礼堂听报告,报告会后我步行送她回西单住地,我们缓缓地走到了西单。我一个人又从西单走回了东四十一条。我惊异于灯火璀璨的北京夜晚的辉煌美丽。当然那时候不可能有太多的灯,由于我回来时街上再无一人,我只觉得千万盏灯在为我而照耀,我幸福得如同王子。
当时我只有十八岁,瑞芳只有十九岁,我虽然不大,但已经是干部,已经是小“领导”,已经自以为胸有成竹。而我的追求使她情绪极其波动,有几次她正式拒绝,又有几次我们恢复了来往。所有这些都无比地美好,被友好地拒绝竟也是这样地美丽。
一九五二年我们组织了马特洛索夫夏令营。马特洛索夫是一位苏联英雄,用身体堵住了法西斯敌寇的碉堡枪眼。有一部影片《普通一兵》讲的就是马特洛索夫的事迹。我们请作曲家郑律成谱写了营歌:
我们有一个,
亲爱的朋友,
他就是马特洛索夫普通一兵,
普通一兵是我们中国青年的心,
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我们热爱自己的人民。
八月的一天,一批学生,一批团员骨干,扛着帐篷、食品用品,浩浩荡荡,行军到西苑的一处空地,安营扎寨,开始了露营生活。快乐的集体生活让我非常感动。露营结束后我写了一篇长长的报道,报道与工作总结也受到了本单位领导的赞扬,报道寄给了北京日报,最后变成了两条简讯,每条不足一百字,但也还是刊登出来了。
九月下旬,我们忙于准备国庆节的节日活动。已经表示不怎么打算和我发展下去的瑞芳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去不去看深夜举行的阅兵式预演。我们的一切都是与伟大的国家伟大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不仅一起看了阅兵式预演,不久,我们去设备最好的东单大华电影院看了描写苏联海军生活的彩色影片《在和平的日子里》。
三反五反的热烈开展与平稳结束,给人以不同的感觉。与此同时,朝鲜战争陷入胶着状态,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开始,停战已只是时间问题了。报纸上集中宣传的已不是战争,也不是三反运动,而是大规模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制定。上级明确指出,欢庆解放与民主改革的阶段已经结束,现在的任务是建设,学生的任务是学好正课,学校团组织的首要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学习。团中央领导蒋南翔并且指出,团组织要做到不要“捣忙”。他没有用捣乱这个词,留了面子。我立即想起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熟悉的一些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需要学习。我充满了历史感,乃至于沧桑感。
也是巧合,这一年秋天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苏联女诗人阿里格尔的诗剧《卓娅》,它的主题歌叫做《蓝色的星》,唱得软绵绵:
生活是多么幸福,
生活是多么美好,
我愿意永远这样生活,
让蓝色的星儿照耀着我。
很可能这首歌曲并不算成功,但是它带来了一种新的情调。北京召开了亚洲与太平洋和平会议,我们的团市委书记许立群还讲过有些市民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会议的意义,传说什么“要和了”(按:“和了”云云是中国内战时期常见诸报端的语言)。我有一次机会和拉丁美洲的客人座谈。此前我读过一些对于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报道,熟悉并崇拜像苏联的爱伦堡、法国的法齐、阿拉贡、约里奥?居里这些和平人士。我感觉到中国人的生活正在变得国际化。我也与苏联共青团的书记谢米恰斯特尼(后来曾任KGB的领导人)座谈过中国的青年工作。我在与拉美朋友座谈的时候朗诵了我的一首小诗,表达对于世界人民团结与捍卫和平的歌颂。
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世界、和平、生活、幸福、岁月、日子这些字眼,这些字眼令我感动莫名。我在新恢复的杂志《译文》上看到的头题小说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描写新从大学毕业的女建筑师尼娜怎样在建筑工地上体验到了艰难与幸福,所谓走向生活,所谓和平建设,所谓城市与人的崭新的前途。我学会了在夏季喝冰镇的啤酒,就上炸花生米使我美得像上了天。我常常在夏季的周日去什刹海游泳池,我想不到自己已经活得这样滋润。我与姐姐还购买了旧货留声机。那时的苏联唱片八角钱一张,虽然转速常有快慢的差别,我们还是从这个留声机上听到了尼基丁唱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米哈依洛夫唱的《沿着彼得大街》,尤其是聂恰耶夫唱的《列宁山》,“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峻峭的山岭使人神往……当我们回忆少年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首都,我们的首都,我的莫斯科!”它的抒情和阳光,赞美和纯净,标志着我的青年时代的福气,青年时代大唱《列宁山》样的歌曲的人是幸运的,即使我后来发现列宁山毫无峻峭,莫斯科大学的斯大林式建筑显得傻气,而苏联的阳光明媚后边有着太多的麻烦和不明媚也罢。
而听到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时候我会感动得泪流满面,一听到收音机里放这个曲子,我就会恳求周围的同事或者家人,允许我关闭灯光,拉上窗帘,我要在黑暗中静听这首乐曲。我的这种表现,当然,也成了“生活会”上的一个话题,为什么王蒙有这么多不健康的怪癖呀。
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胜利以后的事情,北京的解放使我一直处于革命的大兴奋中,我甚至于想,由于我年纪小便于隐蔽,我也许会被派到台湾去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我喜欢地下的革命生活,传单、印刷所、秘密接头、暗号、群众运动与情报传递……我看苏联影片《马克辛三部曲》,对彼得堡的工人运动如醉如痴……俱往矣。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人民掌握了政权的和平的日子有多么美好,多么快乐,多么迷人但是回忆地下工作者的豪情与神秘,我又略感失落。
一九五三年我十九岁,十九岁的王蒙每天都沉浸在感动、诗情与思想的踊跃之中。这一年开始了我的真正的爱情与真正的写作。这一年内心的丰满洋溢,空前绝后。我想过多少次,如果有一个魔法,可以实现我的请求,我当然不会要钱,要地位,要荣誉,要任何古怪离奇;我要的只是再一次的十九岁。
感谢上苍,感谢历史,让王蒙在少年青年时代经历了那么多崇高、危险、浪漫、胜利、激情和阳光。显然,我们面临着新的时期,新的特色。我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