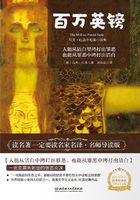生命中有些事看来真是注定了的,老天要帮你,鬼神都挡不住。
报社在过了半月表面上平安无事的日子之后,又出现了一件大事。
这天下午,有个人贼一样地闪进秦雄的办公室来。这人叫邬伟,是广告部的一个策划员,外相长得跟猴子似的,个子又小,乍一看像刚从深山老从里逃出来,秦雄对他的第一印象如唐玄宗对文人的评价:“此人固穷相也。”平时他们接触不多,他又刚来报社半年,报社一百多号人,平时对这样一个其貌不扬还有些猥琐怪异的小角色,他是不会关注的,但秦雄识得他,因为他名声不好。
这人眼睛骨碌碌直转,站在那里自说自话地介绍自己的名字和部门,这些秦雄都知道,而且他特别讨厌他,尤其讨厌他的来历。邬伟混进报社的经历比捞仔还要荒唐,听说他只是个小学文凭的外地人,几年前竟在伶南文报社做过两年的记者。说来好笑,当初他连简单的消息都不会写,却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好几篇颇有分量的通讯,主要领导很重视,就找他谈话,可他却说出“新闻就是报道,报道就是采访,采访就是问话”这样无知的鬼话来,让领导深感蹊跷,一查,这人是伪造大专学历混进来的,而且那些文章都不是他本人写的,他在外面雇了个老乡做枪手,一开始一般的消息由他去采访记录并拿资料回来,由老乡执笔写,后来则是带着老乡单独行动采访写些通讯,慢慢地也学会写消息了,要不是出了几篇有份量的通讯,他的来历还没人知道。按说这一来他的出路应该是不用问了,可文报的领导是一位慈祥的长老,看他模样可怜得像个孤儿似的,还把他留下了,只是换到广告部去拉广告,而他雇的那位不得志的老乡也因祸得福被招进去做了编辑,现是该报的文艺部主任。而邬伟呢,广告还做得比较出色,只是后来不知怎么又跳进党报来,还做起广告策划,这就让秦雄羞于向外人提起本报还有这样的人了。
秦雄问:“有事?”邬伟说:“没事没事,就是请领导有空的时候,多到我们部门去指导指导工作。”
秦雄想,这人真是厚黑大法练到家了,这话咋也轮不到他来说,凭他的职位和身份,也不可能说出啥子内幕消息来,便不耐烦地说:“我有事,改天再说吧。”可邬伟赖在那里不走,还自己去倒了杯水喝,过了好一会,又作贼似的从怀里掏出一份报纸来,一看,是本报三天前的报纸。邬伟指着摊在眼前的时政版,眨巴着眼神秘地说:“你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就看标题。”
秦雄把所有文章标题都看了一遍,没发现有何不妥,邬伟又用手一指,眼睛定定地瞪者他:“这一篇,再看看这另外一篇,连起来读,有什么问题没有?”
这一看,秦雄还真是如新时代发现恐龙一样大惊失色了:这一篇的标题是“市领导×××要求抓好××××理论学习。”紧邻下方是1/4版面的性病广告标题:“烦!烦!烦!”三个字还特显目,内容是“患了梅毒、淋病、湿疣、泌尿系统感染,怎么办?”等等。
显然,这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可堪称是一个政治事件!比起前次发生的问题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秦雄马上去把门锁按死,问:“都有谁知道?”邬伟说:“没有谁,就我一个看出来。”秦雄坐着想了好一会,说:“这事就你我两个人知道,不能对外去说。”
邬伟的脸色就由明转暗,疑惑说:“你不打算让外人知道?传出去对你有利啊。”秦雄说:“个人斗争事小,报社名誉事大,不能让外人看出来。”邬伟说:“领导你风格高啊,可人家跟你比风格吗?还把你往死里整呢,我们胡主任就加入了他们一伙呢,你不知道?”他说的是广告部主任胡冬。秦雄说:“让他们闹去吧,任何事都要以公为大。”
邬伟还不死心地说:“如果你不方便出面,我负责把它捅出去。”还用食指作了个猥亵的动作。秦雄严厉地说:“不要再说了,就这样,不能外传。”
邬伟本是想以自己的重大发现来邀功请赏的,这下心里好失落,一脸疑惑和狼狈地往外走,秦雄又安慰性地补上一句:“不管怎么说,要谢谢你的提醒。”邬伟这才稍露喜色,点头哈腰地去了。
秦雄虽然已在心里拿定了主意,但想着阮社长半月前对他的吩咐,又匆匆地走进莜青的办公室,说:“这里有个大事,我们商量商量。”
莜青在他的点拔下看明了玄机,顿时面如土色,平时沉着智慧的她第一次显得手足无措,求救似的望着他,喃喃道:“怎么办呢?你看怎么办呢?这事我也要负责啊。”
秦雄说:“正因为你也要负版面的责任,我才决定把这事压下来,要不,我早把它捅出去了。”莜青说:“可这事压得下吗?别人说不定也会看出来的。”秦雄说:“都过去三天了,很难有人留意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莜青问:“那个邬伟可靠么?”秦雄说:“也应该不成问题,放心吧”莜青说:“老秦,感谢你这个时候还想着我啊,要换了别人,我跟钟义一起完了。”
秦雄回到办公室,想着莜青那张惶而可怜的模样,心里犹豫极了,但最后还是狠下心,把报上两个标题用红笔一圈,中间连上一条线,装进了一个标准信封里,又用左手在信封上写下了两行字,密封好,出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