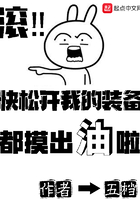我浑身战栗不止。我决定跪下做祷告,希望能告别过去那个坏孩子所做的一切,重新做个好孩子。于是我跪在地上。可是祷告的话到了嘴边却说不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来呢?要想瞒过上帝是不可能的,自然也不会瞒过我自己的。我知道为什么祷告不出来。这是因为我的心还有邪念啊,因为我在耍滑头搞两边倒的做法。我一面在装作要告别过去的行为,可我心中还抓着那件最大的罪过不放。我想让我的嘴上说,我要做规规矩矩的事,做清清白白的事,还想给那个黑奴的主人写信,告诉她他如今的下落。可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是个谎言,上帝也知道这是谎言。做祷告可不能撒谎,我算是知道这点了。因此,我心里就烦恼到了极点,不知道应该如何才好。最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在心里说,我要把这封信写出来,看我写完了信还能不能做祷告。嘿,真奇怪,想到这里我心里马上就觉得像根羽毛一样轻松,所有烦恼都随风而去了。于是,我找出一张纸和一支笔,又兴奋又激动,坐下来写道:
华珍小姐,你的黑奴杰姆逃到了离这里两英里远的派克斯维尔村,被斐尔普斯先生抓到了。如果你送来赏金,他就会把人放了。
哈克贝利
我感觉挺轻松,好像身上的罪过一下子都给清洗得干干净净了,这种感觉我这辈子还是头一回有。我明白现在就能做祷告了。不过我并没有马上做,而是把那封信放下,坐到那里想。想一想我差一点儿误入歧途,下到地狱,现在我做的这些又该有多好。然后又接着想,不禁想到我们沿着大河漂下来的这一段日子。我仿佛看见杰姆就在我眼前,我们在白天,在夜晚,有时在月光下,有时在暴风雨里,坐在木筏子上漂啊漂,一起说笑着,一块唱着歌。想了这么多,我好像找不出一点儿让我对他狠起心来的理由,并且想到的全是他的好处。我总是想起他值完了他的班,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又接着替我值班。我想到我从那场大雾里回来,还有家族械斗那次,我在沼泽地里又一次找到他,还有好多这样的时候。他是多么的高兴,对我多么亲热,他总是亲切地叫我宝贝,总是为我做他能想到的一切,一直对我都那么好。最后我想到了那一次,我告诉那两个人说我们木筏子上有人害天花,救了他之后,他对我那么感激,说我是老杰姆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现在唯一的朋友。想到这儿,我刚好转头向四周看,我又看到了那一封信。
这件事真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拿起了这封信。我的手在发抖,因为我明白,我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并且永远不能反悔。我放慢了呼吸,认真思考了一分钟。然后我对自己说:“去他妈的吧,下地狱就下地狱吧!”扬手把纸撕掉了。
这是个可怕的想法、可怕的话语,可我还是说出这句话了。既然我说出来了,就不再去做什么改过自新的事了,我要把这件事统统甩到脑后。搞歪门邪道这些事才是我的老本行,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正经事我干不来。从现在开始,我先干上一件事,就是把杰姆再偷出来,叫他摆脱奴隶生活。要是还有比这个更坏的事,我也去干。因为我既然干了这一行,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
于是,我就开始想用什么办法下手。我在心里想了好多种办法,最后确定下来一个我认为比较好的计划。到了晚上,我悄悄地划着木筏子来到了大河下边一点儿那个树木茂密的小岛。到了那里,我把木筏子藏了起来,爬进窝棚睡了整整一晚上,天快要亮时才醒过来。吃过早饭,我换上了那身现成的新衣服,把其他衣服和零碎东西打成一个捆儿,划着独木舟到了对岸。我沿着岸边的水面向下游划,我估计离斐尔普斯家不远了,就靠了岸。我进到了树林中,把一捆儿东西藏好,然后在离岸上的一个机器锯木厂下边半英里远的地方把独木舟灌满水,装上石块,沉入到水里。等我需要时再来找它。
做完这些,我走上了大路。走到那个锯木厂旁边时看到一个招牌,上面写着“斐尔普斯锯木厂”。我又继续朝前走,到了离锯木厂两三百码之外的农庄,我仔细观察着周围。现在天已经大亮了,可是周围却没有一个人。这对我来说是最好不过了,因为我只是想把这一带地方摸清,不想见到什么人。按照我的打算,我本应从下游不远的那个村庄走过来,是不应该路过这里的。于是我就随便看了一下,就急忙朝镇子上走去。没想到,我见到的第一个人竟会是公爵。他正在张贴演出“王室怪兽”的海报——只演三晚,和上次一样。这两个骗子,脸皮还是这么厚。我来不及躲开,刚好和他碰了个对面。他好像大吃一惊的样子,说道:
“你好!你这是从哪儿来呀?”然后,他又好像很高兴很关切的样子问道,“木筏子呢?你把它藏好啦?”
我说:“我还正想问大人您呢?”
他显得有点儿不高兴了,说道:“你问我,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大人。”我说,“昨天我在那个酒吧看见国王醉成那样,我就想,他几个小时内酒是不会醒的,我们也没法把他弄回去。因此,为了打发时间等他,我就在镇上随便溜达。一个人走过来,请我帮他把船划过河对岸,再顺便带一只羊回来,并给我一角钱的报酬。我看有钱可赚就跟着他去了。他把羊赶到船边,让我一个人在船上拉住绳子,他到羊后面去推。可是羊力气太大了,我没拉住,它挣脱绳子跑了。我们又没有带狗,只能在后边追着满地里乱跑,一直到天黑羊累倒了才抓住它,然后把它运过河来。我这才向下游找木筏子,可是到了那里一看,木筏子不见了。我就以为是你们俩惹上了什么麻烦,慌忙逃走了。可是你们把我的黑奴也带跑了,那是我在这世上仅有的一个黑奴呀。现在我远离家乡,一分钱也没有,连木筏子上的一点儿东西和黑奴也没有了,所以我就坐在地上哭起来。后来我就在林子中睡了一夜。可是木筏子到底去什么地方了?还有杰姆,可怜的杰姆他现在怎么样了?”
“见鬼,我怎么会知道?!我是说,那木筏子的下落我不知道。那个老笨蛋做了一笔生意赚了四十块钱,然后到酒吧和那群二流子赌钱,半块钱的赌注。等我们找到他时,已经输得只剩下付酒账的钱了。昨天深夜我把他弄回去时,发觉木筏子不见了,我们想是你偷了木筏子甩了我们,顺河逃走了。”
“我怎么可能丢下我的黑奴呢?他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黑奴,我唯一的财产呀。”
“我想也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已经把他也看成我们的黑奴了,真的,我们就是这么想的,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因此,当我们找不到木筏子,我们又穷得没有一分钱,也没有别的生计,只好再上演一次‘王室怪兽’。为了准备这个我忙得不可开交,好长时间没喝上一口水了,喉咙干得快冒火了。你那一角钱呢?赶快给我。”
我身上有不少钱,但是只给了他一角,并央求他用这钱买些吃的东西,还得分给我一点儿,因为我身上只有这点儿钱,从昨天到现在我什么东西都没吃呢。他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大声对我说:
“你那个黑奴会不会把我们的老底儿都说出来?他那样做的话,我们非把他的皮扒了不可。”
“他已经逃跑了,还向谁说?”
“他没逃跑!是那个老笨蛋把他卖了,一分钱也没分给我,现在钱也花光了。”
“把他卖了?”说着我就哭起来,“他是我的黑奴呀,那是我的钱。他在哪里?我要我的黑奴。”
“不要哭了,你的黑奴回不来了,就这样吧。你再哭也没有办法。你也想揭发我们吗?我有点儿不相信你。你听着,你要敢揭发我们的话……”
他停住没再说下去,可是他这么凶恶的眼神,我过去从没见过。我还是不停地抽泣着说:
“我不想揭发谁,我也没时间去揭发谁。我得赶快去把我的黑奴找回来。”
他看上去有点儿左右为难,站在那儿,演出海报在他手臂上随风飘动,他皱着眉头在用心思考。最后他说:
“我给你透点口风。我们准备在这里停留三天。如果你答应不揭发我们,也不让你那个黑奴揭发我们,我就对你说去哪里能找到他。”
我答应了他,他这才说:
“一个农民名叫赛拉斯·斐……”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他打算实话告诉我。但是,当他停顿一下,又仔细考虑的那个样子,我估计他又改变了主意。事实果然如此。他不肯相信我,他是在想办法把我支走,让我在这三天都不能妨碍他。所以没多久他又说:
“把杰姆买走的人叫阿兰布姆·福斯特……阿兰布姆·格·福斯特,他的家在离这儿四十英里远的小乡村里,沿着往拉法耶特去的路走就能找到。”
“好吧,”我说,“三天我就能走到那儿。今天下午我就走。”
“别等了,你马上就开始走,不要耽搁时间,一路上也不要和什么人说话。把嘴巴闭紧点儿,一直朝前走。这样你就不会给我们惹祸了,听到没有?”
这正是我最想听的话,也是我故意引导他这样说的,我希望无拘无束地照着原定计划自己干。
“你赶快上路吧,”他说,“如果你不想多费口舌,你可以直接对福斯特先生说。没准儿他会相信杰姆是你的黑奴,有些傻瓜不会要证明看的,反正我听说过大河下游南方这一带有这样的傻瓜。只要你对他说那告示和赏金全不是真的,你再给他说明白为什么要耍这些花招,没准儿他会相信你。赶快走吧,你想跟他说什么都行。不过不要忘了,从这里到那里的路上不许多嘴。”
于是我就走了,往乡下的路上走去。我知道他在紧紧盯着我,所以我没有回头看,不过我会让他自己盯得不想盯的。我朝乡下的路一直走了一英里多远才停了下来,然后钻进树林里,沿着林间的小路往斐尔普斯家跑去。我认为最好不要耽误时间,马上着手按我原来的计划行动。因为我想在这两个浑蛋走之前堵住杰姆的嘴,让他不要说太多。我不想跟他们这路人再有什么来往。我早就看够了他们的可恶行径,只想把他们彻底甩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