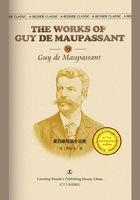在八月十七八日,又使南门瓮城边茶铺里的一伙人大为高兴起来,尤其是傅隆盛。这因为接连两天,颇抬了二十几个伤兵回来,甚至还有一位军官。何以知其为军官呢?即因军帽上有一道金线绦。
当伤兵抬到城门洞前时,这伙善心人呐喊一声,全扑到茶铺门前,睁着大眼,射出锐利的目光,恨不得一直射到他们创伤的底里。差不多轿子才走进城门口,这里欢笑的声音便高高腾了起来,似乎在戏场里看了一出什么好戏似的。而微感美中不足的,受伤者乃是陆军兵士,并非可恶的巡防兵。
大家推论起来,为什么这两天会有这么多的伤兵?“这还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恐防还有多少我们没有看见的哩!”不消说,仗火一定打得很厉害了。在那些地方打呢?有主张仍然在新津河边的,傅隆盛则力主绝不是还在那里,一定在黄水河一带,“如其在新津河边,打伤的人,咋能一天的路程,这早就抬拢了?我听见说过,现在打仗,并不像从前随时都可以打,现在总是在天见亮时打,打到吃早饭时,两下就鸣金收兵了。”他的话自然是对的,因为是专家。不过为什么全是陆军呢?这只能说:“怕是巡防兵全打死完了!”傅隆盛更有一说,是营务处曾招了三营新兵,拨交陆军且练且战,老兵打仗是懂得战法的,怎样放枪,怎样躲避。新兵就不懂得,打起仗来,自然只有吃亏的。“说不定抬回来的这些伤兵,都是些新毛猴儿罢?”他一说到此,心里便打了个寒噤,陈荞面兵名叫做陈占魁的,正是新兵!该没有他罢?为私情起见,伤亡的不能全是新兵,然为公义起见,伤亡的又不能不全是新兵。
傅隆盛如其有点二十年后一般人常常挂在口里的科学精神的话,他很可以亲身跑到军医局去,查问一下,有否陈占魁这个人?有了,自然可以澈底知道此次的战争情形,即使没有,也可以别种方法,打听得出官军确实的胜败,何致枉用心思的推测呢?但是,时代的巨轮,尚未转到,也幸而傅隆盛没有像现在新闻记者似的,去到军医局向受伤官兵探询,尚得使他们借以自慰的假定,多保留了一两天;不然,他们失望的惨痛,断不会等到十九日,新津确实被官兵占领了,才会感到的。
原来在八月十三日,东门外河里的大小半头船四十只,已借着若干人的脚,徐徐走到了新津河边。同时,赵尔丰下令,即日进攻,只许进,不许退,退者定以军法从事,先从带兵大员办起。如其在三日内将新津克复,赏银二万元,七日内赏银一万元,官弁等从优升级。这么一来,官兵才精神一振。并且由制台衙门传到的消息:岑宫保是断然不会来的,四川的事仍倚重着赵大帅在,大家荣衰的命运犹然在他的手上。赵大帅是誓死也要将新津攻下的,大家须得把他这个面子顾全,也才对得住上司呀!
并且田振邦就进驻黄水河,向朱庆澜表示:如其陆军真个怯战不进,他便要把巡防兵调为先锋,亲自统率进攻了。朱庆澜自然不肯把这面子全让给他,使自己二十几天的功劳,废于一旦。因即倡言:陆军绝非怯战,只因以前无渡河之具,今既有了,断无不能把新津克复之理。于是自己就进驻到花桥子来督战。所以十四日这天,真实的战事就开始了,打到下午,便有八百多陆军把三道水中比较窄,比较小,比较流得缓一点的第一道水,平安的渡过,只误伤了三个人。
十五过节,停战了一天。十六的战事就猛烈了,因为第二道水正是主流,水势甚急,河面又较宽,距离县城更近,不但九子枪可以打到,就毛瑟枪也打得到的。陆军就分为两队,一队乘船横渡,一队就在沙洲上猛烈的向城上密放,不使守城的人敢伸出头来还枪。虽然如此,也死了两个,伤了十多个。十七日,陆军进占了第二道水与第三道水之间的沙洲,朱庆澜便揣量形势,若然纯以步兵抢渡,仰攻上城,胜算倒是可以操的,不过死伤恐怕不小。于是就把炮队调来,将两尊并不甚大的磅炮安在沙洲上,一面叫人到城里去交涉,叫他们快点自行退却,把城让出来;那吗,他的陆军进城,可以秋毫无犯,并且不准巡防兵有一兵一卒进城骚扰。如仍前抗拒不退,他就要开炮了,大炮轰炸,玉石俱焚,那于他们太无好处,并且也枉害了百姓们。信使往返数次,因为周鸿勋的要求太过,投诚他也可以的,但是,第一要保升他做陆军标统,第二他的这一标人,要他自己招募。先是退让也可以,但是,第一要送他快枪一千支,五子九子不论,银洋二万元,第二要等他走后三日,官兵才能进城,告示上不能称他为逆匪。条件太苛,全不是陆军统制所能办得到的,于是,在十九日的早晨,朱庆澜便下令叫炮兵开炮。
据说是开花炮弹,一连轰隆的十几炮,到底炸坏了好多房屋?打死了好多人畜?官军这面是不知道的。但是只听见城里人声鼎沸,这里也就不再开炮了。
又过了两点钟的时节,步兵又在沙洲上放了一排枪去试探,并不见城里还枪。只见一些普通人在城墙上摇手大喊,喊的什么,不可得闻,但是意思是明白的,即是说城里没有敌人了,快不要放枪。于是,官兵便放心大胆的渡过第三道水,从从容容的整队入城,城门早已是大开着的。
辛亥年,依太阴历算来,是八月十九日,依通用的太阳历算来,是十月十日,正是武昌起义的那一天,据守二十七日的新津县城,正式被陆军十七镇放了十几炮,未伤一人一畜的克复了!
新津克复了!制台衙门在上午十点钟,业已轰动。官场中知道的人也很多,都按照规矩,纷纷坐轿上院来禀见叩贺。赵尔丰这一天之喜,喜可知也!并且在当天下午,总督部堂招抚各路乱民的告示,便已贴出。告示上说得明明白白:抗拒官兵的叛弁周鸿勋,据城作乱的匪首侯保斋,业于本日上午九点钟,被官兵奋勇攻入新津,生擒活捉,立地正法。其余胁从兵民,概弃械投诚。本部堂体念好生之德,已电饬罔治一人。新津之事可鉴,尔等盲从附和,宜速痛改前非,各自归农安分,本部堂爱尔等如子,断不究尔等之前愆也。“谕尔愚民,其各凛遵!”
但是城里人民,全都不自在起来。互相找着问道:“赵屠户的告示,说新津已经攻下,是真的吗?”互相回答的必是:“未必然罢?他龟儿子专会说假话骗人的,自从他接事以来就是这样的了。”
傅隆盛自然否认得更凶,他说:“这一定是赵屠户在说梦话,他做梦都想着要把新津攻下,要把侯保斋周鸿勋擒来杀了,那是容易的吗?新津城那们坚固,还有那条河,太平时候,空手行人尚那们样不好渡过,动辄船翻了,把人淹死。打仗时,你在渡,别人在朝着你放枪,恐防渡到河中间,船就打翻了。抬船是好久的事?咋个就说把新津攻下了?即使攻下了,官兵一定死伤得不少,咋个这两天并没有看见抬伤兵进城呢?这一定是赵屠户的谣言,故意说来捣乱民心的,半句话都不可靠。啊!或者因为岑宫保快要拢了,所以他才说些诳话来圆他的面子的。”
众人明明知道他的话才未必可靠,总督部堂皇皇告捷的公事,岂能乱说?但是比较之下,他的话毕竟入耳些,也就自诳自的大为点头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