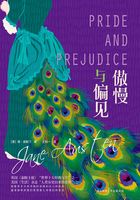楚子材既受了表婶的重托,代她照管全家。并且临别时,说得那样的真挚:“你是我顶相信的人,所以才托跟了你。不过你也不要太认真了,如其当真有人按来,你千记不要同他争执,最好是赶快逃到龙家来。我的东西都不在我心上,要是你有了啥子不幸,我是一定活不起来的!我本来不打算托你,想把你也带回娘家去的,一则怕人家多心说闲话,二则你表叔是这样主张的,我咋好不依他呢?乖儿子,你要听我的话呀!丢你一个人在这里,我实在是不放心的!”
因此,他便实行了古人所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第一天昼夜都不出大门一步。知道没有什么人来,便叫看门老头子简直把大门关了,坐在门房里听着。老张照规矩是买了菜回来,便不出灶房门的;何嫂除了洗衣服,也只坐在后面围房里做她的活路;一个院子,清静到只有虫声,只有鸟声。
他在第一天,还感觉得很有趣味,这样的清静,各个房间任凭他走来走去;偶尔把书房里的书,翻出来看看,总是经史之类,不甚有劲,倒有一部《聊斋志异》可看,却是已经看过三四遍了,只一看题目,就已熟悉写的是什么事。好在表叔的黄酒白酒是现成的,要一点小菜,躺在敞厅的花皮椅上,对着阴云密布的天色,独酌起来,倒也自由自在。
但是到第二天初七,过了大半天,就感觉到了寂寞。同时寻思:到底不晓得街上是什么光景,别人托看房子,意思只在不要使乱人进来,不要使东西失落罢了,外面的情形,总应该晓得。如其真有什么,也才好打主意呀,明天就是初八了!
他遂来到门口,两头一望,还不是同平常一样?本来做生意的就不多,少城公园早已关闭,由此而进少城的人,更是少了。他心里已是怀疑:“如此平靖无事的气象,咋个会说明天就要攻城呢?”刚要回身进去了,忽然看见彭家麒挺胸凸肚的从西头走来。
他高兴极了,老远就招着手喊道:“老彭!老彭!几时进城的?”
“噫!你在这里!可就是黄家了?好辉煌呀!”
“进去坐谈一会。现在是我一个人在此,暂时算是主人家了。”
彭家麒已跨进侧门,方问道:“黄家的人呢?那个很胆大很有趣的娃儿呢?”
“你没有听见人说,初八攻城吗?人家害怕,全躲开了。”
“哈哈!攻城?谁来攻城?”
“说是各路义军,有四五万人。上前天城门洞,已发现了一张周鸿勋的告示,有几句是:八月初八,义军进城,只拿赵周,不问平民!”
“你亲眼看见的吗?……伙!好个院子!这房子真不错呀,花木这样的好!”
楚子材一面让他坐,一面递纸烟给他道:“告示就有,我相信也是假的。不过我们没有出城,还是不晓真实景象。只到处都听人在说,周鸿勋已打到双流,田振邦已逃回成都,把城里做官的人骇得东藏西躲的。我正要问问你的消息,你是从城外来的。”
彭家麒嘘着纸烟笑道:“要问我的消息?我的消息,怕是城里人不愿意听的!”
楚子材止住他道:“你怕口渴了,我进去跟你斟杯茶来。”
“很好,我本打算到公园去喝碗茶,偏偏尝了一碗闭门羹。这院子实在好,我觉得比公园还有趣,就只小一点。”
他把茶壶茶杯全拿了出来道:“老彭,今夜不出城,就在此地歇一夜,床铺是有的,你睡我的床,我睡主人家的床。我叫厨子去弄两样菜,有现成酒吃,黄白都有,随你的便。”
彭家麒笑道:“楚子材竟阔了起来,有高房大屋,有花园,有厨子,还有留宾之榻,好罢,我就搅你一夜。只先交待明白,我不等到打二更就要睡的,明天绝早起来就走,这是我过惯了的,不能再陪你半夜半夜的谈。”
“你放心,绝不苦你的。头回是在你家里,又是悬心吊胆的时候,自然要吵你了。你是昨天进的城吗?学堂里去过不曾?”
“今天吃了早饭才进城的,是家父叫我到正大裕、马裕隆几处去打听一下二哥的消息。自从邮政不通以来,就没有接过重庆的信了。顺便也到学堂去走了一遭。人真少呀!我们那班,现在才八九个人。最痛快的,是土端公简直变成龟儿了!我今天去时,正碰见别班几个富顺、隆昌、泸州一带的学生,因为要回家去,叫他把火食费退出来,好拿去做盘川。他东枝西梧的不肯退,着他们几个大骂一顿,几乎连他的祖宗都跟他叨尽了,他还是笑嘻嘻的。是我来,我真受不得,不说是学生,就是我们长辈,我也要赏他几捶的!”
“这些且不忙说,且说你那城里人不愿意听的消息。”
“这有啥说头?一切都是谣言!新津的情势并不好,我知道得很清楚,只是官兵不肯进攻罢了,要是一进攻,那天就打平息了!”
楚子材笑道:“城里人诚然把新津夸张得太过,把一个侯保斋说得比关公,比张三爷还凶。其实,他是我远房的外公,我是常常同他见面的,那有不晓得他的?人倒义气,但是岁数也大了,又吃了一口鸦片烟,做什么也没有精神。这回不晓得咋个会钻了出来,我想一定是很强勉的。就说王文炳会打条,也不过比我们高明一点儿罢了,未见得就当真赛过了诸葛亮。自然,都说得太过火了,可是照你说来,又几乎是半文不值,你的折扣也未免太打凶了些。”
“哼!你说我打折扣,我是有真凭实证的。”
老张已用掌盘把酒菜杯筷端了出来,摆在桌上道:“表少爷,街上实在买不出啥子来,只炒了一盘新核桃肉丁,一盘红辣子肉丝,在皇城坝配了一盘烧鹅,一盘白斩鸡;吃饭只是一样黄花攒汤,格外还要啥子?”
彭家麒道:“两个人,四菜一汤,还不够吗?够了,够了!”
把大曲酒斟上,两个人遂开怀畅饮起来。
彭家麒颇颇有点感慨道:“像你令亲一家人,真算享福了!房屋庭园造得这样好,使的底下人又得用,如此的起居穿吃,也才不枉了!像我们乡下,真是枉自有钱,一点福都不会享。我将来有本事时,一定要在城里过这样他妈的几天。”
楚子材笑道:“我也是。在这里住惯了,一回去,总不方便。不过据我审察起来,要住这样的家,也得要像舍亲一样,自己先要懂得,还要讨一个大家人户的姑娘来做老婆才行,不然,叫你我家里的人来,还是弄不好的。”
两个人谈了一会,仍旧谈到新津的事。
彭家麒笑道:“我们场上团丁,那天跟着会长跑的有三十多人。起初跑到温江,后来听说新津起了事,势力很大,便又跑到新津。中间有个姓邹的,邹老幺,是我家一个佃户的儿子。在上月底,因为想家,开到旧县来接仗时,便乘间开小差,绕了一个大圈回来。这个月的初三,我在田坝里碰见他,仔仔细细的一问,才晓得了新津的真情实事。”
据他转述起邹老幺的话,原来新津城里,只算周鸿勋手下的三百多名兵是顶行的,一色九子快枪,打也真打得准。七月二十五,陆军攻到河边,得亏保子山上一哨人,放了两排枪,把陆军兵士打倒了两个,登时就退了。以后来进攻的兵,都只在旧县放些枪,从没有敢临到河边来了。至于同志军,的确有二千多人,还不是同各地团防一样,使刀叉的顶多,大部份是抬炮。单响毛瑟有三百支的光景,前膛枪有四五百支,其余各种杂枪有百多支,周鸿勋在旧县新兵营里抢了四十来支五子快枪,他认为不好,送给一个同志军的首领,这就是七月二十八,同志军渡河到花桥子前五里,把巡防兵前哨,打死三个人,打伤八个人的利器。但是子弹不很多,大家都爱惜得什么似的,不轻容易打一枪。九子枪的子弹也不多,每一个兵顶多八十来颗,有少到三十几颗的。毛瑟枪的子弹也缺,前膛枪火烟倒足,发火的铜帽壳也没有许多。大体看起来,军火太争差了。周鸿勋同几个同志军的统领都拿着钱派人四路收买洋枪同子弹,不知道结果如何。兵士的意见倒很豪的,因为打了两次小胜仗,把陆军和巡防兵都打退了,所以大家都相信官兵怕死,不敢再来了。城里也还安定,人民照常的做着生意。不过邹老幺绕道回来时,才看见沿途的官兵真不少。打听一下,双流城里简直驻不下了,黄水河也驻有千把人。而且官兵都是快枪,子弹也富足,一箱一箱的只见抬。又听说还有开花大炮,放在双流,尚未运上前去,如再攻打不下,就要用开花大炮了。邹老幺吐着舌头道:“我幸而开了小差回来,在新津时,还不觉得好险,如今一回想,官兵多到十来倍,快枪大炮,那么厉害,就如二十九那天,陆军打了一个多时候,子弹在房子上面飞得就像大白雨的雨点,只要碰一下,便没事的。恰巧三十那天,跟着一个姓何的统领渡河,偏偏没遇着一个兵,如其不然,一定打死无疑。”
所以彭家麒的结论,才是“只是官兵不进攻罢了,要是一进攻,那天就打平息了!”
楚子材道:“那吗,明天攻城的话,简直是谣言了。”
“何消说呢?新津的真象且是这样的,其他各路义军,更可想而知。”
楚子材复蹙起眉头道:“新津情形真如你所说,那不太险了?我家里人,不晓得是咋个的呢?”
“你家里还有些啥子人?”
“娘老子都在,还有一个半成人的妹妹。”
“那你焦啥子?你们是本城人,纵然兵打进城了,也可躲的呀!并且如今的时势,到底文明多了,像古代那样动辄屠城的事,是不会有的。就像七月十五那天的事,在从前说起来,堂堂的一省总督,打死几十个百姓,算得啥子?如今不同了,大家硬要说他的不然,他也不能不多方掩饰,生恐人家议论他妄杀。我再说一件事你听,这是前几天的事罢?双流城里,有七八个巡防兵,因为估吃霸赊,恰恰碰见田振邦出来,人民拦着轿子一喊冤,他竟自拉了两个兵去枪毙;并立刻发出很多张告示,连我们场上都有,申明军令,说是凡骚乱人民者斩!田振邦尚晓得要买民心,所以我敢说新津就攻下了,兵也不会乱来的。”
这话很有理由,才使楚子材重新放下了心。他又同彭家麒研究起来,官兵既比义军强那么多,为啥不一鼓作气,把新津打下呢?他们研究不出理由,只好归之于陆军深明大义,不愿徇赵尔丰的私意来屠杀同胞。
两个人醉饱之后,点上灯来,吸着纸烟,喝着热茶,又论起四川事情,不晓得如何的下台?
彭家麒道:“怕要等岑春煊来了,才会有转机罢?”
自然,这不是彭家麒一个人的话,真可以说是那时一般人的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