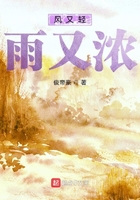人众都起来了,雨还没有止。
成都的暑日,本是容易落大白雨的。大白雨有三阵,必在几天燠热之后,一阵黑云涌起,其黑如8,很像黄昏,而后雷声轰轰,风声虎虎,豆大的雨点很有力的打在瓦上,雨势越来越强,强到对面不能谈话,瓦上庭前,溅起的雨丝霏如濛雾,直像一片广大的瀑布,从天上挂下。但这样的雨,必不会终朝的,三四小时之后,积水成潦,而云破天青,依然赤日耀空,余下的凉意,至少又可保存数日之久。
但阻止楚子材起程的雨,却不是那不终朝的大白雨,既无急雷,又无暴风,其势又非倾盆,只像秋霖一样,不住的下,而云色永是一片灰布似的,不知有好宽,也不知有好厚。虽然暑气全消,而气象令人不爽快。
黄澜生望了望天空,才向楚子材说道:“你的运气真不好,才说要走了,天就这样变起来。”
“不是吗?”他做得很焦急的样子,紧皱着眉头。
“路是滥透了,今天如何能走!若是过午不住点,明天就不再下,路上是硬头滑,轿夫也未必肯走。”
“不是吗?”他嘘了一口纸烟,依旧皱着眉头。
“也好,下雨天留客。”
忽然从背后传来一种很熟的声音:“天留我不留。”
黄澜生哈哈一笑道:“才是老吴!你真是急装缚袴了!”
吴凤梧把淋淋漓漓的雨伞收了,顺靠在阶沿上的砖壁脚下。又把麻耳草鞋脱了,将一双污泥糊满的大脚,伸在檐溜边,一面借檐溜淋洗,一面笑着向楚子材道:“你才鸩我的冤枉哩!早晓得你逢雨不走,我真不该打早就跑到武侯祠去了!”
黄澜生道:“你的脚不能那们洗法,恐怕受寒,我叫人提热水出来。”
“老哥子不要把我看得太娇嫩了,我们还能洗冷水澡哩!”随把声气放低了笑道:“又不像老哥们伉俪情深,夜无虚夕,我们是把独宿丸服惯了的。”又是一个哈哈。
黄澜生翘着短须笑道:“莫胡说!我们赌喝一碗冷水看!”
振邦兄妹一路跳着笑着奔了出来道:“吴伯伯来了!”回头看见楚子材,“你还没有走吗?妈妈诳我们,说你打早就走了。”
吴凤梧接过罗升递与的洗脚帕,将脚擦干,穿上黄澜生的旧鞋,一面接过楚子材的纸烟嘘着道:“你们楚表哥上路,大概有三不走:逢雨不走,逢热不走,日子不好不走!”
楚子材道:“吴先生你太挖苦人了!这们大的雨,路上多滥!咋个走呢?若是走得,轿夫还不来催走吗?”
“轿夫竟没有来吗?”
楚子材摇了摇头。
“今天不走,明天又要多耽搁一天了。”
黄澜生道:“我不是这样说过?若是今天的雨不早点住点,明天路上定是硬头滑,自然走不得了。”
“倒不为的是硬头滑。听说赵大人定于明天到省,不消说,从城门洞到双流,这四十里路全是人夫轿马的了。大路只那们宽,八人轿四人轿那们多,不消说,还要加上总督部堂的全堂执事,将军都统司道们的执事,亲兵,卫队,统制标统率领的新兵等等,你算算有多少人!我们坐小轿子和步行的行人,让得完吗?与其慢慢的让着走到双流投宿,倒不如多耽搁一天,到后天打早走,一天就到新津了。”
楚子材不禁笑了起来道:“我倒不忙,横竖大姐出嫁还有六七天的日子,我只要赶得上过礼,就没事的,缓天把走倒不妨。”
黄澜生道:“子材毕竟是长了一岁,今年就不像往年:一到放假,就慌着回去,连半天都不肯多耽搁。”
黄振邦仰面看着楚子材道:“你不走了吗?”不等得到肯定的回答,便领着他妹妹一路跳着奔了进去,还一路叫道:“妈妈,楚表哥不走了!”
吴凤梧已咂燃了第二支纸烟,躺坐在花皮椅上,瞅着楚子材道:“看你的意思,你回去只为的是你令姐出阁,那吗,你装了舅子后,不仍旧要上省吗?”
楚子材正出神的看着淋在雨丝中的那张与他颇有关系的凉床在,——那是一张红豆木框,广藤密心,宽约二尺四五,可坐可卧的老式凉床。据说,还是黄澜生的老太爷入川时,亲自带来的一种故乡家具,所以式样很苏气,高矮也甚为合度。——随口答道:“自然喽!”
雨已不如适才大了,风却一阵一阵的吹起,树枝树叶上的积雨也一阵一阵的淅淅沥沥的洒下。灰布似的云幕,似乎薄了一些,阳光显得更明了点。
看门老头子进来说道:“表少爷,轿夫来问,今天到底走不走?早晨你说雨太大不走,现在雨小了。”
楚子材红着脸道:“今天还走啥子,路那们滥,一百里的路程,走得拢吗?”
“他们说,若是不走,每人要二百钱的店饭钱。”
吴凤梧道:“依我说,今天还是走得拢的,何犯着耽搁一天,就是两天哩!”
“你是打空手走路,自然可以,别个抬着一百多斤,多老火哟!”
黄澜生道:“快八点钟了罢?滥泥路,走起也吃力,多耽搁一天,算啥子。子材,你就出去把店饭钱跟他们开消了,并跟他们招呼,明天也不走。罗升,进去看饭菜好了,就摆出来。我吃了,还要过张大人公馆里去哩!”
一直到早饭之后,黄澜生坐轿走了,振邦上学去了,吴凤梧说是去找王文炳,约定明天再会,也拿着雨伞,仍旧穿上麻耳草鞋走了,——雨已全住,灰云也散得越薄,庭中积水全由阴沟消了,花草枝叶格外精神,柳枝上的蝉子也照常的鸣了起来,成都西南城最多的乌鸦也咶咶的叫着在高枝上晾翅膀。——楚子材方走到堂屋外面,听见表婶的依然清脆悦耳的声音正在上房后间吩咐何嫂洗什么东西,吩咐荷花做什么事情,声口还是那样的简洁老当,威武有力,一点不曾失去太太的身份。
他寻思:“如其是年轻女人,经了昨夜的事变,不知还能这样庄重不?如其是女郎们,恐怕今天更是昏昏沉沉的了。”他又想起了“我确是经历过来的”这句话,便惘然起来:“她的经历,不知在出嫁前,或是出嫁后,果然是个老角色。我能够问她么?她该不疑心我在追究她?该不疑心我要吃醋罢?”因为他只管迷恋她,仍旧是害怕她的。
她的步履声一直走到前间,打开了衣柜,像是在换衣裳似的。
他撩起门帘,轻轻跨了进去。
她果然背向外站着,下面一条雪青旧官纱裤子,蓝白绿绦的裤带,照常一个油光水滑的鲍鱼纂,插了一朵半开的栀子花,从颈项到裤腰的肌肉全裸露在外面,手上提着一件白洋纱马甲,正在清理纽扣。
他两眼都花了,觉得那一段白背,简直像敷了一层粉,然而又有一层浮动的光彩。肌肉很丰腴,翅膀骨只隐隐有一点,两个肩头几乎是浑圆的。他赶紧走去,一把将这一段温和而富于弹性的艳肉搂贴在胸前,两只手恰就抄在前面,抚着那对绵软而肥满的乳房,同时那热烈如渴的嘴唇便紧贴在那圆而不很长,并且毛业经绞光的脖子上。
她并不如他所想象那样吃惊,只轻轻的嘘了一声。
他颠倒了,两臂更其用力的紧紧箍着,手指和嘴唇也像发了疯,心房的跳动使她从背肉上感觉到。
她一面摇动上身,用力的要摆脱他的搂抱,一面蹙着眉掉头向他微笑道:“哎呀!快放手啦……婉姑儿就要进来了……庄重点!我问你的话!”
虽然是笑着在说,但那黑白分明的眼珠里的威光,以及毫不可通融的口吻,却自然而然使他吐着哮喘,努力压抑下要发狂的念头,睁着火球似的眼睛,把手放开,瞪瞪的看着她毫无其事的把马甲穿上,纽子扣好,将一对极其动人的乳房压得平平的,变成一片过于肥厚的胸脯;然后又将一件旧料子改成时兴的高领浅边的酱灰花绸衫,罩在马甲上,对着紫檀架的玻砖座镜,慢慢的扣着。
“你为啥子今天不走?”依然对着镜子,但从镜中却看得见他那红光笼罩,——骚疙瘩更其像红豆一样,一粒一粒的鼓了起来,觉得别有一种意味。——同时又是憨痴痴的面孔,她复忍不住的一笑道:“怎吗,憨了?我在问你的话呀!”
他咽了一口口痰道:“下大雨啦,你难道不晓得?”
她车过身来,正正的对着他道:“你看你这个人,这样的不听话!我昨夜不是说过,今天就是下刀,你也得走!你年年都是一放假就走了,为啥子今年这样舍不得走?大家细想起来,岂有不诧异的?一定会默到你必然有啥子舍不得的人在省城。你住在我家里,又不曾在外面胡闹,那吗,你一定是舍不得我了。我昨夜不是说过,我是经历过来的,……”
他眉头一扬道:“着!我正待问你,你是经历过偷情的事吗?你说了好几次。”
她笑着把他的脸一拧道:“你还有这点聪明啊,真果是草帽子底下相女婿,看不出人材啦!只要你肯听我的话,我自然会告诉你的。你到底为啥子不走?”
“唉!何必说哩!硬是舍不得你。”
“舍不得,就不走?也好那吗,就永远不要走!”她的脸立刻就放了下来,并车身到床前,将换下的衣裳,一件一件的折叠起来。
楚子材看见她生气的样子,觉得别有一番风韵,心里更其爱得发痒,不禁伸手去握她的膀膊。她却使劲的一肘撑来,恰撞在他的大腹上,并咬着牙齿说道:“你要咋个!叫你放尊重点……你把我当成啥子人了……告诉你,你虽偷上了我,还是不能由你的脾气的,凡事都得由我……我要咋个,就得咋个!连我的表哥、姐夫、男人都是这样的在将就我,随和我……你一个四浑小伙子,仗恃啥子,敢来强勉我?……你再不规矩,动辄动手动脚的,看我把你搌得出大门不……”
这一瓢冷水,把他的什么兴头全浇熄了。垂头丧气了一会才道:“你不要生气,我立刻去喊轿夫来就走,今天总可以走到黄水河的。”
她本要向后间走了的,这才转出笑脸来道:“此刻走,又不必了!只要你知错,不故意同我顶撞,我自然会多爱你一些的。你舍不得离开我,我难道不晓得?不过,也不要太热很了。俗话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热如火。只管热得像火,但是一眨眼就化成了灰,连一点热气都没有了。我愿意的,就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虽然淡,却是长远。乖儿子,你是才同女人打交道,这些话,你还不懂。我晓得你的心眼,也同我的那几个一样,碰头香,一上了手,就恨不得不分昼夜,时时刻刻把我搂在怀中,一动情就来。这不说于你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并且也像点心铺的徒弟。你晓得淡香斋待徒弟的方法不?徒弟才招来,一看见点心,那有不馋嘴的?见啥子,吃啥子,总像啥子都吃不够。因此师傅在做热点心时,便特意把徒弟喊去,让他先吃一个饱。吃不得了,还在劝他。一次两次之后,见着点心就要发呕。男女偷情也是这样,若果一开口就吃个饱,不久就会生厌的。如其偶尔一次,比如肚子十分饿了,吃一盘精致点心,你想,这比撑开肚皮吃热点心的,那个味道长些?……所以我昨夜才叫你走。我的意思,就是要把这味道留在你的心中,让你回家去慢慢咀嚼。你自然越咀嚼越流口水,你也才会慌着要来,不至于像往年一样,定要等到开学了才来。乖儿子,你现在该懂得我的心了不,怨恨我了么?”
楚子材只管恍然,但他心里仍很愿意当个淡香斋的新徒弟,自以为绝不会吃得发恶心的,他也有他的理由。
婉姑恰奔了进来,要找什么东西。她妈妈唤着她道:“不准跑!我问你一句话,早晨,你爹爹咋个会说起楚表哥今年舍不得走?”
她张着大眼,同她妈妈一样的黑白分明而有神的眼珠左右转着,半会,才说道:“爹爹没有说。”
“放屁!爹爹说了来,你哥哥告诉我的。”
楚子材笑道:“表叔是说过。说我长了一岁,就不同了,往年一放假,就慌着走,半天都等不得。”
婉姑接口道:“是的,是的!爹爹是这样说过,说楚表哥往年硬慌得很,半天都不肯耽搁,一放假就跑了。”
“……并没说我今年为啥子舍不得走。”
“意思不还是一样吗?精灵人说话,那里肯说尽的。”
婉姑已在连三抽屉内找着了她要找的东西了,便又登登登的向后面跑去了。
“……你默到澜生老实忠厚吗?他才是精灵鬼哩!年轻时候,又是当过花花公爷来的,就如今说起韩二李老幺那些烂婊子屁股虫,还在恋恋不舍哩。你昨夜对我的举动,他岂有不晓得?……”
楚子材骇然道:“一定是你出来时,表叔还没有睡着。看是看不见,或者听见了。他说过啥子吗?”
她喘的笑道:“就骇着了吗?”
回身坐在柜桌前的那张藤心靠椅上,把身边的美人床一指道:“你站得啦!今天腿杆还那样有劲吗?……唉!年轻人真不同!三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差不多都累不得了!”
楚子材很不安的坐下道:“好妈妈,不要说闲话了。”
“昨夜澜生不是品评过吴凤梧?……这也是个怪东西,专门好男风。他的老婆,你没有看见过吗?虽是小家人户的人,倒好个样子。二十几岁,嫁跟他有五六年,听说同睡的时候很少。我想小家人户的妇女,说不上啥子见识,说不定已偷过人的了。唉!妇女家真值不得,偷了人就要着人耻笑,说是失了节。胆小的只好忍耐到害干病死,发狂。我就胆大了,可是也只好偷偷摸摸的,敢同男人家一样:只要有钱,三妻四妾,通房丫头,不说了,还能在外面随便嫖,嫖女的,嫖男的?大家还凑合他们风流。会做诗的,还要古古怪怪做些诗来跟人家看,叫做啥子情诗艳体。我不信男女既都是一样的人,为啥女子的就该守节?人人都不明白这道理。一般妇女更可恨,她们一说到那个女人失了节,偷了人,便都摆出一派鄙薄的样子来,好像自己才正经,别的人就不尊贵了。其实,我看得透,鄙薄别人的只由于嫉妒。嫉妒别人有本事偷人。正经女人多半是没胆子没本事的。这好比一些穷人看见人家顿顿吃好的,整鸡整鸭,肥浓大肉,他何尝不想也这样吃吃?因为没这力量,也没这福气,只好向人说他是善人,不肯伤生。我这个人,历来就古怪,在娘家时,大家说,表妹是不应该见表哥的,小姨子是不应该见姐夫的。我偏不听,我硬要见,并且还要一堆耍,一堆吃,有说有笑,别人只管疑心我,却也不敢说我。我说过:要偷人,你们也挡不住我,就不偷表哥姐夫这些上等人,三小子、裁缝、大班、厨子、不是太太、姨太太、小姐、姑娘们偷过的吗?有啥稀奇?就不说一百家里头,有九十家的底子翻不得,即是那些守贞守节,守到害干病发狂的一些贞节妇女,又有几个人的心子经得在孽镜台照得呢?比如前几年走马街的那件事,说起来真笑人……”
楚子材大抵都不甚了解她的话,只觉得她胆大、武辣、厉害,而急于要晓得的,还是她那领题的一句话。
“我的乖妈妈,乖表婶,你的话越说越远了,你安心把人急死吗?”他竟溜下美人床,扑的跪在她的跟前,两手抚着她的一双丰若有余的膝头,仰起他那焦眉愁眼的脸来。
她把他的发辫摸了摸,得意的笑道:“这么大一块人,有本事偷女人,又这样的胆怯,我倒没见过,真是澜生说吴凤梧的话,有饭胆没酒胆了……好罢,你起来,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既存了心偷人,我就不怕啥子的。以前,我没有出阁时,胆子更大,也还要放荡些。如今哩,有儿有女了,倒不能不有点顾忌。不是为的我,只为的他们,也一半为的澜生,不要使他受人家的议论,说他得报应。所以一起头,我便叫你放庄重些,举动言谈处处要留心,顶好是在人面前不要睬我,故意做冷淡点才对啦。偏偏你不听话,昨夜刚亲了嘴,过了脉,你看你就掌不住了。在桌子上红起一张屁股脸,两只眼睛亮得好像要吃人似的,并且死盯着我,转也不转。你表叔同你说话,你也好像没有听见。说你神不守舍,有了别的啥子事情在心上哩,偏我随便哼一句,你又听见了。比如我才说:荷花咋个不打一张洗脸帕来揩揩脸?你就慌了,赶快就跑到后头去了。你以前,——不说以前,就前一刻钟,你是这样吗?并且才打过三更,不过一点多钟,你就催着要睡了,往夜是这样吗?这不是明明向着你表叔说了出来:我快要偷你的老婆了!倒是今早起来,冒雨走了,也说得去,却又舍不得走。你这样不听话,我真灰心,想着我以前的几个。”
敞厅上有人在大喊:“楚子材!楚子材”
两个人一齐站起来,从玻璃窗心中,看清楚了是王文炳与吴凤梧。吴凤梧还是那样急装缚袴的。
“他两个说不定又来催你走,你不准答应!若是约你出去,今夜早点回来,我还有多少话要同你细说。你表叔今天有两处应酬,一定又是喝得人事不省才回来的。”
他点了点头。稍为表示了一下,她虽是呸了一声,仍然仰起脸来,把那鲜红的嘴唇,撮成了一点,凑将过来。并把他肩膊结实的捏了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