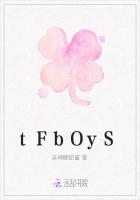大雾迷蒙,县城还在睡梦之中。
方达芬低头快步向城外火车站走去。昨晚一夜无眠。直到几分钟前,宿舍门被她砰的一声猝然锁上,冲下楼梯的时候,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满怀的悲怆、甚至是有几分壮烈——她让自己久久地沉浸在这种心境中,体会着一走了之、去而不返、“易水潇潇”的况味。这样,不觉间来到了车站。
“达芬同志。”一位中年人招呼她。
她抬眼望去,是县政府一个科长什么的,工作中有过接触,但并不熟悉的。当地人热情,爱打招呼,她并不喜欢这种朴素的、但却傻里傻气的热情。可是,又不得不回答:“唔,秦科长出差么?”她觉得这种应酬很虚假,仿佛不是自己的声音。
但人家并未发现她的勉强与矜持,仍然笑容可掬地、似乎决心把谈话继续下去:“两趟车都快来了。达芬同志你是上行还是下行呢?”
她愣了一下。她本想回答人家“上行车”,却又不愿多说,便含糊:“我去买票。”
候车室门口又有人招呼:“方老师回家么?我也去省上开会,正好同路了……”
这是个女的,面熟,却不知道人家是谁,也许是百货公司的,她想。但并不打算动脑筋去辨认清楚。县城真小。方达芬早就发现,仿佛人人都认得她,仿佛人人都对她友好。这种感觉有时使她高兴,有时却叫她懊恼。
售票窗口前冷冷清清。不知为什么,此刻她倒希望那儿不要这么冷清,她希望排着长长的队伍。她站在离售票窗远远的地方,有几分犹豫。而此刻广播响了:“请上行旅客注意,上行335次快车晚点一小时左右到达本站……”小小候车室里立刻嗡嗡吵起来。手里捏着车票整装待发的乡下人七嘴八舌埋怨。他们已差不多等了一夜。为了不至于错过这一趟去省城的快车,他们没敢去住旅馆。
方达芬不埋怨,她甚至是如释重负似的在近旁的木椅上坐下来。她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点庆幸——庆幸什么呢?庆幸上行车晚点么?她本来是为坐这趟车来的呀!
旅客们焦躁地重新坐下,等待着。而有几个急需出发的鲜货贩子还在横眉怒目地咒骂着晚点的火车。角落里那一对青年男女偎得紧紧的,在喁喁私语,全然不理睬旁人的目光。方达芬木然地望着人们。这时,传来火车鸣笛的声音,下行车到站了。她慢慢站起来,犹豫着,向售票窗口走去。
方达芬相貌平平,借话本小说的词儿一用,是“光阴荏苒,岁月无情,早已去了花枝招展年纪”。若是在大城市,无论她走在大街上或机关大楼的走廊上或挤在公共汽车里,是不会引人注目的。然而在这一趟从省城开出来的挤满了“乡下人”的短途慢车的车厢里,她却是并不一般。她穿得不土气,但也无妖气,清爽而大方。一身其实并不怎么花钱的衣服,只因为身材、气度而显得与众不同,使她周围几个村姑大嫂自愧弗如。她们自从腰里有了钱——虽然钱并不多,而且来得也不易——对于城里女人的穿戴已不那么看在眼里了。但眼前这个单身女子的漠然的神情,在她们看来是一种城里人的傲气。在她面前,她们不免自卑。这一群去大城市玩了几天回来而异常兴奋的女人,渐渐停止了唧唧喳喳的谈笑,悄然而坐,时不时地把眼光扫向车窗口那个寂寞的女人。
她当然感觉到了这种目光。她在县城工作,遇到过太多这样的注视。这种女人的悄然的注视,表示一种敬畏之情和难以消融的隔膜,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她认为这是十分可悲的。然而,更可悲的是,在省城里,她也曾用这种目光去注视过那些地位优越、浑身闪耀着青春光彩的姑娘以及那些雍容华贵、脸呈幸福微笑的少妇们。
她深知自己也一样可悲而更加痛苦。她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感到一阵透彻心脾的冰凉。车窗外雾霭正在消散,山影田畴在朦胧中显现出来,幽远而寂寞。
她在县上的工作环境,说来是相当可以的。因为一张大学文凭,她渐渐地受到重用,当然也因为她的勤奋。局里的干部们,老老小小的,有几位年轻点的女同胞,又都拖儿带崽;下乡的任务以及写材料的差事就总少不了她方达芬。三年过去,派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局办”副主任。由此工作更忙,麻烦自然更多些。小城的气氛免不了的那种闲言碎语,加上一些具体事件上与局领导意见不合,搅得不得清静。这还不算啥,问题在另一方面:三十年纪已过,她既无称心如意的男友作为婚姻考虑的对象,又还没有最后下定是否抱独身主义的决心。——须知,在这小城里,下这样或那样的决心都不无困难。她曾悄悄托省城的亲戚帮忙联系过调动的事,调回省城去,这是好些个分配到县里工作的大学生实践过也成功过的办法。但对于她,此路就不通。人家说:除非你的丈夫在省城工作。为了调动而去接受一个“丈夫”,她感到屈辱,不愿意。她很自尊。
而自尊给她带来的并不是幸福。
石头都不经磨,何况人呢?她终于答应了表姐的“条件”:今天去省城表姐家“相亲”,男的是个落实政策重新做了讲师的五十二岁的鳏夫,据说与这种条件的男人结婚,调动的事最好办。她一想到这个便要呕吐。但还是决定去试一试。今天一早出门时那种苍凉和悲壮,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她却踏上这一趟方向相反的列车。
此刻,她心里有点空空的,但到底摆脱了几天来笼罩在心上的“相亲”的恐怖。她感到平静。她渐渐明白起来,她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可以给她安宁的去处。在那里,她备受尊重。那里是一个温馨的角落。每一个人都有那样一个小角落……流浪汉一无所有,但那样一个暂避风雨的小角落还是可以找到的……平静中,她又不无忧伤地想起那些无家可归、四处飘零的弱女子。她当然不是那样的弱女子,谁不知道她是全靠自己的苦学而挣得一张响当当的文凭、工资一百零二元、有独立生活能力、受到社会和领导重视的知识分子干部?她制订工作计划,和领导同志一起研究经济政策,她下去检查别人的工作,她在县委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受到表彰,并被指定重点发言。她拥有许多女人所没有的宝贵的东西。
然而……她又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没有如锦的年华,没有时髦的服装,没有花容月貌,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去争取爱情的勇气,甚至也没有那样的机会。幸福都属于那些漂亮的姑娘么?要不,为什么连那些爱情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全都如花似玉?
太阳升起来了,铁路近旁的景象现出了本来的面目,山丘像血染似的深红,没有树,甚至也没有草。只有绿色的竹林点缀着农家小院分布在山脚、溪边。秋收过后的田野,空旷寂寞。干裂的土地显得异常丑陋。火车进入本县最贫瘠的地段了,方达芬的心情又变得荒凉起来。
小站停车两分钟。她步出窄窄的站台,向前面山洼望了一眼。山的夹缝中藏着一座小乡场。那儿除了一个乡政府和几家商店外,有一所小学。小学校舍是破庙改造而成,就在场口那棵老榕树旁边。老榕树还像当年那般枝叶蔽天。她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有往那儿去。
她走上另一条小路。这条小路蜿蜒如线连接着座座红褐色的山冈,通向遥远。这坚硬的石头小路,她太熟悉了,这些年来,有时想着它就伤心,那是因为想起那些无尽的等待、盼望和失望的岁月;有时想着它又觉温馨可爱,那是因为后来新的生活中伴随着人生价值的实现而相生出来的辛苦、疲累和烦恼。她读遍了所有能够读到的“知青小说”,却很难得为那些青年英雄悲壮的牺牲精神所震动,也极少为那些被凌辱的生命洒下同情的眼泪。她觉得那些女主人公们的禀赋、天资和容貌都是超群出众的,而她自己却太平凡了。寻常之辈,既无大的欢乐,也无大的悲痛;没有惊世骇俗的壮举,也没有感天动地的爱情,作家的笔是不屑于注意的。她觉得自己正是这样。这样的知青何止千万,文学把他们“省略”了,不也是小有遗憾的么?
山下传来“呜——”一声鸣叫,她回头望去,一列上行快车没在小站停留,它呼啸而过,向远方省城驰去。她不由呆了一下,顿觉有些倦意,腿脚发软。她所面临的“现实”像一道枯燥无味、并不难解却又迟迟解不开的数学难题,横在她的眼前……好累呵,她下意识中这样呻吟着。她觉得自己应该坐下来休息。
坚硬的小路缠绕着起伏的红褐色山冈,不知哪里是头哪里是尾,绵绵无尽。
秋阳已快升上中天。微风飘来淡淡的熟悉的气息,令人想到树林中的潮湿,小院里的鸡舍、房顶袅袅的炊烟。
她没有坐下来,她心里明明知道今天为着什么到这里来,却又不愿对自己挑明。看望当年下乡时曾给过她许多帮助的房东大娘,这是最好也是最普通的理由。自从毕业分配到县里,并非没有来过……然而今天,今天却另有缘由……想到这个,悲怆又塞满心头。她咬了咬嘴唇。
现在,她站在篱墙外。爬满竹篱的牵牛花已经结籽。阳光安闲地照着整洁的小院坝,屋檐还是那般低矮,土墙却是新粉刷过,显得耀眼的白。矮凳、蒲团、晒衣竿……占据着它们永恒的位置。狗吠声有点陌生。灶房门边立即出现一位白发老大娘。方达芬露出笑脸,跨进院门。
“哎哟!是达芬……”老人惊喜。
达芬便上前抓住老人的手,叫着大娘。
“快坐呀,坐呀,看你热的!我给你舀水来洗洗……”
“大娘,我自己来吧……”
“哪能要你自己来,坐下,坐下。这儿,这张小板凳还在这儿,你最爱坐的老地方。”
方达芬洗脸。解开领下的纽扣。大娘望着她。大娘用衣袖揩眼睛,老人家太高兴了,达芬在她家住过三年多,朝朝暮暮的。七年前达芬离开,她病了一场,孤单的日子使她老得快。她有儿子,儿子在乡上工作,早晚回家,老人独自打发着漫长的白天,从太阳升起到日落西山。
“达芬,这三年里,你回来过三回,我全记得清楚。一回是正月初五,一回是五月初一,这回是……去年那回,你刚走就落雨了,雨下得瓢泼大!你没有淋着吧?”
“没有淋着,我正好到了火车站呢!”
“我几夜没睡着……五月十二,豆子上县里开会,我让他去看你。”
“是的,我见到豆子哥了。”
“豆子回来说,你好好儿的。还说,你当副主任了。我就想呵,达芬当官儿了,怕是公事忙,再也没时间下乡来看看我们了。九月间,我说,豆子,你给达芬送些新米去,城里人都爱吃新米。豆子说,人家在食堂吃饭,没锅没灶的。腊月尾上,我说,豆子,过年过节的公家也该放假的,达芬没锅没灶的,你去接她来住几天吧。豆子说,人家不回省城过年么,跑到乡下来干啥……”
“其实,春节假期我也没有回去。”达芬的脸红红的。她愿意听老人这样唠叨,听着心里温暖。至于豆子(她从前叫他豆子哥,当年她下乡时,豆子已经高中毕业),为什么不愿意常去看她,她想那是另有重要的原因。她和许多女子一样对某些事特别的敏感。过去,为了不使豆子失望,她曾有意冷淡他,和他疏远,虽然朝夕相处,那时她便清醒地意识到她和豆子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她为了自己的前程,她在那孤独无望的年月里,拒绝自身对于爱情的需要,而不曾像那些与她一般身世一样平凡而意志却很薄弱的“知妹”那样嫁了个农村丈夫……理智果然帮助了她。的确,她那时是胜利了。然而现在想想,那个胜利又有多少值得骄傲的呢?
“……豆子的孝心好,这没说的,可就是成天不落屋,看不见他影子。前月里,乡上的公事也不当了,去考啥子电大,十天有九天不落屋,住在县城里……”
“上电大是好事情呵,大娘你应该鼓励他。”
“我晓得是大家看重他,我不会拉后腿的。他在城里,常去看你了么?”
老人两眼盯着她。
“没有。”达芬笑笑,心里却有点酸楚,“读电大是半脱产,他在组织部帮助工作,很忙的。我知道他就住在组织部楼上……”
“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也不去看看你,帮你做点事!”
“没关系,我也没啥事要帮忙的。只要他学习成绩好,两年毕业,换个工作岗位。”
“不稀罕那个!当个官儿又咋样了?就兴不讲情义了么?当初你也帮助他学习呢。要不是他看你那样有学问,你在前面领着路,这些年他断然不会这样用功学习上进,一个劲儿地啃书本,三十都过了……”
达芬心里怦怦跳,说:“他不只是啃书本呵,这几年乡上的工作也很有成绩嘛!要不,上级会看中他?听说组织部要正式调他去。”
“调他进县城做事?”
“是呀。”
“那,我更看不见他影儿了……”
“到那一天,把你老人家搬到城里去,不就天天都看得见他的影子了!”
老人想了想,意义不明地说:“那么……”
“你舍不得乡下这房子么?”
“……也好。那样,也能够天天都看到你?”
“当然!”达芬断然回答,她又死劲地咬着嘴唇。仿佛近年来,特别是这些日子来交织在内心的烦恼和犹豫至此结束。仿佛决心已下,“豁”出去了……喉头有点发哽,颇有点悲壮似的。
“哎,只好这样了。”一个声音在她脑际明白无误地这样告诉她,而她知道这是她自己的声音。虽然如此,她还是相当激动,也许从此生命将有了新的意义,也许事实上比想象的要美好得多……她不由抓住老人的手,喊了声:
“大娘!”
接着便把脸伏在老人怀里。
老人全然不知达芬刚才的一番心理活动。而达芬这个感情爆发的动作却使老人万分感动,便把藏在心里的话掏了出来:
“达芬哪!这话不知我该说不该说……你早该成家了,为啥不呢?你们城里人眼界太高、太高了些。是呵,像你这样的,文化高、挣钱多,在公家里做着官儿,能够般配的男子也实在不多……哎,常言道:女人家,女人家,女人总得有个家呵!”
良久,达芬抬起头来。蒙眬泪眼中发现灶屋边影子似的立着一个年轻女子。那女子似乎不愿窥视别人秘密,忙垂下眼睑,神态安详地把双手搅在围腰里,跨前几步,站在老人身边柔声说:“娘,饭都摆好了,吃吧?”
老人擦着眼睛,说:“桂儿,还不快来叫达芬姐姐!唉,总是这么面浅。这就是我跟你讲过的女知青达芬姐姐呵。”
“达芬姐。”那女子叫了一声,并欠了欠身子。
这是一个容貌端庄、眉目含情的农家姑娘,身材高高的,匀称结实。方达芬脑壳嗡嗡的想不起自己是不是见过她,同时又意识到自己不该显得惊愕。于是便不失礼貌地点了点头。
“她叫常桂枝,我们叫她桂儿。”老人含笑介绍,并亲切地看着桂儿。桂儿便红了脸转身跑入灶屋去了。老人不无骄傲地小声对达芬说:“是豆子的未婚妻。豆子忙得顾不上办婚事。上月里我的腰疼病发了,豆子又不在家,她就住过来了。她家里人说,这样好,早晚对我有个照应。豆子还死封建呢,生怕人家说闲话……呃,你怎么了?”
“没什么,”方达芬把她变得冰凉的手从老人手中抽回,维持着脸上的微笑,“我们吃饭吧,今天真饿。”
饭后无话。
老人见方达芬神色疲倦,断定是累的,忙心疼地拉她上床睡一会。
她果真累了,不由沉沉睡去。五点醒来,眼眶发青,两颊像消瘦了些。她洗了脸,便要回县城去。
老人苦留。
“忙啊,”她说,“以后我还来看你老人家的。”
临别又看了桂儿一眼,桂儿蹲在地上拌鸡食,忙站起来,柔声说:“达芬姐,慢走呵。”神情泰然。没错,这里应是这个村姑的位置。
她走了。沿着走来的山路。当那小小的火车站又进入她的视野时,她看表,上行慢车再有半个小时就该到站了。她需要作出决定:是买回县城的票呢,还是买直达省城的票?
夕阳在身后留下长长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