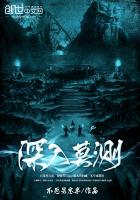我低下头自己拽它,两只短胳膊一点也使不上劲,它还在悠荡。我只好大步快走,在屋里一圈圈地转,想把它甩掉。小狗却像是缝在我衣服上的扣子。我们俩都憋足了劲,不吱声,我出了一身的汗,小狗咬着我裤子的牙是不是累得生疼,我可不知道。
也许我要哭了,也许我还能坚持,这两个结果都没出现,有个人进屋了,一把薅下小狗,扔在地上。我便飞快地往炕上跑,小狗鬼一样地追我。我把着炕沿一蹿高,上半身已经趴在炕上,两条腿也离开了地面,可是小狗还是叼住了我的裤脚。
还是那个人轻轻拍拍小狗的鼻子,它乖乖地松了口。我收回了自己的腿,爬到炕根儿去,再把头掉过来,正好看清楚救我的人了。我把眼睛睁得大一些,再大一些,没有看错!这个人的眼睛真是奇怪,像是年三十的晚上守岁到后半夜,困得就要睡着了,却又不能睡:他深深的双眼皮盖上了大半个眼睛,睫毛又浓又密,像马儿发呆时那样,覆盖了剩余的那部分眼睛。也许这样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视力,他高高地仰着头,从缝隙里看着我,我发现他的眼睛是灰色的,眼仁不很分明。困眯眼,我心里叫了一声。
光顾着端详他,我没有说谢谢,错过了时机,就再也说不出口了。困眯眼也没再理我,脱掉了他的翻毛大头鞋,上了炕,盘好腿,像是早有准备似的抓过炕梢上的一本书,打开,一只长胳膊把书伸到尽头,一只长胳膊取下棉帽子,那本书就倚在他的帽子上,他把两只长胳膊抱在一起,依然仰起头来。
他是摆着书玩儿,还是看书呢?我爬到他前面去,他眼睛的那条缝隙认真地盯着书呢。
我爬回到我的地盘,拿一本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也照着他的样子把它摆得远远的,哈,别扭,没法看。
我瞄了一眼地下的小狗,它本来茫然然地看着困眯眼呢,此刻响应我的动静,回头和我交流了一个眼神,我摇摇头,它抖抖毛,我们一起又去看那个困眯眼了。
后来小狗移到灶坑口处蜷成团睡了,我趴在热乎乎的炕上也迷糊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脑子醒来了,身子还赖在梦中不乐意醒来,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知道爸爸和妈妈都回来了,在说话。爸爸说:“他的眼睛以前是好的,为了救老张,松木砸了他的脑袋,不知道哪根神经被砸坏了,眼睛就这样了。”
“怪可怜的,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呢。”妈妈叹息着说。
“这还不是最可怜的,他……不行了,不能结婚了。”
“哦……”妈妈的“哦”拖了很长,丝丝拉拉的,让人费寻思,“也是因为老张吗?”
“是,谁能想象砸在脑袋上,问题出在那儿了呢?”爸爸声音很轻。
“怪可怜的,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呢。”妈妈重复着叹息。
“老张要把女儿嫁给他,他坚决不答应。”爸爸的声音突然明亮了。
“哪能那么办呢?那两个人就都可怜了。”妈妈更深地叹息着。
怎么了,我怎么听不明白呢?于是,我一骨碌爬起来,说:“妈妈,他怎么不行了?他怎么可怜了?”
问这话的时候,我发现困眯眼不在了,地上的小狗看我醒来开始撒欢,小尾巴又摇了起来,我于是丢掉了刚才的话题,趴在炕沿边儿开始逗它。
大蜘蛛
我哥哥姐姐叫我“贴树皮”,知道吗,这是骂我呢。“贴树皮”是一种很讨厌的虫子,它们肉肉的毛毛的,总贴在树皮上,哪儿都不去。贴那也算了,它们还非常讨厌,颜色和花纹都和树皮一模一样,骗得人以为它也是一块树皮呢。去园子里摘树上的沙果,一不小心碰上“贴树皮”,它们就把带刺的毛毛一撮一撮地刺到你的皮肤里,又痒又疼。
我可没那么烦人。我只是愿意跟在妈妈身边,妈妈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姐姐问过我为什么那么黏人,我说我乐意,气死你。其实有一个小秘密,不好意思说出口,就是因为妈妈漂亮。妈妈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去这里、去那里,可神气了。
这一次和妈妈去供销社排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在一个屋子里。我靠在妈妈的腿上,看着一串一串的后背,密密麻麻的胳膊腿,有点兴奋有点厌烦。就在这时,一个胖阿姨站在我面前,挡住了我。呀,这个阿姨胖得很奇怪,肚子好大呀,就像是衣服里藏着一口大铁锅。她的脸又小又圆,露在外面的胳膊细细的长长的,弯曲着支在腰上,两条腿也是细细的长长的,分开站着。我扬着脸看她,胖阿姨也正好看着我呢,我乖乖笑了一下,就立马想大笑一会儿,因为我发现她有点像蜘蛛,除了一个大肚子,剩下的都是细长的胳膊腿儿。她却只顾仔细地看我,看了一会儿突然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好像故意让大家都听见似的,大声说:“你这小孩这么难看呢,难看死了。”
什么?说什么难看?我难看?“妈!”我拉妈妈的衣角,妈妈没感觉似的,不理睬我,和旁边的人说话。
“哎呀,真是难看死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难看的孩子。”胖阿姨细长的手伸过来了,我知道她是来拧我的脸的,我爸爸的同事于叔叔见了我总要拧我的脸蛋儿。可是于叔叔喜欢我,从不骂我。想到这儿,我愤怒了,举起手啪地打落了她的手。这下妈妈看到了,什么也没说,拉起我就往外走。刚出了大门,我就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妈妈却笑盈盈地,蹲在我面前用她的花格子手绢给我擦眼泪,还说:“哎呀,至于哭吗?还那么委屈。”
“大蜘蛛……骂……我难看呢!”我呜呜咽咽地说不成句。
“什么?大蜘蛛?”妈妈很奇怪。
“就那个只长着一个大肚子的阿姨。”我气鼓鼓地说。
妈妈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你可真会形容。”妈妈拍拍我的头,说,“你看到了,阿姨的大肚子里有个小宝宝呢,她没骂你,是喜欢你。”
“你没听见,她瞪着眼睛骂我长得难看。”一股委屈又冲出了我的眼泪。
妈妈又给我擦掉了,笑眯眯地说:“你还小呢,不懂,这是个风俗。怀着小宝宝的阿姨都想让自己的小宝宝长得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见了别人家漂亮的小孩,就故意骂人家难看,那样肚子里的小宝宝就生气了,没有出生的小宝宝都是很任性的,一定要看看那个小孩有多难看,趴在妈妈的肚子里往外看,心里还说:你不是嫌人家难看吗?我就照着他的样子长了。”
妈妈说了这些话就看着我,我说:“那是什么意思?那只大蜘蛛不是真的说我难看,是吗?”
妈妈打断了我的话,批评我:“不许说阿姨是大蜘蛛。”
妈妈点了一下我的脑门,说,“当然不是真说你难看了,正相反,因为你好看她才故意那样说你的。瞧瞧,我的小石榴一脸鼻涕眼泪的,更漂亮了。”
“哈哈哈……”我和妈妈一起大笑了起来,笑得太阳都一跳一跳的,然后,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看看妈妈的肚子,说:“那我在你肚子里的时候你也骂别的小孩了吗?”
妈妈没说话,只是笑着一直摇着头。“为什么呢?”我追问。妈妈还是不说,拉着我的手回家。到了家,爸爸很高兴的样子,一定是喝了酒了,他每次喝一点酒就可高兴了,爱说话,还给我们发零钱。看到我和妈妈进了屋,爸爸乐呵呵地说:“啊,看我的美人儿回来了。”
我高声回答:“嗯呢,我回来啦!”
我的哥哥姐姐一起笑起来,羞我:“你接什么话把儿,怎么你还成了美人儿了呢?你个‘贴树皮’。”
我才不理他们呢,我连蹦带跳地往里屋跑,回头对妈妈说:“妈妈,你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吧。”
关公脸
妈妈和姐姐刚把晚餐的桌子收拾下去,那个人就进屋了,他一直低着头,在远远的炕边儿坐下了,把自己藏在灯影里。
我看看他,他像一堆无声无息的物件儿,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就转而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我有个坏习惯,扔了饭碗就拿书。可是当我抓着一本新得到的连环画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那是个秋天的夜晚,天气突然冷了起来,我还没有适应,怎么着都是冰凉生冷,像个丢了家的小狗,没着没落的。此刻,火炕虽然热乎乎,但是火墙却冰凉(还不到点炉子的季节),不敢依靠,可是不靠着点什么,昏黄的灯光就把我的新画本大打折扣。我先趴在炕上看,自己的脑袋投下一片暗影恰好罩在画本上,我挪动着身子在炕上转磨磨,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头就抵在了那堆物件儿上,我发现这个地方刚刚好,于是悄然爬起来,后背靠了上去——我是真的忘了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了。十五瓦的灯泡正好悬在我的头上,很快我就非常满意了。那个人的后背厚实又温暖,生硬的椅子背和冰凉的火墙怎么能比呢?画本一页页地翻过去,那个人像是领会了我的心情似的,他厚实温暖的后背迅速升温,我于是把自己团好,像一只灶台上的老猫,紧紧地依着他。
画本很快看完了一遍,看第二遍之前,我想听听爸爸和那个人说话。嗨,这两个人可真逗,说是唠嗑,前一句都凉透了,第二句还没说出来呢。我听出来了,那个人要是不开口,爸爸就绝不吱声。这可是很少见,爸爸可爱说话了,还有趣,家里一来人,总是热热闹闹的,这次是怎么了呢?我伸头一看,原来爸爸是那个样子啊:爸爸不是坐着是躺在炕上的,后脑勺下面不是枕头,是抵在墙上的。爸爸的腰焐在火炕上,他喜欢用热炕暖腰。而爸爸的左腿曲起,右腿搭在左腿上,就像坐着的人翘起的二郎腿。爸爸喜欢这样,这个姿势我没看见第二个人摆出来过,可是,有时候我看到爸爸这个样子会很不满,比如他用这个姿势询问我的学习成绩。那样跷着二郎腿,而且因为脑袋的位置很高,眼皮就耷拉着,小看人似的,我就气得不行,难道我的成绩可以被耻笑吗?不过,当爸爸这样讲故事的时候就无所谓了。
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屋了,本来是坐在那个人的对面的,又匆匆站起来越过我去摸火墙,还小声地嘟囔:“没生炉子啊,火墙冰凉,这孩子怎么热成这样?”听了妈妈的话,我马上侧转身子,把头探到那人的前面,啊,他满面通红,一脑门汗珠子,我伸出手指一碰,一行汗水哗地流下。妈妈低声叫我到炕梢儿去,可是谁愿意离开这个人肉小火墙啊,不去!妈妈就悄悄拽我的脚脖子,我就口中不停地嚷嚷着。那个人慌张了,起身告辞,我失了“靠山”很生气,坐在那儿发呆。妈妈出去送客人,回来之后问爸爸:
“这孩子怎么回事儿?火力那么旺呢,热得汗水快成小河了,脸都成了关公了。”
爸爸“哼”了一声,很生气似的:“口讷。”
“什么叫口讷?”我插嘴。
妈妈瞪了我一眼:“说话费力。”转过头问爸爸,“他要说什么呢?”
“还能是什么?上大学呗,这孩子就喜欢读书。”爸爸愤愤地说,“他自己不提出这个要求,我就不管,不给他列入推荐名单,我还不信了!”
“哎呀,老安,你那是何苦?这孩子一看就是好孩子,既然你知道他的心愿就成全他嘛。”妈妈抱不平。
“你以为他这一辈子就遇见这么一件难开口的事情吗?这孩子是条龙,可他要是不改了懦弱这个毛病,念再多的书也是条虫。”
“他要是始终不敢开口,你还真不让他念大学了吗?”
“不让。”
“那名额不是就白瞎了吗?”
“白瞎什么?这世界好孩子就他一个吗?”
“你心肠够狠的。”妈妈说得有些伤心。
爸爸最后说:“你以为我舍得吗?我是下了狠心的。这孩子是我们大修厂最好的孩子,技术好,人品好,有担当,就是那么一个毛病。可是这一个毛病却是天大的,如果他不改,明年还没他的份儿,我非扳正他不可了。”
我似懂非懂地听了爸爸妈妈的对话,从此当成一件要紧的事情了。爸爸一回家,我就跑上去问他:“关公脸说了吗?”
妈妈也放下手里的活计看爸爸的反应。直到有一天,爸爸一进门,没等我跑上前,就乐了,冲妈妈说:“那小子终于金口大开。给我热酒吧。”
其实,妈妈还给爸爸炒了一大盘子鸡蛋,我们都跟着吃得热火朝天。吃了饭,放下筷子我大声说:“妈妈,我有个要求,我想要一件新衣服,我不想总是捡姐姐穿剩的。”
妈妈奇怪地看着我,半天说:“为什么呢?都是这样啊,家家小孩子要捡大孩子的衣服啊。”
我的眼泪要出来了,可是我用力忍住,一句一句地说:
“是的,我知道,可是我都八岁了,除了过年,就没穿过一件属于自己的新衣服,一件也没有,太不公平了。”
妈妈还想说什么,爸爸哈哈大笑了:“好吧,这事我做主了,明天就让你妈妈给你做一套新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