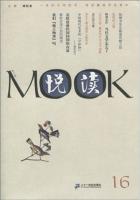——读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
吴投文
从早期白话新诗的起步开始,长诗似乎就不断地遭遇困境,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概而言之,大概包含这样几方面:一是中国向来缺乏长诗传统,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源头性的缺失,对新诗的影响甚大,但新诗研究在此方面没有做系统而深入的清理;二是长诗缺乏清晰的边界,到底多长才算长诗,一直没有定论,实际上也很难达成统一的意见,这是在创作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面临的一个难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这对长诗创作无疑会带来某些不利的后果;三是长诗在“长度”之外,还在内涵与结构上有一些特殊要求,这又很难达成共识。此外,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有待探讨,但在新诗创作和研究中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长诗的历史价值与艺术定位也往往比较模糊,不能在文学史格局中获得独立的身份认定,也就不能充分彰显自身的艺术特性,这样,长诗的美学特质也就不能凸显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长诗创作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在中国新诗史上,也不乏气象阔大的长诗杰作。著名诗评家叶橹先生极有见地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始终不能出现能够抒写杰出伟大的长篇诗歌的大手笔,必定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缺憾和悲哀。”(叶橹:《呼唤长诗杰作》,为洛夫主编《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一书所写的序言,台海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页。)可以说,长诗具有精神界碑的性质,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长诗写作也是极富挑战性的创造工程,大概也是检验诗人才华与心智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有创作雄心的诗人往往会向长诗发起挑战,殚精竭虑地投入到长诗创作中来。实际上也是如此,在长诗创作上取得成功的诗人,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这大概也是很多诗人倾注全部心力投入长诗创作的一种隐秘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讨论撒拉族著名诗人阿尔丁夫·翼人的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也许能找到进入文本内部的某种依据,同时呈现出这部长诗的独特价值。从阿尔丁夫·翼人的写作历程来看,他成名颇早,是当代中国诗坛的一位实力派诗人,尤其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界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先后获得青海省人民政府第四届文学作品奖、中国第四届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当代十大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等重要奖项。从他的主要创作来看,长诗代表其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三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长诗创作,史诗性长诗《漂浮在渊面上的鹰啸》《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等就是当代长诗创作有代表性的成果。他的创作路子显示出自己独立的艺术追求,没有被诗坛的流行色所遮掩,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容易,从中可以发现阿尔丁夫·翼人诗歌创作寻求创新的艺术自觉和独特的艺术情思。
当我们把目光聚集到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上来,就会感到有一种独特的气场笼罩着我们。这是一部在诡异的氛围中流露出深沉的悲剧意识、清醒的历史意识和人文情怀的作品,是一部具有广阔的民族诗史视野的抒情长卷。从长诗的篇幅来看,可谓结构浩大,全诗共五十六节,每节长则二十余行,短则数行,但大多数介于十行至二十行之间,这不仅使每一节显得相对匀称,也使每一节自成精短的篇什,在环环相扣的推进中显示出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从长诗的整体处理上可以看出作者用心甚深,在长诗中有一个整体性的象征框架,沉船既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又是这个整体性象征框架的核心,在长诗中被处理为一种内置性的基本元素,无处不在,但又很少直接道出,这使长诗的主题表现出某种晦暗性,也许不那么好容易把握,但又同时表现出某种开放性,让人在诗意的迷宫里对现实和人生有一种透彻的认识。在我看来,沉船之沉在这部长诗中表现为一种历史思维和神话思维的浑融化一,诗人的思考带着严峻的历史反思意识,在诗人苍劲的笔触中,民族的历史和现实都被置于一种犀利而充满痛楚的审视之中。就此而言,这部长诗具有精神寻根的意义,诗中有一种回溯性的声音,这种声音既是作者个人的,然而个人的声音似乎又被淹没在历史的回声中,因此, 在这部长诗的声音后面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磁场和空间,值得我们注意。
从长诗的主题内涵来看,似乎是具有多重指向性的,尽管这里很难对此进行比较清晰的剖析,但也可以从诗中所显露出来的蛛丝马迹中发现诗人隐秘的意向。大致而言,长诗关乎对于历史的基本理解,却又具有现实的维度;关乎灵魂的受难,尽管显得沉痛,却又并不显得完全虚无;也关乎对个人命运的理解,其中似乎纠结着一些复杂的情绪,诗人对个体在历史中的迷失似乎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又显得疑虑和困惑,诗人对个人与历史的对抗显然有所期望,但又似乎陷入很深的失落之中。因此,长诗的主题内涵并不指向一个透明的实体,这表明诗人的历史感可能是发散性的,也表明诗人对历史的某种疑虑和对现实的警惕。当然,也有一种在历史面前的无力感,毕竟历史是无形之物,也布满无物之阵,那种吞噬性的力量很容易使人产生恐慌而陷入更深的困惑。长诗在历史、现实、想象、存在、神话元素所形成的张力结构中,隐含着一个精神寻根的深层意义结构。正如诗人在长诗的“题记”中这样写道:
我认识一条河
这便是黄河
这便是撒拉尔
对河流永恒的记忆
和遥远的绝响
精神寻根表面上看起来是退却性的,是向虚无中的逃遁,但同时也意味着寻找与皈依,是一种面向自我反思的精神形式,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健全的历史理性和现实批判精神。另一方面,这种精神寻根也意味着皈依与拯救,寻根的过程也是一种历史建构和精神建构的过程,表现为对精神家园的向往,对纯粹诗性存在的追寻,这使长诗显露出一种深沉的现实忧思,而诗中间或出现的荒诞元素,则似乎透露出诗人内心的焦虑,同时也使诗人的忧郁得到放大和强化,也使长诗的主题意向显露出由精神寻根所带来的复杂意绪。这在长诗的推进中似乎随处可见:
出门是山
紧闭是河 山河哟
世界的本源对于存在者而言
船队横对头顶的浮云
苍老地流过—— 一任河的主人惊叹不已
谁的双脚企图同时跨进同一条河流?
纵有风暴袭来 却依然保持一丝微笑
瞧 苦水包容的思想在你的腹中筑巢
阿尔丁夫·翼人笔下的这一阔大场景似乎具有某种提示作用,暗示精神寻根的艰巨过程,也包含着一种豁达的理性精神。实际上,精神寻根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逃亡,而逃亡并不等同于逃避历史责任和现实担当,而是寻找救赎和希望,是在反抗的层面上落实一种健全的生命意志。同样的场景多次出现,隐喻逃亡与精神寻根的某种对应性关联:
哦,河流 生命的绝唱
万象众生的意念
世界的象征宛如血色宛如黄昏
宛如废墟中长出的一枝荷花
以最动人的笑脸 四面捭阖
呈现出无数血腥的花朵
逃亡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主题,但在不同作家的笔下被处理为不同的文学想象。鲁迅的《野草》是作家从茫然到清醒的逃亡,又因过于清醒反而迷失于虚无中,把一种大的哀痛留给读者而显示出思想的深刻与锐利,也显露出作家面对现实难以掩抑的沉痛与矛盾心态;沈从文的《边城》是作家放逐自我的精神逃亡,出走故乡湘西固然是一种逃亡,处身都市而又在精神上退回湘西,潜心建构文学的“湘西世界”,同样是一种逃亡,边城不过是沈从文心造的幻影,他把现实中感受到的悲哀与沉痛用微笑掩抑起来,把一种似乎愉快的心情涂抹在一片桃花源式的风景中,而他自己则隐遁在一个审美的乌托邦中;钱锺书的《围城》所揭示的现代人的生存悲剧与精神困境,同样是一个逃亡的主题,不管是城堡中的人,还是城堡外的人,其实都处于精神上的漂泊状态,而且由于人性固有的弱点,每一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封闭的城堡,不仅他人很难进入,其实自己也难以进入,因此,从本质上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立的城堡,不仅与他人难以取得沟通,也往往游离于自己的内心,这样,人就成为自己的地狱,无法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宿,只能永远流浪在逃亡的路上,或者在进退之间游移。在这些作家的参照下,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中的精神寻根及其伴生的逃亡意识则具有鲜明的当代性。也就是说,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具有直视当下的问题意识,它并不是一个纯然从作者的想象中冒出来的抒情篇章,诗中似乎有一种被压抑的悲郁,既回荡着灵魂的被放逐感,又有与现实对接的忧患意识。诗人阿尔丁夫·翼人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既为历史悲歌,也为现实抒唱,既为自己的民族留下历史的记忆,也为自我的生命打下来自现实的烙印,因此,长诗的主题意向实际上是展开性的,显示出复杂的意蕴,对于读者来说,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应该说,作为一部长诗,《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包含着很多成功的元素,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长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与汉民族文学相比,西北边地的少数民族文学似乎在长诗创作上有着天然独特的优势,显示出边地少数民族特殊的艺术禀赋。对阿尔丁夫·翼人来说,他也得益于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的滋养,尤其是得益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撒拉族的艺术传统,这在《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中似乎不难找到通向撒拉族艺术传统的特殊暗道。这应该是阿尔丁夫·翼人与撒拉族艺术传统的一次对话,也可以理解为是他对自己民族的一次深情礼赞与致敬。同时,从《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中也可以发现诗人得益于域外文学的启示,长诗中似乎游荡着西西弗斯神话的余音,长诗中的悲凉感显然与此有关,西西弗斯的巨石是苦难的源泉,既是惩罚,实际上也是重生,在长诗中则转化为一种清醒的自我发问,难道这块巨石就是周而复始的徒劳无望的命运的象征?此外,长诗所展示出来的个人视野也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的创作也得益于但丁的《神曲》、米尔顿的《失乐园》、艾略特的《荒原》等作品的启示,阿尔丁夫·翼人大概对这些作品做过用心的研读,《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中的气息显示出诗人接受域外文学启示的开放性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的篇幅较大,可以看出诗人刻意经营的苦心,但却没有雕琢的痕迹,长诗的主线似乎与诗人情绪的推动息息相关,显示出结构上的别致。全诗可谓一气贯通,如九曲回廊,有一种沉思的静美,在九百余行的抒情咏叹中,将个人的心路历程与民族的精神寻根提炼为一个充分个性化和概括性的诗性形象,作者的艺术抱负值得称许。同时,长诗以情绪的流动和升华作为主线的结构方式,尽管有一个精神寻根的象征性构架作为支撑,但由于没有基本的情节框架作为显性的叙事标志,读者也可能一时难以理清长诗的思想脉络和主题意向。好在长诗有一种内在的音乐效果,这种结构方式也有利于增强诗歌的艺术张力。就这部长诗的语言来说,作者显然是有考虑的,既没有着迷于满纸晦涩,也没有停留于直白的倾诉,而是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有坚硬的质地和饱满的张力,长诗的整体节奏与作者的内心情绪协调一致,即使读起来也有一种一气贯通的效果。诗人一方面似乎怀着忧郁,这使长诗的背景有一种冷抑的底色,另一方面又由于诗人性格上的豪放,诗中又有着内敛的激情,因而长诗的整个基调显得沉郁悲慨、苍凉浑厚,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从整体上看,长诗显示出诗人对精神寻根的独特理解,这使《沉船——献给承负我们的岁月》成为一部具有丰富象征意蕴的作品,这也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
吴投文,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批评家。1968年5月生,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有学术专著《沈从文的生命诗学》等。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两百余首,出版有诗集《土地的家谱》等,有诗歌入选《2007中国新诗年鉴》《2008—2009中国诗歌双年巡礼》《新世纪诗典》《2010年中国诗歌选》《中国当代诗歌导读(2010卷)》等二十余种诗歌选本。另有一些诗歌评论发表。兼任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湘潭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湘潭市文学研究会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散文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