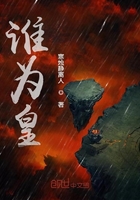登时,帐中一片寂静,未熄的烛火轻微一声“噼啪”,此时听来分外燥人。
他徐徐起身,淡然望着不远处高耸的城墙:“孙将军,你可知侮辱主帅乃是死罪?”
戎马半生的铮铮铁汉,忽而泪流满面,“叛军……八万之众,区区……区区两万人马……末将……末将已眼见六万弟兄……战死九函……你天潢贵胄……流血漂橹,流血漂橹你可见过?好不容易等来援军,却……”
九函关外,大漠茫茫,此时,似是漫天风沙越过了厚重的城墙,卷进了军帐,帐下诸将皆红了眼圈。
孙诚拭一拭泪,咚地跪地,“末将身为九函关主将,既守不住关隘,又不能保部下性命,还有何面目苟活人世?末将既然侮辱主帅,你便砍了末将吧!”
他轻声一叹,眼下一抹青色若昨夜笼在雾色后的山峦,那样沉重,那样迷蒙,“白卿,再添杯茶来。”
瞬间的酸楚如七弦琴上的蚕丝弦,紧紧地绷在心上,我牢牢握住他温热的手,“师兄,浓茶伤身,你已劳累一宿,莫再饮了。”
累?
一宿?
帐下一中年悍将愤然道:“我九函关将士浴血奋战,你身为主帅,却与男宠彻夜厮混,怎对得住战死的弟兄!实在让我等寒心!此仗不打也罢!”
哼,这军营老油条,心思不堪、又耍无赖,委实欠些教训!
一缕晨光照上他清俊的颊面,我才见他双颊绯红异常,赶忙抬手探向他的额头,陡然一惊:“师兄,你……”
他轻轻摇头,嘴角一抹笑意,如风动即散的轻云,“白卿,添茶。”
中年悍将嗤笑:“此乃议事军帐,不是你二人谈情说爱的野林子!”
忍无可忍!
一股怒气如雨后的鲜笋,噌噌蹿了起来,我扶他好生坐下,眸中凝起凛然之色,“你等便不问,赵将军领兵去往何处?”
高座之侧,我负手而立,明媚的日光拂了我一身锦绣,圣洁庄重的姿容不容侵犯!
众将皆是一怔,仰头愣愣地望着我。
广袖一拂,素手指向兵防图上的一点,“云门,赵将军与梁副帅领兵去往云门。”
一语既出,众将愕然。
孙诚疑惑:“这……”
我冷笑:“薛绪得九函关后有两条出路:其一,坚守,可朝廷兵马集结,夺回九函关不过是费些时日,他取后即失,岂非白费力气?”
略略一顿,回眸望他,他幽深的黑眸荡漾了春水般明澈的笑意,心头些微的惊慌一扫而空,唯余指点江山的从容与霸气。
我淡然续道:“这第二条路,便是直捣京师。可,京师重兵把守,他西南弹丸之地,再战京师必是后继乏力。如此,薛绪得九函关并无实际助益,他却在此虚耗半月有余,你等不觉蹊跷?”
孙诚沉吟:“嗯……”
我一笑,若艳阳冲开了迷雾:“云门,西南门户之地,薛绪一得云门,西南便成割据之势,我等若再想攻入叛军老巢池州,便是难如登天……”
孙诚大惊失色:“你是说,薛绪意非九函关?他……他是想牵制我军于九函、明宁二处,趁机取云门,割据西南之地,养精蓄锐,来日再做他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