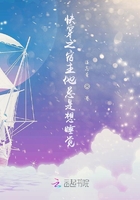毫无疑问,马市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是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不管怎样,在那里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马市上,有成排成排来自乡下的年纪不大的马儿,他们刚刚离开湿地;有成群成群的长着蓬松长毛的威尔士矮脚马,他们个头不比快腿高多少;还有上百匹各种各样的拉车马。其中有些马的尾巴被编成辫子,用鲜红色的细绳系起来;还有很多马长得跟我一样漂亮,品种优良,只是遇上过意外或有什么缺陷,要么是呼吸有问题,要么是有其他毛病,所以才落到“中产阶级”的地步。有些正处于壮年的马儿,身体非常棒,什么活儿都能干。他们被人拉着缰绳小跑的时候,就会放开腿脚,向人们展示稳健的步伐,这时马夫就在一旁跟着跑。绕到马市的后面,还能看到很多可怜的家伙。他们已经被重活压垮,膝关节没法伸直,每走一步,后腿就直打哆嗦。那儿还有许多表情沮丧的老马,下嘴唇耷拉下来,耳朵朝后面靠,好像生活中没了快乐,也没了希望。有的马儿很瘦,你可以看清他们身上每一根肋骨。还有的马背上、屁股上有着以前留下的伤疤。看到这一幕幕悲惨的情景,我们很难受,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或许有一天也会落到这种下场。
在马市上,人们常常讨价还价,卖家出价高,买家就把价格砍下去。要是马儿能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出来,那么我要说,连聪明人都没法说清马市上的谎言和骗人的伎俩。我跟两三匹强壮、能干的马儿待在一起,有很多人过来看我们。我的膝盖上有个明显的伤疤。尽管卖我的那个人发誓,那只是我不小心在隔栏里滑了一跤造成的,可是绅士们一看见它,扭头就走。
买家先是把我的嘴巴掰开来看看,再检查一下我的眼睛,接着把我的四条腿摸个遍,用力拍拍我的皮肉,最后骑着我试了试。非常有趣的是,不同的人做这些事情也各不相同。有的人做起来手脚很重,就像把我们当成一块木头;有的人用手轻轻地摸遍我们的全身,还不时地拍拍我们,就像在说:“请别介意。”当然,我能够通过他们的动作判断出买主是个什么样的人。
有一个人,我觉得,要是他能买下我,我会很高兴。他不是绅士,也不是那些华而不实的自称绅士的家伙。他的个子相当矮小,可是身材匀称,手脚麻利。他一碰我,我就知道他很熟悉马儿。他说话的口气很温和,灰色的眼睛里透着和善、欢快。可能这么说有点奇怪——可这是真的——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清新的气味让我很想亲近他。他身上没有啤酒和烟草的味道(我很讨厌这种气味),只有清新的气味,好像他刚从干草棚里出来一样。他出二十三英镑买我,可是卖我的那个人不肯,于是他就走了。我的眼光追随着他,可他还是走了。这时,一个长相冷酷、嗓门很大的人走过来。我生怕他会买下我,可是他也走了。又有一两个人过来看看我,可并不想买。接着,那个长得一脸冷酷的男人又回过身来,出二十三英镑买我。卖我的人也觉得自己开的价太高了,得往下降一点。这笔交易眼看就要成交了,就在这时,灰眼睛的那个人又回来了。我忍不住把脑袋往他身上蹭。他也轻轻地抚摩我的脸。
“好吧,老兄。”他说,“我想我们互相让一步吧。我出二十四英镑买他。”
“二十五英镑,你就把他带走。”
“二十四英镑十先令。”我的朋友用非常坚定的口气说,“多六便士都不行,怎么样?”
“成交。”卖我的那个人说,“他身上有很多难以置信的优点,要是你用他来拉车,那你可就赚了。”
他当场就把钱付清了。于是,我的新主人拉着缰绳,牵着我出了马市,来到一家小旅馆,在那他已经准备好了马鞍和笼头。他先给我吃些燕麦,自己就站在一边看着我,有时候自言自语,有时候跟我说说话。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出发去伦敦了。我们一路上走得很稳当,穿过舒适的小道和乡间小路,最后来到伦敦的大街上。傍晚时分,我们来到这座大城市。煤气灯早已经点亮。左边是街道,右边也是街道,还有的街道互相交叉,延伸出好几英里。我想我们一辈子也走不到头了。最后,我们穿过一条街,看到排成长长一列的出租马车。我的主人用欢快的口气喊道:“晚上好!管理员!”
“你好!”一个声音传出来,“买到好马了吗?”
“我想我买到了。”我的主人回答。
“祝你好运!”
“谢谢你,管理员。”他骑着我继续往前走。我们很快转进一条街道,走到一半,又拐进一条狭窄的胡同。胡同的一边是破旧的房子,另一边看起来像是马房和马夫住的地方。
我的主人在一户人家前面停了下来,吹了声口哨。房门打开了,出来一个年轻的妇女,后面跟着跑出来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主人下马的时候,受到他们热情的欢迎。
“现在,哈里,我的儿子,把栅栏门打开。妈妈帮我们把灯点起来。”
很快,我已经站在马房前的院子里,主人一家围在我身边。
“他温和吗,爸爸?”
“是的,多丽,就像你的小猫一样温和。过来,拍拍他。”
于是,一只小手大胆地拍遍了我的肩膀。这种感觉好极了!
“你给他洗刷的时候,我给他吃点麦麸粉。”妈妈说。
“就这么办,珀丽,他现在正需要吃点什么。我知道你已经为我准备了好吃的土豆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