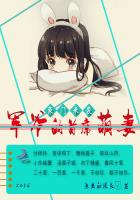等膝盖的伤口愈合后,我被送到一个小型的草场上待了一两个月。那里一只动物都没有,我可以享受无拘无束的自由,还有那美味可口的青草。可是,我已经习惯了群居生活,所以我感到很孤独。我跟辣姜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现在我非常想念她,真希望她能陪在我身边。每当听见大路上传来马蹄声,我就不停地嘶叫,可是很少得到回应。直到有一天早上,草场的大门打开了,进来的正是亲爱的老辣姜。有个男人把她的笼头摘下,然后就把她留在这儿。我一路欢快地嘶叫着朝她跑去。我们都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对方,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并不是为了让我们高兴才把她带到这儿来。她的故事说来话长,可是结局就是,过度的奔跑毁了她的身子,现在被送到这儿休养一阵子,看恢复得情况如何,再决定怎么处置她。
乔治少爷太年轻,不愿接受别人的劝告。他是个冷酷无情的骑手,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出去打猎,不管马儿是不是受得了。在我离开马房以后不久,有一场越野障碍赛马比赛,他决定参加。尽管马夫告诉过他,辣姜有些疲惫,不适合参加比赛,可是他不相信。在比赛那天,他不停地鞭打辣姜,拼命追赶前面的选手。辣姜兴致高昂,用尽了所有力气,终于和跑在最前面的三匹马一起跑到终点。可是,她的呼吸受到了严重损害。此外,乔治少爷的身体对她来说太重,她的后背也拉伤了。“所以,”她说,“我们俩现在都在这儿——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被毁了——你被酒鬼毁了,我被傻瓜毁了。这真是残酷啊。”我们都觉得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俩在一起享受快乐时光。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奔跑,而是常常一起吃草,一起躺着,或是一连好几个小时头靠着头站在酸橙树荫下。我们一起度过那段时光,直到伯爵一家从伦敦回来。
一天,我们看见伯爵来到草场,约克跟在他身后。看清了是谁后,我们仍然站在酸橙树下,等他们走过来。他们仔细地把我们检查了一遍。伯爵看起来很生气。
“三百英镑就这样白白扔掉了。”他说,“可是我更关心的是,这两匹马儿是我的老朋友托我好好照看的,他觉得他们在我这儿能过上好日子,现在却被毁了。这匹母马需要休养一年,到时看看她恢复得怎么样。可是这匹黑马,他必须卖掉。实在太可惜了,可我不允许我马房里的马膝盖伤成这个样子。”
“是,老爷,当然不能再要他了。”约克说,“可是或许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在那儿他们对马儿的外形要求不高,又能很好地照料他们。我知道巴斯有一个人,开了好几个代养马房,他常常收购那些价格低廉的好马。我知道他照料马儿也很在行。那次调查已经澄清了这匹马的名誉,再加上有老爷您或是我的推荐作为担保就可以了。”
“你最好写信给他,约克。我对他那个地方比他能提供的价格更感兴趣。”
接着,他们离开了。
“他们很快就会把你带走。”辣姜说,“我马上就要失去唯一的朋友了,很有可能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面。这个世界真残酷啊!”
一个礼拜之后,罗伯特来到草场,手里还拿着马笼头。他把笼头戴在我头上,牵着我走了。辣姜没有被牵走。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们互相嘶叫。她沿着树篱焦躁地追着我跑,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直到她再也听不见我的蹄声。
在约克的推荐下,我被代养马房的老板买下了。我得坐火车去他那儿,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儿,第一次坐火车需要很大的勇气。可是我发现,火车喷出的烟雾、飞快行驶的速度、汽笛鸣响的声音,特别是车厢的震动,并没有给我带来实质性的伤害。于是,我很快就安静下来。
到达目的地时,我发现自己待在一个还算舒适的马房里,被照料得也不错。可这些马房跟我以前待过的马房比,就显得不那么透气,也不是很舒适。隔栏地面是倾斜而不是水平的。我的脑袋一直被拴在饲料槽上,我只好站在斜坡上,所以感到很累。人们好像并不知道,要是马儿能站得舒服一些,能够自由转动身体,那他们就能干更多的活儿。我吃得很好,身上也洗得干干净净。总的说来,我觉得,这位主人还是尽量把我们照顾得很周到。他养了很多好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马车,都是用来出租的。有时候,他手下的人出去驾车;有时候,把马和马车租给那些愿意自己驾车的绅士或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