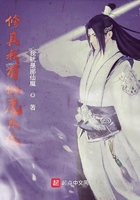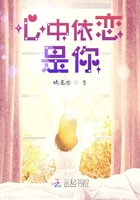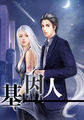人们都承认,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诸多不同。例如,从家庭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被认为是一个赋予家庭以特别重要地位的文化,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家庭至上主义(familism)的社会;还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我近几年在与家庭婚姻有关的问题上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生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等),也为这种差异提供了证据;但是,我认为家庭至上主义、家庭本位这些提法只是对现象的概括,还不是对它的解释。为此,我尝试提出中国的“大概率现象”和中国人特有的“大概率价值观”这一对概念,以便对上述文化差异作出解释。一、中国的“大概率现象”
综观我近年所做的有关中国人婚姻家庭行为方面的实证调查材料,印象最深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相当的整齐划一,在结婚、生育、婚前性关系、婚外恋、离婚等类事情上,人群大都呈现出一种“大多数对极少数”的不均匀分布;而西方社会则不然,在上数各个方面往往只是一般的“多数对少数”的分布。
例一: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30岁以上的从未结过婚的人口只占30岁以上人口总数的2.81%;而在美国,每四个家庭中就有一个是单身者家庭;在加拿大,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单身者家庭。
例二:在我国,自愿不育者仅属凤毛麟角,百不挑一,他们的选择也常常被人视为怪异;而在原西德,全部夫妇中生儿育女的只占约60%;在80年代的美国,18至34岁的妇女中自愿不育者占到11%,在较为激进的大学当中,自愿不育者的比例在1970年曾经高达18%。
例三:根据我在北京市所做的随机抽样调查,样本中承认自己有婚外性行为的只占3.7%,加上没有发生性关系的婚外恋,也只占6.4%。但在美国,40多年前金西做调查时,40岁以下的人当中,承认自己有过婚外性行为的在女性中占到26%,在男性中高达50%。1980年的一项全美调查表明,美国有婚外性行为的人在男性中占60%,女性中占35-40%。在澳大利亚26至50岁的女性中所做的一项抽样调查也表明,43%的人有婚外性行为。
例四:在北京市随机抽样样本中,对男性婚外性关系持反对态度的高达95.4%,对女性婚外性行为持反对态度的更高达96.2%。人们对有感情因素在内的婚外性关系稍微宽容一些,但持否定态度者仍高达93.1%(针对男性)和94.5%(针对女性);而在西方社会中,一般公众对婚外性关系的容忍程度却要高得多。”’
例五:根据我的北京市随机抽样样本,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只占15.5%(其中包括相当数量随后结婚的伴?);而在一项对美国15至19岁未婚女性的调查中,已有过性经历的占到92%,其中60%以上的人在15至16岁发生第一次性关系;另一项对澳大利亚大学生的调查也表明,45%的男性和27%的女性有过婚前性行为。”’
例六:根据北京市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对婚前性行为持允许态度的人仅占样本的30.5%,其前提还必须是“两人确定关系已准备结婚”;如果仅仅相爱尚未决定是否结婚,则持允许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数比例下降至11.3%;假如把前提换做仅仅是两性偶然互相吸引(无感情因素在内),则持允许发生婚前性关系的人数比例继续下降至区区2.7%。相比之下,西方社会的婚前性容许程度要宽容得多,例如,在以色列克布兹人中,有76%的男青年和55%的女青年认为,只要有感情即可发生性关系;就连算不上是个完全的西方国家的原苏联,婚前性容许程度也高于中国(38%的调查对象对婚前性关系持肯定态度)。
例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离婚率近年虽有提高,但仍然保持在1.43%(以年平均人口为分母计算)的低水平上,相比之下,西方社会的离婚率要高得多。”’
以上举例旨在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国,一切有异于常人的行为,无论是单身、不育、离婚,还是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所面临的都是占压倒优势的人群和他们所崇信的行为规范。仅仅这种“极大概率”对“极小概率”的不均匀分布本身,就在无形中给隶属于“极小概率”行为模式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更不必说前者对后者的不宽容、不理解甚至厌恶的态度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了。即使属于“极大概率”的人们对属于“极小概率”的人们能够持善意的宽容态度,后者的处境也远远比不上那些在同类的事情上“三七开”或“四六开”分布的社会中的少数派所享有的地位和处境。二、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是指人们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什么是值得赞扬的,什么是应受谴责的等等。我提出的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则是指这样一种文化心理,它认为:凡是大概率事件(行为)就是可取的、正常的、值得赞扬的;凡是小概率事件(行为)就是不可取的、病态的、应受谴责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一个“大多数”和一个“极少数”的不均匀分布,所以“大概率价值观”就特别盛行。具体到前面的那些例子上面,中国人往往会持有这样的价值观,即认为到岁数结婚,生小孩、不搞婚外恋、不搞婚前性行为、不离婚、只搞异性恋是可取的、正常的、值得赞扬的;而到岁数不结婚(更不用说终生不婚),不生孩子、搞婚前性行为、婚外恋、离婚,同性恋等等,由于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因此就是不可取的、病态的和应受谴责的。换言之,我们的社会不仅在许多事情上呈现出“大多数”对“极少数”的不均匀分布,而且还拥有一种肯定大多数否定极少数的价值观;而西方文化则不然,那里的人不仅在上述的许多方面不存在“大多数”和“极少数”这样的相差极为悬殊的分布,而且也没有中国文化中那样严厉否定少数的价值观。在西方社会里,人们早就习惯了不对他人作价值观评判(It lS not my business,“这不关我事”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也许只有神职人员例外。
每一种价值观的提出,总要有某种理由作为依据(或解释),摩西十诫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理由是杀人损伤别人的肉体。偷盗夺走别人的财产,都是同类相残的行为。而同类不可相残,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道理。然而大概率价值观却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它可以不必提出什么特别的理由,而认为仅仅提出一个理由就足够了――因为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所以就应该这样,而不能是别的什么样子。当然,大概率价值观在每个具体问题上还是有其理由的,比如,人人都应当生育的理由是延续种族和家庭;人人都应当结婚的理由是性行为应当在婚内进行,人人都应该是异性恋者的理由是同性恋不能产生后代,等等。但是,信奉大概率价值观的人们会认为,提出这些理由并不重要,甚至并不必要。只要说大多数人都这样,理由就足够充分了。
迪尔凯姆曾提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区分,前者如家庭,人们一出生,就不知为什么(没有任何目的的)聚在了一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机械的团结;与此相对应的是为某种特定的目的聚在一起的人群,比如商业团体、宗教团体等等。在我看来,大概率价值观属于“机械团结”的范畴。它是没有特定目的的人群所拥有的价值观。它的产生仅仅是因为在这个人群里多数人是这样生活的,都持有这样的价值观。
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宗教的作用很容易察觉,后者有形的宗教较为少见,众人就起了宗教的作用,社会本身就是上帝。这就是说,“从众”行为在我们这里,带有宗教信条的性质,在极少数人和大多数人发生冲突时,这少数人不仅是冒犯了众人,而且他们身上还带上了宗教异端的色彩。而大多数人是那样的喜欢做卫道士,好像他们是神职人员。这就解释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为什么这么少,“中庸”的思想为什么这样深入人心。人们总是宁愿把自己淹没在“绝大多数”之中,这不仅使他们感到安全,而且最符合这个社会的价值观。
大概率价值观在我们的社会中除了起到宗教的作用之外,还起了第二立法者的作用,甚至法律在大概率价值观面前也会变得没有力量,因为“法不责众”。
福柯曾把他所在社会中人称为“我们另一种维多利亚时期的人”;马尔库塞也曾把他所在的社会中人称为“单向度的人”。这些议论引起了我极大的困惑。如果那里的人们尚且被称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和单向度的人,我们这里又是什么呢?因此我有个假设:假如世界上存在着敏感人群和钝感人群的话,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钝感人群了。
当然,我这样来引述以上两位大师的话,多少有点歪曲了他们的本意。他们是说,一个自以为是丰富的社会,很可能并不丰富;一个自以为宽容的人群很可能并不宽容。在我看来,一个社会多少有了一点丰富,才能继续讨论丰富的问题;多少有了一点宽容,才能继续谈到宽容的问题。假如一点都没有的话,这些问题就无从谈起。福柯和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评因此在我们这里显得“超前”。我们的社会在家庭、婚姻、性爱等方面以及许多其他的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目前西方社会的丰富和宽容程度,人们的生活方式显得极为单调,人们的价值观也显得相当严厉,而“大概率价值观”正是这一切的病根。
由于国人中盛行“大概率价值观”,于是整个社会中的个人生活衍生出一种“无趣化倾向”。所谓“无趣化倾向”概括地说就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麻木不仁和单调,它的对立面当然是千姿百态、千奇百怪、生动活泼和多彩多姿。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远些,就会发现大概率价值观绝非唯一的文化图景。世界上存在着相对宽容、相对丰富的价值观。相比之下,大概率价值观显得欠生动,包含的信息量也少得可怜。但是,这绝不是说,在大概率价值观的统治下就完全是死气沉沉,像热力学所说的热寂那样。如果仔细考察,还可以看出一些活动的迹象。举例言之,我调查了一个村子,其中所有的男青年都要结婚,把积蓄的大部分用在婚姻大事上,在这一点上毫无例外。但是有人能请三十桌客,有人只能请二十桌,于是产生了自豪感,也产生了羞愧感。再如,村民们都给祖先修坟,但有人修得更巍峨雄伟。总而言之,就像沿规定路线赛跑,虽然是单调的,但还是可以比个快慢。这是一种推动力。假如没有外来因素造成的变化,可以预言在公元3000年,某村民在结婚时办拉伯雷《巨人传》里描绘过的那种宴会,另一位给自己死去的父亲修一座比纽约帝国大厦还高的墓碑――当然这种情况不会真的发生,那是因为外来的因素要起作用。
在中国,有一个地方最能体现大概率价值观的精神,那就是农村。为此,我提出了村落文化的概念(详见《论村落文化》一文)。在一个典型的村落当中,每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在每个细节上几乎都完全一致:婚姻该是什么样子,家庭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完全一致,所以就没有少数派:这甚至算不上是“大概率价值观”,简直是“全概率价值观”了。引人注目的是,大概率价值观发展到这种程度之后,反而不成其为价值观,而成了一种金科玉律:不是说婚姻是好的,而是根本不能想像自愿不婚;不是说生育是好的,而是根本就不能考虑自愿不生育。更少有人有“同性恋”之类的概念。在农村,个人意愿方面的信息是惊人的缺乏,人们所做的一切均缺少理性的思考。因此可以说,非理性的全概率价值观是大概率价值观的一个极限。
大概率价值观的另一个极限,存在于我的一些学术界同仁心目中。他们把世间所有的人当成一个,规划着大家的前途,却没考虑到人中间还会有例外。这种规划的理论基础也是大概率价值观,或许可以称为“理性的全概率价值观”。然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不可以由什么人简单地规划之。这些规划不管出于多么善良的动机,总是要把被规划的对象送到“非理性的全概率价值观”那里去。“乌托邦”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归宿。
“大概率价值观”的盛行必然会使所有的人趋于一致。就是在我们社会中那些不属于大概率人群的人们中间,也能感觉到它的向心力――在我调查过的同性恋者、独身者和离婚者当中,羡慕“大概率”人群的大有人在。大概率行为规范就像一个黑洞,要把周围的一切都吃下去,其中有一些肯定是它不该吃的。举例来说,在同性恋人群中,有很多人和异性结了婚,维持着一个家庭,过着两面人的生活,他们对妻子和同性伴?都不忠实。这就说明,有些东西大概率这个“黑洞”不但不该吃下去,而且是吃不下去的。同性恋这个小概率人群并不会因为大概率价值观对它的否定而改变自己,而只会因此而转入“地下”,同时继续坚持他们的小概率行为方式。
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已经是世界上最为一致的人群了。当然,它还可以更加一致:消除贫富差别,消除社会分工,甚至消除性别角色的差别,就像“文化大革命”里试图做过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我们可以设想它成功了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全中国每个人都拿一样的工资,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做一样的工作,每个男人都有妻子,每个家庭都生一个孩子。这样大家就都属于最大概率人群,大概率价值观于是取得全面胜利。假如我们以为大概率现象是美好的,大概率价值观是美好的,结果就会是这样。这是一个现代的“乌托邦”。
三、关于“后乌托邦社会”
与西方社会相比,我们的社会可以被视为一种“后乌托邦社会”,因为并不能将它简单地等同于欧洲的中世纪和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虽然同它们十分相像――在中国我们经历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时期,各种“乌托邦”式的社会设计层出不穷,反复试验(公共食堂、人民公社、五七干校、上山下乡运动等等)。在那个时期,我们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单调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社会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在研究一种文化时,总是从生活方式人手,而研究一种生活方式又总是从它的环境人手。如果我们考察人们在选择生活方式方面的意愿,有两种想法最为普遍,一种认为现有的生活方式对任何人都适用,不可能变革,人能够做的只是在这种生活方式内部取得成功。在中国农村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最多,他们被动地接受生活,像老辈子那样生活,积攒婚姻支付,结婚,渴望生育尽可能多的男孩子,这些就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件。另一种观点或许可以算做它的对立面,即认为现有的生活方式不理想,应该有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才是真正适用于任何人的。这样他们就开始构思“乌托邦”。举例言之,农民的生育行为是现在中国的一个大问题,每个人都想生一个儿子。这在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让他们做了之后,肯定会造成将来中国男多女少,造成严重的问题。我的一位朋友想出了这样的办法:用立法的手段,让每对夫妇都能生育一男一女,这样既解决了人口过剩的问题,而且每个男人都有老婆。这种构想假设某种生活方式会适用于每个人,因而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其实,这两种想法合在一起,并不构成一切可能性――只有把所有的人只能有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作为前提,它才算完备。我认为这个前提是十分可疑的。仅从婚姻家庭领域来说,每个人就不一定都要结婚;结婚后也不一定要生育;如果允许生两个孩子,也会有人坚持要两个儿子而不是一男一女,等等。
“乌托邦”这个词来自摩尔的同名作品,里面不但描写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还详细描写了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罗素对它有一个评价:在这样精心构想的社会里生活,一定是十分乏味的。参差多样是幸福的命脉。对罗素那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一个人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就被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是件可怕的事。但是看看农民的生活,虽然没有白纸黑字,但也没有什么变更的余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的生活方式就相当于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生活不像书上说的那么美好。我把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单调划一的社会叫做“后乌托邦社会”,把美好二字扣掉,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里。
任何“乌托邦”式的社会设计都有一个最致命的荒谬之处,即它假定所有的人所喜爱的是同一种东西,所向往的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人们的喜好和要求是很不一致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男女两性的喜好和要求就不尽相同。国外有不少女权主义理论家提出,妇女可以有并且应该有完全不同于男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就是说,妇女可以从自身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出发,构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不是简单地要求和男子平等,男人有的我们都要有。我看不出这种想法有何不能成立之处,唯一叫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早没人想出来。作为一个女性,我不得不承认,在人类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无数大智者,都是男的,没有一个替我们想到了这一点。而女权主义的思想家,无论从思辨的深刻和方法的严谨方面,或许都无法和第一流的思想家相比,却想到了这一点。这说明思维的能力不能够决定一切,还需要设身处地。
单单妇女,就有理由成为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主体,以此为基点去构造一切,就和“乌托邦”的思想方式正好相反。由此就产生了一个纯粹的伦理问题:人的生活,应该是由它的本体去创造呢,还是应该按照一种统一规定,由一个个的人去执行?我本人持前一种观点,所以仅对后一种观点提出质疑。
假设生活是一种规定,很显然,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性生活,什么时候结婚,生几个孩子就都已经被事先决定了。这样我在生活里就相当省心,不用再考虑这些问题。但是我的生活也就少了很多可以有的内容,比方说,由我自己决定要何种性生活,结不结婚等等。省心固是好事,我也就丧失了表现我有思考和做出抉择的能力的机会。须知正是因为有这些能力,人才成其为人。假设我有这些能力,但是始终被保存着,没有机会使用,那么和一只被饲养着供肉食之用的动物有何区别?有什么理由相信这种生活对我是好的呢?
其次,我想知道这种规定出于谁的手笔。假定它是出自摩尔爵士之手,我就有理由表示不平:凭什么他就规划了一切,而我连我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规划。假如它是一种传统,那么当它不适用时,当然可以变革。在变革时,我又不相信什么大智者会把什么都想到。黑格尔、罗素等等,谁都没有为女人设想过。不管怎么说,女人自己的事,女人最清楚。
当然,一种统一、单调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形成的,并且是出于大多数人的需要。但是有很多证据表明,有一些人不适合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人天生具有同性恋倾向,有人厌恶家庭生活,有人不想生育。这些人都感到了主流生活方式的重压。这些压力有些来自政策、规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还有一些则来自周围的人群――大概率人群和他们所持有的大概率价值观。
在我看来,现存的主流生活方式不仅是一种统计上的多数:
——假定如此,它就是个完全的自然现象,我们对它无话可说。
——事实上它包含了意志的成分,它意味着从众,循规,服从,压制个人。在历史上,这种现象更为绝对。这种力量主要作用于个人生活方面,但它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最起码它对形成特立独行的个人品质只会有坏的作用。我甚至怀疑它会造成整体性的愚蠢。在近代,我们国家没有出现柴科夫斯基、福柯、米开朗琪罗(以上同性恋者),没有出现笛卡尔、叔本华、尼采(以上独身者),没有出现萨特(与人同居而不结婚),没有罗素和萧伯纳(打了多半辈子光棍),也没有居里夫人、南丁格尔――这两位杰出妇女恐怕都不是贤妻良母。这与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恐怕不无关系。如果中国人仍旧不能摆脱这种以空前的整齐划一为其主要特征的“后乌托邦社会”,我们的社会就毫无希望。
四、归根结底是“个人”的意识尚未形成
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究竟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发展的因素决定的呢?这个问题又可作如下表达:中西方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究竟是纯粹的文化差异(它不会随着时间变化而轻易改变),还是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如农业社会阶段和工业社会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特征,随着农业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化,这种特征也会随之改变。
如果说它是文化因素决定的,那么无论社会环境发生何种变化,人们仍会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仍会在婚姻、生育、离婚、性行为这些事上(这些是我的研究领域,当然还有别的方面)保持“大多数”对“极少数”的不均匀分布。如果说它是由社会发展因素决定的,那么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就是某一社会发展阶段――具体说就是农业社会――所具有的特征,一旦中国的王业化、都市化、现代化程度提高,大概率价值观也会随之改变。
在上述两种观点中我倾向于相信后一种,即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大概率价值观是以中国文化为其形式以农业社会特征为其实质的一种阶段性现象。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这一切终将发生变化。
可以举出以下一些事实来证明上述论断: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城市人口(约占人口的20%)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的许多人们,已经不再迷恋于各种“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家庭、亲子关系、传宗接代、祖先崇拜等等),他们可以选择不结婚、不生育、同居、婚前性关系、同性恋之类的生活方式,而不至于招致太大的麻烦。形成这一事态的原因是:与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活不同,在大都市中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个人生活空间,一定的保守个人隐私的可能性。这是由于居住形式的改变(从邻里相互熟悉、亲属居住集中转变为独门独户),也由于人际关系类型的改变(从生活在全部或大部分都相互熟悉的人群当中转变为生活在大部分都相互陌生的人群当中)等等。这就是一个证据,证明即使在中国这样文化传统力量十分强大的社会中,如果生活环境尤其是人际关系类型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也会随之改变。
有关这一点的另一个证据是,中国农民明明知道按照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旦进城招工或上了大学,就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有一半的可能性不是男孩,这就是说,他们为此要冒相当大的家庭姓氏失传的危险;然而他们还是鼓励子女拼命考大学,招工进城。这就说明,家庭、传宗接代这类事情的价值并不是不可动摇的。一旦有了选择他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农民也不惜损害自己的家庭和子嗣,义无反顾。这里再举一个极端的事例,据报载,一模范女民办教师,因长年工作优异,得到“农转非”的机会,当她听说已婚子女不得随母“农转非”时,竟残忍地将儿媳、孙女杀害,以图达到使儿子能随她“农转非”的目的。这说明,为了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有些农民不惜毁灭家庭。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人们会说,各种各样的犯罪都会有的,它们都是特例,但是这一事件之所以意义深刻,并不在于犯罪本身――犯罪是非理性的行为――而在于隐藏在这一犯罪事实背后的理性选择一为了成为城里人,不惜毁坏已有的家庭。在选择的机会出现之时,许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原先赋予家庭的价值,而选择一种更好的生活。(当然,为此而杀人就是极端现象了。)由此可见,并没有什么价值观是不可以改变的,如果环境改变,或许是为了改变环境,人们可以放弃旧有的价值观念。
总之,大概率价值观只是一种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农业社会特征,它是农业社会无选择余地的生活环境的产物,是一种以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一旦得到选择的机会,人们则很可能不选择这种文化,而会按照自己的愿望作出多种多样的选择,比如说,独身,不生育,同性恋等等。
弗罗姆曾指出,在欧洲中世纪,“个人”的意识(概念)尚未形成。在我看来,大概率价值观的实质归根结底就在于个人意识尚未形成。正因为人们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有自主意识的个人,他们才能把不幸福的婚姻“凑合”下去,他们才会认为个人的快乐与幸福同家庭的稳定相比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他们也才能在个人的感受与家庭及婚姻的形式发生冲突之时,使个人的感受屈从于家庭和婚姻的完整形式,并且认为这样做并不困难。而对于一个个人意识业已形成的个人来说,这样做就要困难得多。
既然“大概率价值观”来源于个人意识的缺乏,既然欧洲人在中世纪也经历过个人意识缺乏的时期,那么“大概率价值观”的盛行就不是一个纯粹由文化因素决定的现象,而应当说是一个阶段性社会的产物,即农业社会的产物。可以预言,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人也会逐渐放弃这种“大概率价值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将会变得更加丰富,中国的社会气氛也将会变得更加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