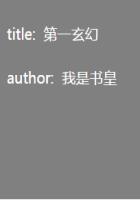她睡觉的姿势是孤独的蜷缩。相当寒冷的样子。他只有等她完全睡熟以后,才敢慢慢地靠近她,把她的手脚展开。然后她会发出小小的呻吟,钻入他的怀里。
这是她最无防备的时刻,眉眼舒展一如婴儿。他悄悄地将自己的手臂张开,身体调整成她最舒服的姿势,然后手指轻轻地搭上她的背。一整个夜晚,他都努力地保持着这样的姿势,虽然清晨醒来,觉得躯体僵硬如木偶,可是他的心里是一波一波如海浪扑打的喜悦。在一些工作的间隙,他突然抬起来头摸着眉毛笑,这样的感觉,是不是真的就叫幸福。
他们在一周后才开始做爱。他始终记得那一天的晚上。他因为临时有事加班,回到家里已经是九点半。推开门的时候,看到她怔怔地坐在客厅的桌子边,好半天才回神过来看他,程,对不起啊,我忘记了时间,我现在就去做饭。他走过去拉住她的手,白白,没有关系,我们下楼去吃饭,或者今天吃泡面。
然后他的眉毛拧起来,白白,你的手怎么这么冷。
三月的北京,暖气还残余最后的余温,天气亦有春来转暖的趋势。但是她的手,苍白冰冷地卧于他的掌心,轻轻地瑟缩。她抬起脸来看他,然后努力地笑,你可不可以抱我一下。我真的有一点冷。
是这样水到渠成的一件事。他曾经对着自己发誓,如果不是她的亲允,他绝对不会对她心生妄念。她是他要捧在手掌里呵护的女子,她和任何别的女孩子都不一样。他爱她,尊重她,生怕自己一个闪失她就如露水般消失。幸福是如此来之不易的事情,他曾经多么黯然地想,这幸福永远也不会来临。
可是她的手环上他的脖子,仿若使尽浑身力气攀附于他的身上,瘦弱的身躯贴近他,似乎要把自己揉进他温热的胸膛里面。然后她踮起脚,嘴唇颤抖着勇敢地印上他的脸。
他发现自己所有残存的自制在瞬间碎裂,而热情是忽忽窜上的火苗,自浑身四处熊熊烧起。未曾有任何犹豫,他将她整个抱起,然后踢开卧室的门。他终于能够叠上她赤裸的身躯。少女的细致柔腻的皮肤,在他炽热的手指间微微颤抖,像一匹素白微凉的绸缎,渐渐印染上他的体温和气息。他辗转亲吻她深刻如海峡的锁骨,然后深深呼吸,他终于进入她的时候,他听到她发出钝重的一声闷哼,然后指甲掐入他的手臂。他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不停地掉眼泪。他一边战栗着一边俯身下去亲吻她的嘴唇,他尝到泪水咸涩的滋味,却开始分不清到底是谁流下的。
六
那一天,他们正式同居。她是他渴慕已久的花朵,终于被他攀折下枝头。
他亲吻她,无限珍惜而宛转的,他说,白白,你是我的女朋友了。然后独自发出呵呵的傻笑。
生活对着他打开了顺遂如意的一扇门。正式工作半年之后,他居然以律助的身份拉到了一笔不小的业务。主任单独把他喊进办公室,然后自宽大的皮质转椅上走下来,满面含笑地拍拍他的肩膀。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会有前途。
中午的时候,他拿着提成奖金在街上兴冲冲地走,浑身似打通任督二脉,精力充沛而丝毫不觉劳累。他走了一个小时才走到一家商场,然后在首饰专柜停下来。
晚上他带着她出去吃饭。她还是素淡从容的样子,漆黑的头发散在面孔两边,穿一件白色印花的长T恤,罩了黑色的外套。眼睛抬起来,微笑沉静地看着他。
始终是他这样眷恋和向往的一张脸,面色苍白,但瞳孔黑如点漆,眼眶里面似终年氤氲着水气,光华流转。
他隔着桌面捉住她的手指,他说,白白,等你一毕业,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她轻声地笑,程,你现在最应该摆在心里的,是司法考试。
考试前的最后冲刺他加大了每日复习的时间她在网上为他找许多往年的试题或者成功者的心得,有时候他一边吃饭,她一边念给他听。一吃完饭,她就将他推去书桌旁,自己去厨房洗碗,然后收拾屋子。他只在一些背法规背到感觉大脑已经完全被塞满的时候,走出来,伸手自她的腰间绕过去,然后拥抱她,将头埋进她的头发里。
考试需要两天的时间,因为路途太远,他寄宿在同事家里。他给她打电话,她轻柔恬淡的声音自话筒传来,她说,程,你感觉怎么样。程,你要早点睡觉,晚上不要看书太晚。考试有不会做的题,也不要紧张,把他当成了一个小孩子,他呵呵地笑,白白,不用担心,一切都好,我一定可以考过。
他站在同事家的露台上,手机里电流滋滋作响,整个小区静谧无声,但是抬眼望去,可以看到远处闹市区的灯光闪烁他突然觉得心里温暖而潮湿,那些自一起初便开始洋溢的感觉,始终未曾消磨,像温柔而缓慢的潮水,他再次对着她轻声的开口,白白,我很想念你。
这一次,她未曾笑而不答。是漫长的沉静,他听到她呼吸的声音,然后她开口,她说,程,谢谢你四门考试结束的时候,他从考场里面走出来。沿路都是探讨考题、怨声载道的人,可是他只觉得自己归心似箭。
他按捺不住自己的亢奋,他想掏出手机来给她电话,但是他又停下手,他要回去给她一个惊喜。她现在在做什么,是在睡觉,在小区附近的市场买晚饭的菜,是趴在床上看小说,还是打开电脑在上网。
他的心在这样的揣测里焦灼而热烈。不管她在做什么,他都会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然后一把将她抱起来。她会发出低低的一声惊叫,然后回过身捶他的肩膀。
然后他要郑重地向她求婚,他们可以先订婚。几个月后等她毕业,他们就正式举行婚礼。他会给他在当地声名显赫的父亲打电话,他答应过要送他一套市区的房子做结婚礼物。他的境况已经好起来。过不了多久,他可以贷款买一部车子,她可以什么也不要做,只要每晚在家里亮一盏灯,告诉他回家的路。
他兴冲冲地打开家门,然后呼唤她的名字,他说,白白,我回来了。
七
可是没有任何人来回答他。从卧室到客厅再到厨房,他甚至跑去阳台细细搜寻,没有她。他用力压抑下心头逐渐窜上的恐惧,他想她只是出门买菜去了,或者她回学校有事情。他掏出手机来打她的电话,关机。他再次坐下来安慰自己,一定是真的有事情,所以不能接电话。
直至此刻他才发现他几乎不知道她任何的联系方式,他不知道她是什么系,不知道她住哪个宿舍,他甚至连她平常爱去哪里都不知道。他给她发短信,虽然知道关机的手机一样也接收不到消息,但是他还是一条一条地发,他说,白白,你早点回家。白白,我回来了,你在哪里,我去接你。
夜色像窗帘一样哗啦落下。他再次独自坐在黑暗里,惟有桌子上滴答的闹钟提醒他时光无情的飞逝。
最后的时候,他站起来笑,他想她真的是和任何别的女孩子不同。蓝住进来的时候,携带了自己大包小包的生活用品。走的时候,把一切都撤离得干净利落,包括她放在洗手间的毛巾。但是她,从未带来过自己的任何东西,除了一只背包,里头装了她的小说、手机和烟盒。她只需一背起包,就可以背走她的整个世界。
他的笑声凄凉而绝望,一声又一声,最后感觉自己面部的肌肉已经停顿下来,但是依然有他的笑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他想摸一根烟来抽,发现自己的手已经反复打不亮火机。他用力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他说,程,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摸到自己满脸的潮湿她真的消失掉了。像他们开始认识的时候,那个每日跳动的鲜红头像,毫无预兆地黯淡下去,然后成为一盏失明的灯,再也不会发出任何只字片语他拨电话给宋,同他说一些寒暄的话,说各自毕业后的生活,然后他轻描淡写地提起她他说她真是一个特别的女孩子,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然后宋就叹息,上次我们广州地区同乡会的时候还说起她,说她众目睽睽下被那家伙的女朋友扇了一记耳光后,整个人就变了。后来那家伙和他女朋友出国了,她还自己一个人暑假跑去他的家乡,也不知道她去找什么。估计还是没死心吧。听说今年三月,那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了,我们都觉得白白像失踪了一样,估计是受不了打击,一个人躲起来了。
挂掉电话的时候,他毫不迟疑地将烟头拧到自己的手臂上。那种瞬间扩散的焦黑和腐烂的气味,让他迅速地痉挛了一下,然后又恢复镇定。
一个丑陋的伤口。在许多细碎的疤痕中间,触目惊心。她做爱时候惟一投入的见证,是会将指甲掐入他手臂的皮肤里,他用自己的指腹一处一处的抚摩下去,然后缓慢地咀嚼她的名字,白白,我恨你。
心里有多痛,就有多恨。原来她七月的那次消失,是去了别人的家乡,找寻往日爱情的浮光掠影。
她一直没有忘记那个人吧,所以才会在听到他和她结婚的那个晚上,抱住他企求温暖。她和他在一起,为他做饭,和他上床,原来只不过是将他当成了一段替代。是她感觉恢复了吗?所以她毫不迟疑地,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他对她所有的爱,都成了她取暖时候的炭火。她在他身边停留,不是因为她爱他,只是因为她冷。
是的,她从来也没有爱过他。她从未对他说过一句,程,我爱你。她不曾把她的任何现实讯息告诉他,她未曾把自己的任何切实生活带进他的屋子。她要走的时候,连通知他一声都没有,她的到来和离开都如此轻易,并且预知了最后的结局只是他,他满心沉醉在渴慕许久的幸福里,毫不迟疑地扑入到幸福的幻象里,他甚至想得那么长、那么远,他要娶她啊,他想给她幸福安稳的生活,与她共同度过三五十年的岁月。他从身上摸出自己在商场里买下的对戒,然后用力地掷到对面的墙上去。那样一闪而过的璀璨光辉,然后跌落于沉黑的地面。像眼泪,像他满心欢喜的幸福生活,像他所有曾燃烧的信仰和梦想。
他多么多么地恨她。在他已经愿意对她交托余生的时候,她怎么可以,怎么可以,从未有一刻要真心地想在他身边停留。
八
他没有再去找她。没有再去追问她的宿舍或者家庭的电话。他已经习惯QQ上她静默灰黑的头像,一如他习惯很多半夜拨过去,那个永远关机的手机号码。
他还是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公车去上班,精力充沛地奔波在工作需要的各个岗位。他还是每天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公车下班,在楼下的饭馆吃晚饭,或者直接泡一碗面。
晚上的时候,他开着电脑写一些方案书或者项目表,偶尔阅读一些相关的材料书籍。然后睡觉。
一个多月后,司法考试的成绩公布,他一点也不意外自己高高地超过了分数线生活如此顺利衔接。仿若一切都未曾发生。他一个人上班下班的身影,是他的这部电影里惟一的剧情。他并没有任何抱怨,也早已经习惯那一些澎湃的爱和恨,都已经在时间里轻易地平静下来。他的心是已经打烊的旅馆,不再对任何外来的人开放。而余下每一天,他都会努力地打扫心里的房间,将那些不愿意碰及的记忆打包封存他在律所一开始做的,就是整理卷宗,他最擅长做此类的工作。他终于变成冷淡的一丝不苟的男人。
生活简单,事业渐入佳境。
可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是不愿意搬离学校附近的那处居所,就如同他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要在电脑上开着QQ,虽然他的好友里面空无一人,除了那个永恒的静止的名字。
季节的更迭似乎已经丧失意义,他是个尽忠职守的演员,有一张云淡风清的脸。从春天,就如此这般,一路又走到了夏天。
人间的六月天。大排档又已经四处摊开,马路上突然多出来许多的啤酒罐子。街道边的蔷薇花开了,校园里的别离又正是轰轰烈烈的好时候。
有一个小师弟去他所在的律所面试,回来后请他吃饭,说以后请师兄多关照。
他微微地笑,端起手里的大扎啤杯子,同他碰了一下。他还是习惯坐在面朝里的位置,他对一切路上来人都没有任何兴趣。他只是看着那些穿白褂子忙碌的师傅,有的在涮菜,有的在下面条,有的在收钱,夜里的风吹过来,有隐约的花朵的香气,生活本就是如此平淡庸碌的事情。
然后他再次听见自己对面的人招着手喊她的名字,白白。
在有一个瞬间,他的身体僵硬成了石块。然后他慢慢地转过身去。
他看到了她。时光的河流刷刷回溯,他的眼睛里面涨满了眼泪,像一年前的那个夏夜。她依然是一个人,穿黑色宽大的T恤,棉布裤子,斜背着挎包。她的刘海还是那样的长,挡住了她的半边面孔。
她抬起头来,朝这边点头。神情依然是淡然的。但是在看到他的下一秒,她怔怔地站立在原处,没有低下头,没有继续走。
他站起来,朝她走过去,一把扣住她的手腕,然后拉起她就走。
他的心脏突突跳动似要冲破耳膜,他紧紧地扣住她的手,用尽力气,以至自己的手掌都微微颤抖。他的大脑里面刮起了一场暴风雨,把他收拾好的房间吹得七零八落。
那些他刻意要遗忘的段落,都扑腾着从他加了锁的箱子里抖落。他不知道自己要把她带到哪里去,他拖着她只知道不停地往前走,路过那些饭馆,路过学校,路过店铺,路过街道上许许多多的人,路过那些回忆里泪落如雨痛不欲生的时刻,一直走到筋疲力尽,走到了一处陌生的十字路口。
他这才如梦初醒地放开她,她一直跟着他走,走了这么长的路,一句话也没有说。他举起她的手腕来看,已经有赫然的一圈青紫,他痛苦又内疚地看着她,他的措辞又开始支离破碎,白白,你疼不疼。对不起。我说好要恨你的,如果再见到你,一定要给你一个耳光。可是,对不起,你疼不疼。
然后他听到她的声音,程,我不疼。
他从未见她在他的面前哭过,但是她的眼泪大滴大滴地掉落,她伸出双手环上他的腰,她说,程,对不起。她说,程,我很想念你。
§§§尾声
如果我曾经沉迷在往事里只知埋头颠沛流离如果我曾经是迷路的孩子,走近你,又逃离如果当我终于懂得摒弃过往珍惜眼前的生活你还会不会,会不会站在原地等我如果我要用这么漫长的别离方可见证对你的思念如果我以为要决绝消失,才可以不沉沦,不贪恋如果我真的舍弃一切却始终舍弃不了对温暖的怀念你还会不会,会不会站在原地等我如果当我终于发现我爱你的时候如果当我回头……如果我终于愿意此后夜夜为你点亮一盏归家的灯火你还会不会,会不会站在原地等我请你,请你,站在原地,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