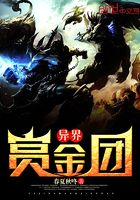鸠雅目睹国母被大将军家臣公孙豹揪住头发撞死在廊柱上,顿时吓得面色惨白,刚要喊叫,却被一只苍劲的手捂住了嘴巴,随即被人横抱起来,只听得来人低声说:“公子不要出声,随我来!”
鸠雅听出说话之人正是山伯。山伯当年随同鸠雅母亲一同入宫,自称是鸠雅母亲的家奴,自女主人死后,他便终日陪伴在鸠雅身边,寸步不离。此人一身朴素,平日里沉默寡言,左手生有骈指。鸠雅体弱多病,国后稷柱氏很是怜悯他,视为己出,为了方便照顾,就让鸠雅搬到凤仪宫住下。那山伯也就随着鸠雅搬了过来,住在宫门一侧的偏房里,他除了悉心照料鸠雅以外,最喜欢侍弄花草,将整个凤仪宫修整得如同花海一般,国后便笑称他为“六指神农”。
山伯刚抱起鸠雅,公孙豹已带人冲了进来,二话不说举刀就砍。山伯一侧身让过刀锋,抬脚把公孙豹踹飞出去。那公孙豹素来自恃武艺了得,不想却被一个看似庸常的老头轻而易举踢中,在空中原要扭腰翻起,竟使不出半分劲力,反而将后面的随从撞到。
山伯轻声对鸠雅说:“公子,捂紧口鼻。”随即手一扬,但见屋里弥漫着一片红色花粉。山伯趁机从窗里一跃而出。公孙豹爬起来,正要冲杀,不觉一阵迷糊,与一众随从瘫软在地。
鸠雅被山伯横抱在腰疾奔而出,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呼,随着山伯几个纵跃,忽高忽低,一面感到身体倦怠,一面又暗暗惊奇山伯竟深藏不露。转眼就来到一处殿堂之外,四周柏树森然,寂静无声,虽是白天,但没有人走动。鸠雅知道此处乃是祭祀堂,以前每逢十月中旬举行国族祭祀,他都要随着公父到此行礼。
山伯快步走入祭祀堂内,将鸠雅放下来,说:“公子稍候片刻。”就飞身到大梁之上。鸠雅调匀呼吸,在一片幽暗中看到迎面一尊真人般大小的黄金塑像。那塑像兽身人面,跨乘两龙,口含火珠,一脸肃杀,这就是夏州族始祖祝融。祝融身下是一排历代国主牌位,由于很少打扫擦拭,早已蒙上一层灰尘。
这时山伯从梁上下来,手里已多了一件黑布包裹住的物事,黑布上沾满蛛丝。鸠雅还来不及开口询问,山伯拉着他走出祭祀堂,关上殿门,抱起鸠雅跃上殿前的老柏树。这老柏树少说已有千年树龄,约有五六人合围,二十多米高,冠盖如云,分支犹如虬龙飞舞。山伯悄无声息地落在一株巨大的树枝上,屏住呼吸朝四下里张望,鸠雅也随着他的目光看出去,只见四周并无一人,偶尔还能听到凤仪宫那边传过来的纷沓之声。
片刻之后,山伯抱着鸠雅滑向主干。鸠雅这时才看清,原来这老柏树主干顶端早已被人削平,只因它四周分支太多太大,从下往上看,并不能看出这老柏树早已没了树尖。鸠雅猛然发现老柏树中心空空如也,有一道绳梯垂直而下,直通底部。鸠雅睁大眼睛,觉得惊奇无比,再想到这必然是山伯所为,更觉得不可思议,同时忽然间好像与山伯陌生起来,这个整日陪伴在自己身边沉默寡言的人,似乎隐进了一片云雾之中,浑身充满了迷雾。
“公子,快下去吧。”山伯探身扶住绳梯,让鸠雅拽着自己的手臂慢慢滑到绳梯上。鸠雅稳住身子,一步一步地往下,起初还能看到光亮,大概往下七八米以后,四周就一片漆黑,幸而鼻子里闻到一股柏树的清香,再抬头还能看到山伯的身影,也就鼓足勇气直下底端。不一会儿山伯也下来了,他点亮一只火折,周遭立时明亮起来。
两个人站在树洞里,顿显逼仄,只能侧着身。山伯将火折递给鸠雅,在树身上一拍,前方顿时开了一道暗门,山伯便拉着鸠雅弯着身子走了进去。借助火光,鸠雅看到眼前是一道曲曲折折狭窄灰暗的地道,仅可容身,不知通往何处。他们一老一少前后紧随,在这地道里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去。
大概走了一百多米,前面豁然开朗,虽然还没有到达地面,但这儿的通道却有三米多宽,墙壁上乱石丛生,不似先前墙面平整,还有水滴落在头上,空气也变得潮湿了——这原来是一个天然的山洞。道路变得宽阔,走起来分外轻松,不像刚才弯腰弓背,可山伯丝毫没有停留,仍带着鸠雅不紧不慢往前走。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鸠雅有些支持不住,正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却见山伯忽然停住脚步,前方隐隐已有一线天光。山伯停了下来,找了一块岩石坐下,说:“天色尚早,我们还得再等等。先吃点东西吧。”说着从怀里拿出一株紫色药草,让鸠雅含在口里。鸠雅顿觉口齿生津,周身疲劳为之一扫。
鸠雅这时才明白,这密道原来是利用了天然洞穴,想想也是,倘若依靠人力,不知得动用多少奴隶,得耗费多少时日。以种种情形揣度下来,这密道完全是山伯一人所为,但单是掏空老柏树,再挖出一百多米的暗道将两处连通,想必也费了不少功夫吧。
鸠雅靠在洞壁上,裹紧雪狼皮缝制而成的大衣,仍感到冰冷刺骨。从八岁起,鸠雅总是畏惧风寒,就算在夏天,也常常穿一身厚重衣服,对于他来说,阳光不曾有过片刻的温暖。趁着山伯休息的时刻,他终于说出了心中的疑惑:“山伯,他们为什么要杀国后?难道连我也要杀了?这是为了什么?”
“恐怕宫中出了变故了吧。”
“什么变故?”
“政变!”
“那我公父呢?他虽然病着,但谁敢如此胆大妄为?”
“大将军鸠鸢!”
山伯总是如此,说话简短,似乎对于他来说,运用舌头是件极不情愿的事情。鸠雅早已经习惯了,但他还是被山伯的话震惊住了:鸠鸢,那个曾教自己射箭的公伯,竟然背叛了父亲,还派人杀死了国后。一想到国后,鸠雅立时泪如雨下,他想到端庄慈爱的国后曾给自己多少疼爱啊,而她死时又多么惨不忍睹,脑浆四溅血肉模糊。鸠雅忽然感到更冷了,冷得仿佛骨髓都在寸寸冻裂。
鸠雅嚎啕大哭,内脏犹如针扎。
山伯慌忙捂住鸠雅的嘴,说:“公子,小心招引来人!”他任凭鸠雅在自己怀里挣扎扭动,生有骈指的左手轻抚鸠雅后背,叹着气,眼泪却顺着脸上的皱纹滑落下来。
鸠雅半晌才镇静下来,又问:“山伯,你为何修这密道?”
“为了救你母亲!”
鸠雅更是不解,刚要张口,却见山伯抬头往前看,洞口已经看不到天光,夜幕降临了。山伯扶起鸠雅,说:“公子随我走,一定要寸步不离,懂吗?”鸠雅点点头。快走到洞口时,山伯熄灭了火折,两人轻声摸索着往前。不多时,便能够听到山风呼啸,两人已出了洞穴。
星沉云暗,四下里一片漆黑,只能模糊看到前方有一座岩石胡乱搭成的哨台,有两个守夜的兵士站立着,显得漫不经心。山伯往前匍匐过去,快接近哨台时,手一扬,那两个兵士就倒了下去。又静静地等了一会儿,山伯立起身,招呼鸠雅往哨台走去。
鸠雅来到哨台,看到两个兵士只是昏迷了,想必是中了山伯的花粉迷毒。他这时才知道,原来他们已经到了后山,祝融城淹没在前面的山峦之中,后面是洵山绝顶,鸟兽绝迹,人更是无法攀登。西边是一处百丈峭壁,只有沿着山脉往东,有一条羊肠小道直达黑水河,河边却是有一座营寨牢牢守住港口。因而这一处哨台虽是小心起见而设立的,但绝不会遭遇敌军,守卫既少,又不像别处需要费心费力。
看来只有往东去,从港口渡船离开祝融城了。两人在夜色掩护下,小心行到黑水河边,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找到一条渔船,山伯拿出十两白银,终于说动那渔夫渡他们过河。这一夜虽说天气阴沉,晦暗无光,但河面也算得风平浪静,渔夫在山伯催促下,不多时就划出四五里,眼看就要到达对岸,却不想从上游飞速驶来一条战船,船后还远远跟着几只小舟。
战船上一众兵卒,披坚执锐,手举火把,将河面照得通明。这战船速度极快,往前一插,便挡住了渔船的去路,那几条小舟也围了过来。战船上站着一男一女,男的也是一身甲衣,竟是鸠鸢之子鸠桓;女的紧身劲装,头发高高束起,却是国师瞿父的幼女瞿莹,约莫十五岁,自幼喜欢练武骑射,长相秀丽却好作男儿打扮,倒有些英姿飒爽。
鸠桓朗声说道:“我听得探子来报,有一只渔船不顾戒严令夜晚渡江,便率兵追来,不想在此得遇公子鸠雅。鸠雅,你体弱多病,不在宫中修养,为何半夜来受这江上冷风?快随我回宫去吧,国主……”
话未说完,只听得瞿莹插话道:“鸠雅哥哥,你这一下午从宫中消失,吃了不少苦吧?你不要再逃了,我去求求新国主和爹爹,让他们不要为难你。快上船来,跟我们回去吧!”
“莹妹妹,他们,他们杀了国母……我公父呢?”鸠雅听到瞿莹提到新国主,早已猜到公父必然是凶多吉少,只是还不愿承认,声音却哽咽住了。
“国主死……驾崩了……”
鸠雅立身不稳,差点跌落入水,山伯从后面一把托住了他。
这时,一个满脸络腮胡子,额头前凸的男子上前对鸠桓说道:“公子,国主可是严令杀了这前朝余孽。”他不等鸠桓答话,一挥手,身后的兵卒便弯弓搭箭,对准了渔船。山伯立马将鸠雅挡在身后,那渔夫吓得趴在船上直哆嗦。
“且慢!桓哥哥,那可是鸠雅啊!”瞿莹转身面对利箭,急切地说,“桓哥哥,我们几人一同长大,亲如兄妹,你忍心杀害鸠雅吗?”言语间已是珠泪滚滚,忽而挺起胸坚定地说:“如果你真要这么做,先让这箭从我胸膛里穿过去吧!”
鸠桓正自踌躇。那男子却道:“既然公子不愿动手,那就让我来吧!”原来此人乃是长右门外门弟子楼金逑,因偷学内门武功,被逐出山门。近日才入了鸠鸢帐下,一心想在这改朝换代之际崭露头角一显身手,好确保来日荣华富贵,因而立功心切,一时也不管是否冲撞了少主人鸠桓,当下飞身而起,只扑渔船而来。此刻便有四五个与楼金逑怀有同样心思的家臣也纷纷亮出兵器,紧随其后。
山伯纵使武艺了得,然而双拳难敌四手,加之渔船狭窄,又要腾出手保护鸠雅,难以腾挪,一时间便被伤了几处,只能护着鸠雅往船尾退去。眼看就要死在乱刀之中,忽然风声大作,江浪滚滚而起,双方一时站立不稳,摇摇晃晃,暂时停手。
山伯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连连挥出团团花粉,一跺脚,将渔船生生从中间震裂,霎时将敌人隔开,自己与鸠雅站在这边断船上。可江涛汹涌,船又断裂,立时就倾倒下去,那渔夫早就被江水卷走了。山伯看到鸠雅脚下趑趄,伸手去扶,不想胸口却中了一刀,回手将来人打落水里,还没有回过神来,那楼金逑已越过头顶,一掌打在鸠雅胸前,鸠雅便跌落江里,霎时被江浪席卷而去。
原来江风太大,山伯的花粉被早早吹散,效用不大,楼金逑内力深厚,并没有像公孙豹一迷就倒。但山伯的花粉毕竟奇特猛烈,楼金逑用尽全力,此时身在空中,直觉头晕目眩,来不及收势,也一并落入江里。
山伯顾不上那么多,一掌震碎船身,抱起一块较大的木板,便朝着鸠雅被江水卷走的方向奋力游去,片刻间也不见了人影。
此时风急浪涌,天昏地暗,只听得瞿莹跪在甲板上一声又一声地呼喊:“鸠雅!鸠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