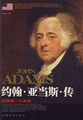看曝尸的人们传说,这个被曝尸的女人,看模样没有死,不管怎么看都有一股活生生的气脉。看过的人们都说:死的是郭松龄两口子,活的是魏三娘。这一下子就传扬开,说有个会动眼珠的活尸。四处一传扬,小河沿更加热闹起来了。人们从早到晚围着看,沈阳城周围百八十里的农村的乡下人都坐车、骑马、步行来看了。看的人都连连点头,觉得这也不过是两条腿的死人,看郭松龄两口子的模样活着的时候并不面恶,现在龇牙咧嘴,是中了枪弹。也有些细心妇女,先从魏三娘头发上发些议论,说她头发是乌黑乌黑的,看来这个女人活着的时候满利索,她最近还剪了发,不然长发会遮挡住漂亮脸宠的。这个女人埋在土里还会活。当然也有人说:她是风流人物嘛!留着长发到阴朝地府有个转轮,绕到轮子齿上就不好脱生了。来世脱驴变马谁知道。不过也有人说,凭这几个“妖人”,闹得从山海关到奉天城天翻地覆,差一点把张大元帅王八打把式——赶挪出窝子。这些议论是出口天官赐福,闭口就骂男盗女娼。
大帅府从早晨就象拜大寿一样,文武百官象用线穿着,不断头地转游。鞭炮不住声地响,大红喜帖子成双成对地往正堂里送。庆功大宴从早晨到黄昏也没有停过。
天近黄昏,大帅府的宴会正到高潮。张作霖大元帅要亲自出来主持几桌主宴席,招待奉为上坐的有功之臣。座位上蒙着红呢子,由会客厅到宴会厅,都铺着朱红地毯。天棚和墙壁上彩花灯通明,但大元帅的脾气是喜欢古色古香的。十个头的烫金大蜡不能不点,檀香不能不烧,宫灯、纱灯不能不点,走马灯不能不转,这样既有现代的文明气味,也有古色古香的气氛。
张大元帅身着藏青绸的团龙皮袍子,对团花的青龙对襟马褂,卷出一圈白袖头儿。头戴四喜貂皮帽子,脚上穿着薄底浅帮缎鞋,这种打扮看着潇洒利索,大有一尘不染之态。他走在前边,却一个劲儿回身,抱双拳,连声寒喧:“大哥,老弟,请入座!请!请!”不时把身子低低地扫一躬。
“大元帅请!大哥请!老弟请!”
应声而出的有张作相,吴大舌头、杨宇霆、王永江、莫德惠、汤玉麟、袁金铠等等,高矮胖瘦各人摆个姿势走出来了。
当走到上座时,张作霖突然煞住了脚步,往红地毯旁一抽身.拱起双手说:“吴大哥,您请入主座!”他霎时间脸上暗淡得失去神彩了。大家顿时止住脚步,一阵惊慌,有些人神经失控了,手里托着的军帽掉在地上用脚踩着。双手捂住嘴巴,翻着白眼,要哭又哭不出声来。吴大舌头连连摆手往后直退身子,说:“咬(老)弟,你洪五(福)齐天。大锅(哥)猪(吾)哪里担当得体(起)!咬(老)弟请!”他退身想躲开张作霖的一揖到地的架子,一下子撞在张作相的大肚皮上。张作相微微一躲闪(躲快了怕吴大舌头摔倒),可皮鞋后跟踩在汤玉麟穿着的布鞋的脚趾头上了。
汤玉麟连声说:“抬脚!抬脚!”
“抬脚!抬脚!”这一句话救了驾,大家一阵风齐声喊着:“抬着我们的张大帅入座!抬呀!抬起来!”
就这样一阵招呼和热闹,张作霖被张作相等人捧上了首席座位。
张作霖坐在红呢子宝座上,摘掉四喜貂皮帽子放在大案子上,还用袖子不住地拭泪说:“多蒙老友们抬举,作霖实在不才。郭鬼子已经天诛,本人胸口已经出了口恶气。”说完环视一周,然后用低沉的语气说,“今天这个会虽然还是由我主持,可我是出来向大家作交代的。”他望着袁金铠说。“四哥,你把通电先宣布一下,明天就发表!”
袁金铠高声朗读了通电,大意是:“张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今后将东北行政交王公岷源(王永江),军事交吴公兴权(吴俊升),请中央另派贤能来主持东北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
还没等袁金铠念完,吴大舌头站起身来,摇手摇头地说。“唔……唔……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唔……咱哥俩一块撂下担子。”
王永江也连忙站起来说:“永江代理一省政务,也不称职,惟宥大帅在,我得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现吴督军不肯负责军事,我又不胜任政治,东北大局实不堪设想,倘有不测,招致内忧外患,大帅有负国家人民倚托之重。”
杨宇霆也站起来说:“苏皖挫败,以致牵动金局,招致叛变,我是罪魁祸首,理应明正军法,但蒙大帅宽容,准许戴罪立功,这完全是从大局着眼。现在李芳辰(李景林)已退出天津,冯玉祥指挥军东下,我们应赶快收编郭军残部,封锁辽西要塞,然后派劲旅,策应直鲁联军击败冯军,占领京津,以安北方大局。在这种危急存亡之际,决不是大帅引退休养之时。非大帅无他人能安邦立国。”
还有许多人发言,有的说这次事变仅一个月就平定了,全仰仗大帅洪福……
张作霖站起来用手往下一压,让发言人坐下。他说:“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支架起来干!行,将来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让贤。”这时张作霖脸色遽变,眼光四顾问道:“常荫槐来没来?”
常荫槐从后边角落里站起来说:“大帅,我在这里。”
张作霖忽然大声地喊道:“你是军政执法处长,我命令你坐专车去把张学良给我抓回来,我自己枪毙他。你要让他逃跑了,拿你的脑袋来!”
这时,张学良就在小客厅里坐着,他老子的话是句句听得很清楚的,不用坐专车,拉开门就抓住他了。
常荫槐转身刚要走,吴大舌头站起身来摆摆手说:“唔……常处长,你慢走,我有话说。”
张作霖怒冲冲地对吴大舌头说:“你有什么说的?”
吴大舌头说:“唔……过去没有张军长(张学良)还将就,眼下没有他一天也不行……”
张作霖把脚使劲一跺,全场震动,大声说:“你胡说!”
吴大舌头连忙说:“唔……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两万人马在山海关,若和冯玉祥一合股,比郭鬼子力量大几倍,打过来,奉天就顶不住,唔……收编郭军,谁也办不到,唔……我不敢去,大帅也不行,非张军长不行!他一摆手,那些人就都回来!张军长再往前一挺,天津、北京就落在咱们手里,那时候我才敢保你上北京。”
这时张作相也站起来发言,张作霖又大喊一声:“你们住口,我姓张的用人,向来是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并不是我自己养出来的都是好的。小六子这个损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什么他妈的讲武堂、教导队、大学校,花了几百万块现大洋,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地装他妈的了不起。这帮杂种算狗屁!‘天下好’(王永清当土匪时的诨号)带一个骑兵团就把这帮兔崽子打得懵头转向。郭鬼子、小六子瞧不起吉、黑两省的军队,瞧不起于兰波(于芷山)。我的天下就是这些人打出来的。我姓张的用人向来一秉大公,李景林,张启坤、许兰洲这些人都是外来的,和我素无瓜葛,还有于孝侯(于学忠)是佩孚的外甥,谁不知道和曹、吴对头多年,可是我对他外甥是重用的。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奉天来扛个行李卷儿,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激得把他妈给我当老婆他都愿意。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平辈。郭鬼子手下的马得标和他那个一会儿猫一会儿狗的老婆魏三娘,都不是好货。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叫他学李世民,清君侧。我要不亲自毙了小六子,对不起在座的诸位……常荫槐!你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先毙你!”
这时杨宇霆站起来说:“请大帅息怒,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的对,为大局计,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得授给他统帅全军的大权,扭转大局,非张军长不可。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归他一个人。”
在座的都站起身来齐声说:“请大帅息怒!我们都有责任。”
张作霖坐下呼呼生气,人们看见他的眼珠稳定了,便知道他肚子里让贤和要说的话倒空了,再有气是假装的了。
有人张罗上菜,斟酒,大家为张作霖敬酒,张作霖这才举杯过顶向在座的人敬酒。大家一饮而干。大帅常说,酒这玩艺儿不是尿水子,接着连干数杯,有人脸上就挂着酒气了。
这工夫,有人扯长声喊:“张学良军长到!”全场肃静一下,接着大家使劲鼓掌,吴大舌头喊:“要张军长给大帅和我们敬酒!”
张作霖一拂袖子,伸手去摸茶碗子。
张学良身着军装,几颗特大的闪光的勋章挂在胸前。他看见大帅拂下袖子,他赶忙站起身来,一手擎着酒杯,走上主桌去给吴大舌头、张作相敬酒。这两个人连忙站起身谢酒。
张作霖把手中的茶碗飞出去.打在墙上,摔了个稀粉碎,恶狠狠地训斥道:“都是你交的好朋友!如果不是老兄弟们出力帮助,咱们父子俩哪有葬身之地!”气得浑身直劲打哆嗦。
张作相赶忙站起身来说:“大帅,你这就多怪了!树隔皮看不透,人隔肚皮闻不臭。何怪老把侄呢!他这次辽河一战,千古奇绝呀!功高于过!来,来,我们老哥几个敬学良一杯酒!”
全席的人都站起身来。张学良在人群中穿梭敬酒,先给大帅敬了酒。他没有给杨宇霆敬酒,也没有喝杨宇霆杯中酒。
吴大舌头接着说:“成(贤)汁(侄),是青猪(出)鱼(于)蓝,乘(胜)鱼(于)蓝。是猪(吾)辈继承人!来,来,干陪(杯)!”他把酒杯举过头顶了。
正在酒杯丁当响之际,忽然有人来报:“启禀大帅!有密信一箱送上!”
杨宇霆两眼扫视着酒席上不少得意之辈,他奸诈地从桌子旁走出来,眼角眨着,脖子都有些颤抖了。他对参谋一摆手,叫禀告的人员抬进一个红牛皮箱,重重地放在大厅绿色地毯上,在灯光照耀下,简直象一滩鲜血。
张作霖放下酒杯,瞪起被酒泡得血红的眼睛,不太明白地往身边看着,觉得大有名堂,不由得屁股离开了坐位,把身子探了出去。但他觉得这时不要亲自去过问,透过清水会看见碗底的,两只手按在桌子边上。
杨宇霆偏偏不把问题说明白,却用两只眼睛在身边不少“文武百官”脸上转,好象对这些人说:有你,有他,谁也逃不出去!都攥在我手心里了。他此刻明白,刚烧起来的火,让风吹吹才会烧旺,刚磨出的尖刀子,在寒风中吹吹刺人才痛。他迈着缓缓的步子来到张作霖面前,声音不大不小地说:“大帅,这箱中皆是从郭鬼子那里搜得的城内人私通他的密件!请大帅处理!”他说完紧着几步走到牛皮箱跟前,伸手拧开锁,揭开箱子盖,探手抓出一手信来,往大帅眼前晃动,这一下子把在座的不少“文武百官”弄得惊慌起来,又象一阵风,吹得在场的人们“举座惊慌”了。因为有不少人,认为郭松龄打过锦州这东北就垂手可得了,在此期间他们给郭松龄写信,或献计献策,或在信中声讨独夫张作霖,甚至说不绞死张作霖不解心头之恨。尤其在张作霖自已也稳不住阵脚时,奉天城人心惶惶,张作霖的亲信大多跑到日本人经营的旅馆里。张作霖在这种情况下曾让王永江召集省城各界名流,对这些人讲,大帅说,郭松龄倒他的戈好象演戏一样,郭松龄嫌我唱得不好听,让他上台来唱几出。我们在台下去听听,左右是一家人,何苦兵戎相见,你们可以备专车去迎接郭松龄,我张作霖可以正式移交……
事隔两天,传出张家父子要浴血抵抗了。传说,张作霖在南门里张瞎子那里算了一命,说张作霖是大命之人,郭松龄灭不了他……其实张作霖求的不是瞎子,而是彭汉贞子,不是算命,是求日本保命。
宴会一开始,张作霖还亲自给南门里张瞎子敬酒来着。杨宇霆暗中差人献出郭松龄的“牛皮箱”,这也是他清君侧的一计了。
张作霖酒是喝多了几盅,可他心里暗想:这个小诸葛又对他扇小扇子,是扇的哪股风?于是拍下桌子问道:“邻葛,你看过这些信了吗?”他问得声音很大。
张作霖这一问,真是吓得给郭松龄写过密信的人胆颤魂飞。
杨宇霆被张作霖这么一问,也语塞得像热馒头堵嘴,半晌没言语。他心里明白,这些信他看过,可他此刻说看过,那张作霖对他就大为不满,因为张作霖平日有戒,内情必须他亲自过目,不准外人先他处理。他吞吞吐吐地说:“大帅,我没看过!但这些信……”
“叭!”张作霖使劲拍一下桌子。这工夫他心里在拿主意。他一偏脸见儿子学良突然从桌上火锅里,用铁筷子夹起一根炭火,很明显地对他摇晃了一下。
张学良看如周围的情况,夹个火炭是示意大帅压压火。
张作霖忽然哈哈大笑,真是笑得人们毛骨悚然。他摆着手说:“郭既死,事已了,其余一概不究,快把这些谁也没看过的信拿去烧了,尽管多吃多喝,以后也不要讨论这些败兴的事。”他这是收买人心,稳定政局。
张学良万没料到老子看了他的压压火的暗号,却想出这么一个高招。于是使劲地为大帅的权术鼓掌。他带动得全宴会厅里的人们都热烈鼓起掌来。此刻张家爷们这股火烧在一个窑里了。
秘书长走过来问:“大帅,在哪里烧?”
张作霖大声说:“在看得见火光的地方烧。连牛皮箱都他妈拉巴子给我烧了。”
大家看着窗外的火光义喝起酒来。正酣饮之际,忽然有人高声报:“彭三爷到!”
在席位的人们都停下手中酒杯,这时才发觉,今天的盛宴彭三爷这位上宾却来迟了。
张作霖脸色阴了一下,但心头一转念,也许这个糟老头子给他带来洪福,没有当仞,哪有今天呢!于是摆下手说:“请!”
“请——彭——三——爷——!”
稍停。只见彭三蝎子拄着手杖从正门走进来。在他身后跟着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搀扶着一个从头顶到身上蒙着块大红布的人(这是何人?只能看见两只脚走路)。黑红相衬倒也很有生色。大家不明白这又是何典故,都面面相觑,屏住了声息看着动静。
张作霖也不由得手捋胡子尖,不明白这老头子的葫芦里装的是啥药,又耍的是啥鬼把戏。
彭三蝎子当众伸出干枯的双手抱拳说:“我是来给大帅贺喜!平定妖邪郭鬼子!定会长寿百岁!”他又对大家一抱拳,作了个罗圈揖。
这时蒙着红布的人,被推到地当中,彭三蝎子举起手杖连往那人身上击三下(很轻)说:“跪下,孽子!”只听扑通一声,那人双膝跪下了。
彭三蝎子伸手揭开蒙着的红布。大家这才看清楚了,原来跪下这人是彭汉臣,身罩孝服,腰间系着麻绳,手里捧着个木牌位。上边写着:
姜登选大人之神位
在场的人们几乎全都站起身来。在这红堂堂的大喜大庆的日子里,张大元帅坐在大红椅子上,象登极坐金銮殿一样,突然来了个吊孝的,这不赶上娶媳妇遇见抬棺材的一样了吗?这不但败兴,而且也太丧气了。
张作霖在座位上几乎气暴炸了肺叶子。
可是彭三蝎子却纹丝不乱地说:“借这大庆功的日子,借大元帅的洪天大福,把我家彭汉臣这个畜生,押来交大帅惩治。他在郭鬼子逼迫下,动枪毙了姜登选督办,而姜公是雨亭的忠良。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雨亭怎能忘了忠良!我彭家在雨亭檐下,出此丑类,我着实心疼。我来向雨亭认罪,一者请你处罚这个畜生,二者我彭家想完成雨亭之心愿,愿为姜登选公修祠堂。我已将地点买妥,在风雨坛修建姜公祠。敬请在座诸公教诲。”他这番话是彭汉臣教了三天两宿,才说得这么完满。
在座的人都看张作霖的脸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