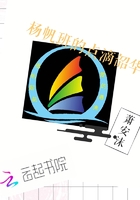孟梓清已经在自己的房中转了一整个上午,他紧闭屋门,不让任何人靠近,而他的视线,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桌子上的那封信。三天前,有人将这封信悄无声息地放进了他的书房中,信中只有寥寥几个字。
一别数年,故人安否?
这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句话,却在加上落款之后,变得尤其的刺眼。
锦绣。
这虽说不是一个太过寻常的名字,可也实在看不出什么特殊。但是孟梓清知道,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锦绣是一个从小便在他身边随侍的宫女,一个已经死了七年的宫女。
一个他亲手灌下剧毒投进井里的死不瞑目的宫女。
可如今,这个早已尸骨无存的女人竟然在他的书房中留下了一封信。孟梓清当然不相信什么鬼神作祟冤魂索命,他派人去打探锦绣是否还有亲人在世,传回来的消息便是,锦绣有一个妹妹尚在人间,在她无故断了消息之后难以生活,便卖身进了青楼,如今还做了头牌。好巧不巧,这个风头正劲的女子正是他的亲弟弟孟梓铭日日肖想的清风楼清倌,月见。
孟梓清只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他不相信月见接近孟梓铭只是巧合,不过他也不怕月见会对孟梓铭不利,左右不是对自己下手,亲弟弟又如何?天家的兄弟情,能有几分是真的?他已经能肯定书信就是月见送来的,他现在焦虑的是,月见的接近,到底是为弄清锦绣失踪的原因,还是她已经知道了锦绣为何而死,怀揣着报复之心而来?虽然不想承认,但是桌上的书信就那么明确的昭示着,月见替她的姐姐,来问候这个曾经的主子了。
孟梓清皱着眉头,心中烦乱不已。这件事绝不能翻出来,因为这件事背后掩藏的,是他这副道貌岸然的外表下,最肮脏的一颗心。
元帝十二年冬,皇后旧疾复发,终日精神不济缠绵病榻,孟彦卿感念皇后结发之情和多年陪伴,决定在孟梓铭十四岁生辰之日大摆筵席,算是为皇后冲喜。孟彦卿未登基之前常驻军营之中,生活一向朴素惯了,就连过年的时候宫中都不曾大宴群臣,这一次摆了如此大的场面,孟梓铭自然喜上眉梢。皇后也难得恢复了些精力,吩咐宫人们事事都上心些,还让人做了几件新的冠冕和衣服给孟梓铭,孟梓铭特意拿了其中一套送去给他的大哥孟梓清,觉得两人是亲生的兄弟,荣光自然也要一同分享。只是沉浸在喜悦中的他并没有看见,孟梓清眼中那一闪而过的愤恨。
彼时的孟梓清已经十六岁了,当年他父皇登基时经历的叛乱,几乎日日都投影在他的梦中挥之不去,所以他老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权势利益人人争抢,那是因为只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才能事事随自己的心意,只有将别人踩在脚下,才不会有朝不保夕的担惊受怕。他是皇后所出,是孟彦卿的嫡长子,原本理所应当的太子之位,却在等了十六年之后仍等不到他的父皇松口,更让他惶恐的是,明明是一母同胞,可是母后却明显偏袒着孟梓铭。如今为孟梓铭办的生辰宴,说的是为母后冲喜,可谁知道他的父皇心中想的是不是借此机会将孟梓铭置于人前,让他来结交群臣呢?
烦心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掠过心头,孟梓清只觉得身上的新衣服好似一把枷锁,插满了带着孟梓铭施舍的淬了毒的匕首。他看着与自己并肩同行兴高采烈的孟梓铭,心中的愤怒和嫉妒像疯了一般不断滋生,终于在行至文熙湖的时候假装绊倒,狠狠地将孟梓铭撞入了湖中。
宫中的宫人尽数被遣去招待宾客了,待找到人将孟梓铭从湖中拖上岸,他早已经面色苍白昏迷不醒。皇帝大怒,孟梓清长跪在孟彦卿跟前,自责自己没有照顾好弟弟,孟梓铭高烧三日不退,他便在孟梓铭的床前衣不解带滴水未进地跪了整整三天,孟梓铭转醒之后,他也体力不支晕了过去。孟彦卿见他如此也不忍再苛责于他,便相信此事不过是一次意外,过去就算了。只是自那之后,孟梓铭的身子遗留了寒症,每年冬天都会复发,每次都像剜骨削肉一般难捱。皇后知道了小儿子身体已损心中大恸,本来就孱弱的身子经不住这样的打击,在苦撑了一月之后将一口心血呕出,再也没有醒来。
于是,孟梓铭伤身之后再经历母后薨逝,性情大变,自此成了一个只顾寻欢作乐不学无术的废物。孟梓清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成为母后的催命符,实在的悲痛了一场,只是这悲痛没维持几日,便被失掉了一个夺嫡对手的沾沾自喜冲淡了。欢喜过后,孟梓清猛然想起来,那日孟梓铭落水时,他宫中的侍女锦绣几乎是眨眼间就到了跟前。锦绣原本是来送他忘记戴的玉佩,那么她究竟看没看见自己并没有绊倒而是直接撞向了孟梓铭?这件事绝不可让他人知晓,孟梓清思虑再三,为了不留下一点风险,便在一个深夜,亲手给锦绣灌下了鸩酒,而后将尸体投入了废井之中。
从往事中回过神来,孟梓清将那封信抓进手中揉碎。事情已经过了七年,孟梓铭如今一心帮着他对付孟梓琦,只为了日后能做个闲散王爷潇洒度日,可偏偏有人将这事再揪了出来。
孟梓清慢慢握紧了拳头。
此事若是被翻出来,那后果,远不止身败名裂那么简单。
孟梓铭将月见送回去之后,满面春风地去了孟梓清的宫中。他没有让人通报,进门后先自顾自倒了杯茶喝,半天没听见孟梓清出声,转头一看,才发现他的大皇兄正一脸阴郁地看着他。他收敛起脸上的得意,气愤地说:
“算老六这次运气好,竟然勾搭上了那昱国的小公主,保他勉强躲过了这一次。皇兄且消消气,来日方长,咱们慢慢地整治他!”
说完,小心的打量着孟梓清的表情。孟梓清紧盯着他看了一会,看的孟梓铭后背直冒冷汗,才缓缓开口。
“听说,你和那清风楼的月见走得很近?”
孟梓铭以为孟梓清这么严肃是有什么大事,没想到只是要问月见。他松了口气,语带轻松地说:
“不错,我早先就看上她了,还打算明天就将她赎出来,接到我外头的园子去。皇兄你可要替我保密啊,可不能让我宫里那个妒妇知道了。”
“不行!”
孟梓清一拍桌子,吓了孟梓铭一跳。
“皇兄,你这么大反应干什么,我不就是买个女人嘛。”
“要是这个月见,就不行!”
孟梓铭觉得有些疑惑。
“有何不可?难不成皇兄也对她有别的心思?”
孟梓清冷哼一声。
“不过腌臜之地的风尘女子,怎能来污了我的眼?”
孟梓铭疑惑更甚。
“那就奇怪了,我买个女子在外头养着,用我自己的银子,也不劳皇兄费心,你为何要如此反对?”
“你堂堂皇子之身,怎么能和那种女人有联系?传出去让我们皇室的颜面何存?”
孟梓铭心中有些不快。
“我如此乱来已不是一日半日,怎么皇兄今日才想起来我毁了皇室的颜面?”
孟梓清几日来的不如意,在此时听到孟梓铭与他反驳之后,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出来。
“你成日里游手好闲,哪里有个皇子的样子!如今还敢来顶撞我,你莫要忘了,我可是你的兄长!你就该听我的!”
孟梓铭将手中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语气也生硬了起来。
“皇兄也莫要忘了,现在这皇宫中,说了算的可还不是你呢!”
说完,不顾孟梓清变得铁青的脸,佛袖而去。
孟梓清被孟梓铭最后一句话戳中了心事,不禁怒火中烧,最终大喝一声掀了桌子。
孟梓铭冷着脸一言不发回了宫中,他的皇子妃李氏很少见他如此冷酷的样子,便招来随身侍卫问话。
“今日殿下都见了什么人?”
侍卫知道这个李氏皇子妃性格泼辣,若是让她知道孟梓铭偷偷去见了月见姑娘,恐怕要闹得天翻地覆了。于是他隐去了这一段,恭敬地回答道:
“回禀皇子妃,殿下今日去了大皇子宫中。”
“可有事发生?”
“殿下与大皇子在屋内谈话,属下只在外头隐隐听到些争吵声,之后殿下出门便已是这般盛怒的模样,具体情况属下就不知晓了。”
李氏听完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孟梓铭一向爱跟随着他这个大哥,从未有过不和,到底是什么事会让两人竟然争吵起来?
孟梓铭回到自己宫中,静坐半天仍是无法平息心中怒火。他这个大哥平日里总是一副伪善造作的样子,今日不知抽了什么风,平白无故的要对自己发火。他只觉得眼前的什么东西都碍眼,乒乒乓乓将屋里全砸了一通才算消了气。
第二天一早,孟梓铭收拾停当便出发去了清风楼。虽然心中还是因昨天的事情有些耿耿于怀,不过想到月见马上就是自己的人了,又觉得舒心不少。到了清风楼,他将风清雅叫到一旁,正准备商谈为月见赎身的事情,却见风清雅福身施了一礼,面色哀切。
“孟公子,你来晚一步了。月见她,已经走了。”
孟梓铭立马喊出声来。
“走了?去哪里了?”
风清雅眼眶一红。
“昨日傍晚,有两人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与月见说了几句话,等那两人走了之后,月见便一言不发地回了房中。我知她近几日烦心,所以便没去打扰,谁知今早喊她吃饭,就见她将自己吊上了三尺白绫,就那么走了!”
孟梓铭脚下一个踉跄,推开众人便向月见房中跑去。进了门,却只看见月见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早已没了生气。风清雅跟着他进来,声音哀恸。
“月见昨日回来满心欢喜地对我说,孟公子愿意给她一个安稳的栖身之地。我许久没有看见她笑的那样美了,可谁知道,那竟是她此生最后的一个微笑。”
说完,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无声滑落。
孟梓铭身子晃了一下,再开口时声音冷若冰霜。
“风老板可知那两人是什么人?”
“我离得远,只隐约听到几个字,好像是……”
风清雅轻轻拂去眼泪,眼中有精光一闪而过。
“孟府,大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