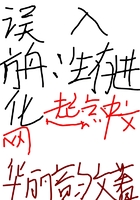钟离涟阳紧追于荀祉身后,荀祉没有办法,便飞入了荀府大堂,只见一身着盘金彩绣棉衣,项挂镶玉金圈,手挽轻罗纱,一对尊银希水晶玉镯串于手间,头盘朝阳五凤髻,插着十二金步摇的中年女子正襟危坐于贵妃椅上,一派雍容华贵,细看那眼如水般轻柔,想这女子年轻时也必是何等倾国倾城。
现在一面向那女子跑去,一面作委屈状叫道:“娘亲,娘亲,钟离他欺负我,快保护阿祉!那厮就快追来了,娘亲快将他使唤出去。”,荀祉扑进了那女子怀中,两眼清泪瞬间充斥着整个眼眶,似落未落,可怜巴巴的望着荀母——赵避霖。
赵避霖轻抚着荀祉背脊,一脸宠溺的说着:“唉,又贪玩了,你这小丫头片子,定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钟离的事,他才会这般追打你。再过几日就要及笄了,还是这般顽劣,也不怕他人笑话。”
“哼,那又如何。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再者,我便权当未曾听见罢了,我便是我,又何须改变?”荀祉冲着赵避霖调皮一笑。
须时,荀祉又似想起了什么,从赵避霖怀中跑出,在门前望了望空中那逐渐逼近的黑影,心神乱了起来。
“呀,莲花要来了。娘亲,你就看在阿祉平日里还算乖顺的份上,帮阿祉挡挡吧吧!我先走一步。”荀祉焦急的向赵避霖惊呼着,话落便向错综复杂的走廊跑去。
“砰”只听得一声巨响,飞尘铺天盖地而来,赵避霖急起身,奔向堂外,那一片尘雾中隐约见一身影缓缓爬起,向赵避霖走去,边抱怨着“啧啧,什么样,每次都这样,痛死小爷了。”,尘雾逐渐散了去,那人容貌也越发清晰,虽是满脸灰尘,却也能看出这男子正是“风度翩翩”的钟离涟阳。
赵避霖略皱了皱眉,这钟离每次使用御风术飞行,降地时都会把持不住,最终总会以头撞大地的惨状而结束,堂前石板也不知咋坏了几次,皆是修好后又被钟离涟阳丢脸丢到家的御风术折腾个面目全非。想到此处赵避霖颇为无奈,她怎地养了这两个顽猴,又是蹙紧了眉头,也不知在思虑何事。
钟离涟阳抬头,忽见赵避霖倚与门前,愣了神。本以为方才没人看见,还暗喜这次终于没人知道是他做的了,虽是弄得这般狼狈,却是无人知晓。可谁知此番大动作又被抓个正着,便十分尴尬的笑道:“义母,还是莫要怪罪我了,这,这我也无法控制啊。”
“无妨,虽这石板又被你砸坏了,你也不必自责,差人修好便是。今日我瞧你这御风术相较前几日还算有了长进,石板损坏程度小了些,便不怪你了。只是这御风术你还得抓紧练着,这种程度还是远不够的。”赵避霖安慰道,掏出丝绢来,细细擦拭着钟离涟阳脸上的灰尘,眼里蒙了层不知名的神色。
钟离涟阳呲牙笑笑,待赵避霖擦完,见她并无怪罪之意,便问道“义母可曾见过阿祉来过此处?钟离正寻着她呐,义母可否告诉钟离。”
赵避霖转过身,缓步走于贵妃椅前,庄仪坐下,端起桌上温热的上好龙吟茶,轻抿了一口,丝丝灵气环绕于唇齿间。看了看钟离涟阳,微张红唇,道“何必来问我,素日里你同阿祉那般要好,甚是了解她,定是知道她往何处去了,我就不用告诉你了,也省了一番精力,去吧。”
钟离涟阳听得此话,暗自诽谤道“也是,阿祉的小心思小爷也算看透了,她拿到雪灵石必是回房搞装修去了,按她这性格,若非那样,我还不信了呢!”便匆匆向赵避霖辞了去。
眼见堂内已无他人,赵避霖闭了眼,不知向何处说道:“那人走了?”
“嗯,走了。”暗处缓缓走出一身着一身雪白的直襟长袍,温润大气的柔美男子,两鬓几根银丝看上去略有些沧桑之感,眉头微皱着,向赵避霖走去,将手抚上赵避霖双颊,眼底一片柔情。那男子正是荀祉父亲,荀望凡。
赵避霖睁开双眼,望了望荀望凡,血丝赫然显现于眼中,突显两汪晶莹泪花从眼角滑落,留下两道水痕反着银光,一片茫然无措的眼神在这张雍容娇贵的脸上格外突出。
“荀哥哥,我舍不得。”赵避霖向荀望凡哭诉道。
“避霖,这世间有诸多舍不得,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有舍方有得,除了这样做,便也无他法了。该来的总会来,你我二人也终究躲不过……”荀望凡用手拭去赵避霖脸颊上的两行热泪,将赵避霖拥入怀中,柔情百转,终是无奈的叹了口气。
空荡荡的厅堂中只余相拥的二人,格外凄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