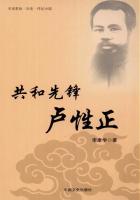一旦引入西方文学史的写法,文本之外的很多东西便获得了挤入文学史的机会。这些东西往往可以造假,比如各种流派的命名,因为这类命名是挤入文学史的捷径。本来按照中国传统是没有机会造假的,如果历朝历代只关注文本的话,这类命名就没有机会入史。所以,如果真要建立一个良性的评价体系,我们真应该参考中国古代的评价体系,当然我不是想全盘否定西化的写史方法,但既然选集体系有很好的治史功效,把它和西式治史方法结合起来,就有可能降低浮躁。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诗人的行为,普遍觉得很多诗人的个人操行很成问题,但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个人操行问题。这种操行跟刚才我讲的也有关系,既然造假也有机会入史,一些头脑聪明的人便会利用这些机会。其实个人修为的问题,还折射出我们整个环境缺少一种“士”的精神。中国古代有一种“士”的精神,我们当代已经没有。这个“士”的精神相当重要,说得白点儿,“士”的精神与西方文人所谈的知识分子精神其实一致,无非是对思想独立、自由、正义的追求和关注。“士”的精神曾在魏晋乱世、元代等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曾是中国文人的精神财富和创造源泉,导致古代文人的骨头普遍比较硬。相比之下,当代文人的骨头为什么普遍比较软?我觉得是当代缺了一种“士”的精神氛围。这种氛围的缺失,当然跟当代体制有关。在受到体制束缚的环境里,我们是否就该随波逐流、无所作为?我觉得自扫门前雪,从自己做起是根本。我们都应该怀着原罪的态度,我也不能例外,如果当代文学生态不好,我们每个人都难逃罪责,必须有勇气进行自我审判,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别人身上。说极端点儿,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养育和培育“士”的精神,应该成为我们心灵的重大课题。我想提醒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能否在个人范围内,恢复讲究修身,追求独立、自由、正义、良知的“士”的精神?
我还发现很多人有一种言清行浊的行为,什么叫言清行浊?说起来都特别的好听,修为的标准都很高,但是自己做起来,就完全是另一码事,可能他做的一切正好是他谴责的一切。我用“言清行浊”来描绘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与中国当代的“两层皮”文化有关。我们的当代文化有两层皮,一层作为内里的真皮,一层作为外表的假皮。在重大场合,我们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假皮”,很好听,无非是美德、良知、真相等等,实际行动起来用的就是那层真皮,那是一张装着人类全部欲望的真皮,这层真皮当然藏在那层假皮下面。当然,“两层皮”文化不是诗界独有的,是整个社会共有的。如果你真按“假皮”提供的想法去生活、做事,你就会四处碰壁,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孤儿。所以,很多人为了讨生活,只能采用“两层皮”的策略来应付。谋生存、利益时用“真皮”,诉说、交流、交际时用“假皮”。这个现象不是我们诗界独有的,只能讲,这是社会风气对诗界的渗透和污染,诗界已经失去抗污染的能力。
我还有一个感觉,当代批评已经圈子化了,圈子批评已经成为主体。我感觉,到处是圈子批评家。什么叫圈子批评家呢?说白点儿,在圈子批评家眼里,文本评价已经不再是文本评价,文本评价不过是一个权力问题。在圈子批评家眼里,我这个圈子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其他圈子的东西都微不足道。就是说,诗歌评价变成了权力权衡,这个问题导致我们的评价体系失效。这个现象在当代非常突出。圈子批评家已经把文本批评问题,蜕变成了权力问题。权力一般要靠多年养育才能获得,一旦获得就变成了可以左右他人观念的东西。其实每个人的判断力里,都有从众的裂缝,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弱点,每个人内心都藏着从众的恶魔,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孤单。当一个人听到掌有权力的批评家发话,他的判断力就会受到干扰,他之所以失去自信,无非是从众心理在作祟,尤其一般公众,难以抵御这种恶魔。所以,从众心理是圈子批评能发挥作用的人性依据。
纵观当代批评,机智的特别多,诚实的特别少。我认为,宁可要笨拙的诚实,也不要机智的撒谎。当代批评文章有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诚实与否,哪怕是笨拙的诚实,也比机智的撒谎高明许多。因为我们对当代的评价,一定有后人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评价经不经得起后人审视,其实每个写文章的人心里都清楚。
目前杂志太多也成问题,我的看法是,当代诗歌的出版与发表,已经走到了诗歌的反面。为什么这么说?当诗歌版面很少,编辑就会设定比较高的标准来选稿,因为每年产生的好诗不会太多。可是一旦有那么多的版面需要诗来发表,就造成大量版面得靠平庸之作来填充。这样的发表实际上是给批评添乱,给鉴赏添乱,给读者添乱,实际起到了湮没好诗的负面作用,同时也让批评承受着巨大压力,当然是说恭维话的压力,因为每个诗人都要求批评说恭维话,必然导致非常多的虚假批评,红包批评。
我把这类平庸之作,称为“废纸篓诗歌”。十几年前,这类“废纸篓诗歌”面世的机会比较少,现在面世的机会太多。过去扔进编辑部废纸篓的诗歌,现在堂而皇之出现在大量杂志、书籍里。平庸之作的大量发表和出版,可以说破坏了当代生态,它唯一的作用是普及了诗歌,但干扰了鉴赏和批评的秩序,成了谋杀好诗的帮凶。大量的发表机会,也让很多不错的诗人不能正确对待灵感。我不相信一个诗人有那么多的灵感,诗歌版面对这些诗人的追逐,那些要求他们发表诗歌的呼声,那些蜂拥而来的约稿,导致很多诗人经不住诱惑,就铆足了劲儿写。这也说明,我们对数量的迷恋,远远甚于对质量的迷恋。对单首诗的迷恋,远远低于对集束诗歌的迷恋。我们几乎用发表消灭了对单首诗的关注,我们关注的不再是单首诗,关注的是一个人在各种杂志的出镜率,我们开始像要求明星那样要求诗人。
此外,我们的生态里还有不少政治思维的遗存,比如,“大跃进”思维,“文革”思维。“大跃进”思维,导致我们迷恋多快好省,决定了我们做事的一些特性。比如,都喜欢通过评奖、评选等,快速选出大诗人,没有意识到评奖或评选,并不能令一个诗人超越文本的价值,得奖最多的诗人,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诗人。认为通过评奖评选,就能解决审美甄别问题,不过是大跃进思维在诗坛的体现。其实审美甄别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看看古代就非常清楚。很多大诗人的地位,绝对不是通过一个朝代就可以确立,有的甚至两个朝代都确立不了。如果仔细考察李白、杜甫之流,就会发现,他们在唐代并不算大诗人,陶渊明在自己的年代更不是,他们大诗人的地位主要在宋代确立。比如,陶渊明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当做一个中品诗人,难入大诗人之流。“大诗人”不是空间概念,它是历史或时间概念,把历史概念当空间概念来使用,是我们当代的一个误区。尝试在当代确立大诗人,实际上是把出没在未来的关卡拆除了,这是政治自大的表现,不过是把我们时代颂扬为最伟大时代的野心。想一想魏晋玄言诗在后世的命运,我们就应该抑制这种文本外的野心。若真有野心,不妨把它撒在文本里。
至于“文革”思维,它的表现更是普遍。刚才陈超兄提到,当代“二元对立”的东西在诗歌里已经在减弱。我觉得在诗人言行上还很普遍。为什么诗坛的争吵特别多?多数争吵的实质就是相互攻击。我认为,这是农耕时代一元思想的体现。大家之所以吵,无非是想吵出名堂——直至某人吵赢!吵赢的目的不是为了接近真理,只是为了征服对方,用自己的思想消灭对方的思想,这是赤裸裸的一元思想,跟新诗关注的现代性完全背道而驰,现代性思想的根基就是多元并存。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身体虽然已经滑入现代社会,但脑袋还留在农耕时代。我们还不太适应现代社会,我们现代意识的发育还不充分。正是对现代性认识的不足,才导致诗坛有那么多的争吵发生。现在到了该抛弃一元思想的时候,该建立一个观点和文本的市场,让各种观点和选本自由竞争,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一定会产生好结果。我记得经济学中有个科斯定理,它是说: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不管产权属于谁,市场都能使配置最优。把这个定理应用到诗坛,可以这样讲: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不管好诗是谁写的,市场都能把它挑出来。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的交易成本一般不为零,通过贿赂、利诱、人际关系等,我们已经把交易成本升了上去。如果交易成本真为零,那么市场一定会优选出好诗,我们就不必为审美甄别的问题人为操劳。
最后,我认为口碑也非常重要。大家可能有同感,用文章表述的看法和在私下传播的口碑往往不一致。我认为口碑是评价体系里的原生态,应该好好保护它。现在有许多人通过文章、贿赂等各种手段在破坏这种原生态。我们应该把私下流传的对某个诗人,对某首诗的真实看法,像文物一样保护好,在同一个时代空间里,口碑的判断是经久的,时常比文学史著作、批评著作等的判断更靠谱。
林莽:到现在四个发言人,各有各的角度,都说得非常好,黄梵从文学史切入,讲到文人的骨头、修为,他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审视,另外还讲了各种各样的思维、圈子批评等,都非常好。
潘洗尘:近五年来,包括在天问举办的五届活动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言。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是由于自己游离诗坛多年,虽然起步不算晚但现在我是心悦诚服地把自己当成一个后来者,我怕自己对有些东西还看不全、看不准,怕说错话、怕说外行话,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只想听、只想看,只想默默地写、默默地做一些事,尽管到现在做得也还不够好,写得就更不够好了。
近几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的是,除了大量的无产者(意识形态领域的和生活层面上的)充斥诗坛之外,还有一批莫名其妙的人,也时常出现在各种诗歌出版物和诗歌活动上。这也是我尽量少参加各种活动的原因,今年以来我拒绝了几十个活动的邀请,只参加了三个自己主办或必须参加的活动。我确实有时候还不能自信到把自己“可疑”的身份洗脱“干净”的程度。我也怕,仅仅因为我的职业,对我所从事的,完全是基于热爱的事情形成伤害。
诗歌生态这个话题,很早以前我就向林莽兄和树才兄提出过,而且我们私下里也讨论过多次,我也写过一些东西,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就几个目前比较突出的“生态”恶化的现象和问题,简单地谈一点儿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想谈谈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的问题。因为这几年办《星星》诗歌理论刊物,所以就对诗歌评论这一块关注得比较多。
近几年又开始有人过分夸大诗歌写作的社会功能了,这是让我觉得忧虑和担心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像汶川地震后带来的灾难写作热,其实,当天灾人祸发生时,诗人出于良知自发地表达各自的悲与悯,这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如果当灾难写作不再是诗人自发的,而是应景的甚或是被组织的,这就会导致灾难写作的泛滥,而在天灾人祸注定会越演越烈的今天,灾难写作一旦泛滥,则必然要导致写作的灾难。
另外还有一点儿担忧,就是当下诗歌批评标准的严重缺失和批评家的浮躁,尤其是年青一代批评家的集体浮躁。
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像谢冕老师那一代和晓渡兄这一代批评家,他们不仅都有着深厚的学养,更是一切从文本出发,他们的批评是建立在对文本的把握上的,但现在我们的很多年轻批评家,他们更热衷于采取投机式的做法,不愿意干文本把握这样的细活累活,更有的索性抛弃文本,大搞学术投机,最典型的就是“命名热”的出现,这样更容易因引发话题而被关注,比如近一两年来出现的有关“新归来者”的命名,我因为也是主要的“被”命名者之一,所以只好反复声明自己拒绝“被”命名的立场。为什么?理由非常简单,诗歌也许是我穷尽一生都无法抵达之地,一个人有什么资格可以面对自己还从未到达过的目的地谈“归来”?批评家可以以此来制造噱头,但我们自己却应该始终清楚自己的斤两。
我曾对多个年轻的批评家谈过这样的一个观点,一个批评家其实把一首诗读好了,批评就已经完成了一半了。这几年《星星》每期的栏目都有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桑克主持的《文本细读》栏目,目的就是想要倡导一种从文本出发的批评态度。
另外,从诗歌写作的层面上看,问题也是比较多的。一是诗人们对话语权争夺的热衷有时候远远大于对文本精耕细作的热忱,这对写作带来巨大伤害。二是近年来由于诗歌写作的门槛被无限降低造成的诗歌写作泛滥。我真想写一篇文章,奉劝一些年轻人,干吗非得要让自己去写一些只是看上去很像诗歌的东西呢,既然诗歌只能是少数人的事,那就不如还是交给那些真正有天分的人去做好了。
现在我想重点说一说诗歌刊物。一份好的诗歌刊物,应该是一个过滤器。只不过,现在的绝大多数刊物,都已经丧失了这个功能。所以,现在的刊物,已与泥沙俱下的网络媒体没什么差别了。我们为什么办《读诗》?这些年我能够看到的刊物非常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现在,绝大部分的诗歌刊物都成了卡拉OK似的了,只要你翻开,基本上全都是作者和作品在自娱自乐。而《读诗》,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诞生的一本对自己有着明确要求的诗歌刊物,我不敢说我们能把它办得有多好,但是我敢保证,合我们四个人之力,一定不会把它办得很差。
现在,人们常常把诗歌交流变成了诗歌交际,各种座谈会、研讨会等诗歌活动无不是如此。至于中外的诗歌交流,也难说不是如此。结交外国诗人是为了译介自己作品、受邀参加国外的诗歌活动或是为了获得国外的什么诗歌奖项。
和公共话语体系、社会世俗的对抗与分离,在精神上实现高度自治,本应是我们所热爱的诗歌的最基本姿态。但是,随着权、钱、色对诗歌的全面渗透,目前我们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社会不公正现象同流合污,我们的诗歌生态正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困境与险境,甚至是绝境。
我的结论:对于诗歌而言,一个可能是最坏的时代已经到来。
林莽:今天的论题就是我们和洗尘多次交谈产生的,最后的题目是我定的,我觉得洗尘的发言是身在其中的体验,这点很重要。下面请燎原发言。
燎原:诗坛的生态问题,对于当代诗坛的评价问题,也是我长期以来关注的。因此,我也很想知道我的同行们在想什么、怎么看。刚才大家的发言使我获得了很多信息,至于我自己,对于新世纪十年的诗歌生态,我的评价可能要略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