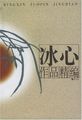星期二身着蓝色睡衣
淡淡的惆怅插在花瓶里
轮船在天空为我们铺了一块桌布
吉他和手风琴入夜在阳台上泣诉
庄稼汉和卖菜人憧憬的日子
形状同地图相似
这是星期三,你听!独轮车在呻吟
这是星期三,你听!骡车的铃铛在林荫路上丁零作响
邮递员送来一封书信
女傧相从教堂捧回了爱情
一只花蝴蝶跟在她的身后追来
星期四的黄玫瑰泛着乳白色光彩
星期五骑着一匹棕色大马
士兵们列队进行军事演习
阳光同帽徽在嬉戏
手摇风琴的嘶叫声音凄厉
摩托车选手穿一套运动衣裤
散步场上冒险家昂首阔步
一周之中我最爱星期六
金发缪斯降临人间同我闲游
下一代
女人晒黑的乳房使我的思绪
飞向生长着石松的倦怠的赤道
在那里一个白人抚摩着
一个晾甘蔗的黑女人光裸的线条
啊,我愿为这个女人缝制一件花边似的薄纱衣
我将带领她穿过草原来到湖边
让她看一看自己裹着轻烟多么俏丽
我将向她倾诉我的爱恋
然后我将缓缓地缓缓地解开她的衣襟
跪在尘埃上亲吻她的鞋子
呼唤明月和永不凋谢的满天繁星
在醇酒般的月光下
我将同她幸福地生一个儿子
为纪念这个夜晚他长大后将是诗人
十一月
今天连碧空也满是窟窿眼
树枝光秃秃
唯有山谷里的柏树林尚在
闪烁
你走在纷乱的行列
暗自流泪
落叶飘下石阶在蒙蒙迷雾中
消失
今天连十字架也已朽坏
心中无比寂寞
吻你的额头我的双唇
瑟缩
赛弗尔特
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1901—1986),深受诗歌主义的影响,决意要写尽世上一切的美。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对某些主题的特殊偏爱了,比如女人,比如紫罗兰,比如扇子。美是他的主题,也是他对抗艰难时世的有力武器。他的大多数诗都充满了诗意的温柔和温柔的诗意。著有《岛上音乐会》等三十多部诗集。1984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在诗歌中“展现出人类不屈不挠的解放形象”。
被吻的芳唇迟疑地……
被吻的芳唇迟疑地
微笑着,轻声说:“是的。”——
这样的耳语我已很久没有领受,
它们也不再属于我。
但我寻找的话语依旧是
面包瓤儿
搓成,
或菩提树的馨香制就。
可是面包已经发霉,
香味变成苦涩。
话语在我周围蹑手蹑脚逼近,
当我伸手去捕捉,
它们堵住了我的呼吸。
我不能把它们一一诛灭,
它们却要将我窒息。
而一阵阵的诅咒在我门上轰鸣!
倘若我强迫话语为我跳舞,
它们便一个个哑了口,
还跛了足。
然而我深知,
诗人说出的话语,无论何时
都必须比吼声中隐匿的更有意义。
这就是诗。
否则他的诗句就不能
剖开蜜的帷幔,让花蕾展现丰姿,
或者在揭示赤裸的真理时
使一阵寒颤
冷透你的脊背。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我看到
日头红得像血。
此番景象以后从未再见。
昭示着不祥,它徐徐落向地平线,
仿佛有人
踹开了地狱的大门。
这事我曾询问天文台,
今天已经明白了原委。
地狱,我们知道,无处不在。
它不停地游荡,迈动两条腿。
至于天堂?
天堂也许只是
我们久久期待的
一个笑颜,
轻轻呼唤着我们名字的
芳唇两片。
然后那短暂的片刻令人眩晕,
令人忘却了
地狱的存在。
间奏曲
倘若有人问我
什么是诗
瞬息间我会心中慌乱,
虽然对诗我已这般谙熟!
我曾反复吟诵已故诗人的诗篇,
一次又一次
它们照耀我的旅途
像黑暗中的火焰。
然而,生活并没有踮起脚尖悄悄行走,
却不时抓住我们,凶狠地摇晃,
跺着脚。
我常常摸索着寻找爱情,
犹如一个双目失明的人
两手在枝头摸索,
渴望把浑圆的苹果
抱在手中。
我知道有一首诗,
它的力量像地狱的咒语,
足以震开天堂的门扇,震断门上的铰链。
我望着一双惊讶的眼睛低吟这首诗。
惶恐随着诗句在眼中凝聚,
疲软的两臂怎能抗拒
爱的拥抱!
但是,倘若有人问我的妻子
什么是爱情,
她也许会失声欷歔。
霍朗
弗拉迪米尔·霍朗(1905—1980),在欧美影响极大。长期居住在布拉格的康巴岛上,离群索居,思考生死、存在、爱情、时间和道德等重大问题。他的诗歌告诉人们:诗歌其实就是诗人的自言自语。主要诗集有《死的胜利》《云路》等。
她问你……
一个年轻的姑娘问你:什么是诗?
你想对她说:诗,也可以说是你,哦,是的,
也可以说是你
心中又是慌乱又是惊喜,
意味着眼前出现了奇迹,
你丰满的美使我痛苦、妒忌,
而我不能吻你,不能与你共枕同床,
我两手空空,一个拿不出献礼的人
便只有歌唱……
可是这番话你没有对她说出,你默默无言,
这支歌儿她于是不曾听见。
有一天早晨
有一天早晨,当你打开大门,
你发现一双小舞鞋放在你的门前,
它们那般惹人喜爱,你马上捧在手中吻了又吻。
几年后的一天,同样的欢乐再次出现,
久久压抑的泪水
一齐涌进双眼,化为一个笑颜。
你于是纵情欢笑,灵魂深处的歌声
回荡在青春的寂静……
然而你没有询问,是哪位美人
把一双舞鞋放在你的门前。
这事你不曾弄清,
但那幸福的片刻
却令你迷醉至今……
恋歌
在意志的地平线上,我要
扭转你的目光,去注视
空灵的画面于群山之中,
那里的浓荫会使你步履轻盈。
我要扑灭你脚上的光彩在山岩上,
让你的足音在深渊悄然入梦,
我将收下你,像收下我的一个丢失,
仿佛我想拥有世上的一切。
当你的眼睑发暗,也许是因为困乏,
我将点燃双手
把你奉献,像献出我的一个发现,
仿佛上帝正一无所有。
霍卢布
米罗斯拉夫·霍卢布(1923—1998),在医学和文学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相当程度上,正是医学成就了他诗歌的独特性。他的诗作从现实生活出发,针砭时弊,或借古讽今,笔锋辛辣,幽默,语言简练,冷静。主要诗集有《阿喀琉斯和乌龟》等。
加利列?伽利略
苍蝇舔着圣徒们的鱼眼。
我,加利列?伽利略,
在此听候裁决,
我起誓……
大地惊愕。
太阳被连根拔起
哀号着跌落,
太空缩进圣烛,
天文学家们个个两眼昏花……
我,加利列?伽利略,
在此起誓:
我向来相信,
现在相信,
将来,上帝保佑,也永远相信……
望远镜前疲惫不堪的人们
彼此询问——现在怎么办?
孩子们离开课椅,
拼音课本鲜血淋漓,
历史的搬运工收拾起背筐,
旅程半途而废,
真理残缺不全,
犹如骨鲠卡在喉际……
……相信罗马教皇的神圣天主教会
所宣布、承认和教导的一切……
四境寂静无声。
地球被出卖了。
太阳被出卖了。
梦在血管中结成了冰。
他,加利列?伽利略,
佛罗伦萨人,年龄七十……
我,加利列?伽利略
置身在米内维纳教堂,只穿一件衬衣,
靠一双细腿
承受着世界的压力,
我,加利列?伽利略,
低声,
低声地说,
为了孩子们,为了搬运工,为了太阳——
我低声地
终于说……
地球
确实
在转动。
诗人
正是这个月亮总有缺的一边
——维杰斯拉夫?奈兹瓦尔
有人用步枪打落图像
如同打落纸做的玫瑰花朵,
有人用大头针扎在诗句上
如同把风干的蝴蝶钉在标本匣中。
昆虫学家的心
像甜奶饼一样
——地球在他们眼里并不沉重。
可是有人把诗句捧在手中,
放出它们像放出一群飞鸟,
播种它们像播下花种,
从山坡上把它们撒向四方,
像雪片纷纷扬扬
——这就是他。
在歌曲的灯盏上
他提炼
黑夜的苛性碱和白昼的琼浆,
在曲颈瓶中生产
空气,
水,
光明
和希望
一位炼金术士,
诗歌的有机化学家,
洋溢着
物质的光华,
心脏活泼的血流,
古代语言的频率,
新星的光谱,
比大地更重,
比思绪更轻,
比时速更快——
等我们飞上
月球,
他早已在那里等待。
沙切克
伊希·沙切克(1945—?),他的创作明显带有诗歌主义的印记。他的诗歌活泼,风趣,幽默,常常从生活琐事中提炼出诗意。主要诗集有《早晨比黄昏青色更浓》《纸做的玫瑰》等。
偷看
从钥匙孔里我窥见
一个骇人的陌生世界。
乍看胆寒心惊——
飓风狂吹,太阳在嘶鸣。
在那里,河面上盛开着鲜花,
是奥菲利亚的鬈发,
繁星如急雨
把忧郁的铅水向地面倾泻。
我从里边向外张望,
瞪大一只饥饿、润湿的眼睛,
然而在四面墙壁的锻压机中我被囚禁,
欲出不能——我想上哪儿?
我,一根干透了的火绒,
将会烧成灰烬,
在那个甜蜜的枷锁世界,
在钥匙孔的那一边。
悼威莱姆?扎瓦达威莱姆?扎瓦达(1905-1982):捷克诗人。
诗人何必去给世界镀金?
这个活儿自有油漆匠去干。
诗人也不是
沙龙的明星,玩弄闪光辞藻的魔法师。
他应该敢于鄙夷“艺术”,
有勇气和力量淳朴守真,
用他的诗——心灵深处采集的坚石——
建造一座殿堂。
虽然天晓得为了谁。
像你一样。
诗必须什么样
一
诗的节奏必须和心的跳动合拍,
否则它将被沙沙的纸声湮没,
破碎纸张的沙沙声,
纸上印着你的讣闻。
二
诗必须什么样?没什么,
只是等候。价格在上涨。
不过,你,你必须每天跑在前头,
少说也要超前五分钟。
孤独,但并不寂寞
——纪念杨乐云先生
高兴
一
2009年底,翻译家杨乐云以九十高龄告别人世。
正是最冷的时刻。她的离去显得有点儿仓促,甚至还有点儿窘迫,仿佛在一瞬间摧毁了所有的诗意,却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一个文人的命运。
在拥挤、混乱的急诊室里,我听见先生用尽力气说出的话语:“回家,我要回家。”
先生要回家,回到她的屋子,安安静静地靠窗坐下。抬起头,就能看到两个外孙女的照片。或者把身边的几本书拥在胸口,代替呼吸。那些心爱的书,哪怕摸摸,也好。然后,闭上眼睛,顺其自然,听从死神的召唤……
对于病危中的先生,回家,已是奢望和梦想,已成为最后的精神浪漫。
二
记忆,时间的见证,这唯一的通道,让我们再度回到过去。因了记忆,时间凝固,融解,成为具象,化为一个个画面。
先生在不断地走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已在《世界文学》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临近退休,开始物色接班人。当时,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出于爱好,更出于青春的激情,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书籍。诗歌,小说,散文,中国的,外国的,什么都读。不时地,还尝试着写一些稚嫩的文字,算是个文学青年吧。在80年代,不爱上文学,在我看来,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关于那个年代,我曾在《阅读?岁月?成长》一文中写道:
80年代真是金子般的年代:单纯,向上,自由,叛逆,充满激情,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那时,我们穿喇叭裤,听邓丽君,谈萨特和弗洛伊德,组织自行车郊游,用粮票换鸡蛋和花生米,看女排和内部电影,读新潮诗歌,推举我们自己的人民代表;那时,学校常能请到作家、诗人、翻译家和艺术家来作演讲。有一次,北岛来了,同几位诗人一道来的。礼堂座无虚席。对于我们,那可是重大事件。我们都很想听北岛说说诗歌。其他诗人都说了不少话,有的甚至说了太多的话,可就是北岛没说,几乎一句也没说,只是在掌声中登上台,瘦瘦的、文质彬彬的样子,招了招手,躬了躬身,以示致意和感谢。掌声久久不息。北岛坚持着他的沉默,并以这种沉默,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们当时有点儿失望,后来才慢慢理解了他。诗人只用诗歌说话。北岛有资本这么做。
先生相信印象,更相信文字,在读过我的一些东西后,问我毕业后是否愿意到《世界文学》工作。我从小就在邻居家里见过《世界文学》。三十二开。书的样子。不同于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图。早就知道它的历史和传统。也明白它的文学地位。不少名作都是在这份杂志上首先读到的。我所景仰的诗人冯至和卞之琳都是《世界文学》的编委。于我,它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我当然愿意。
“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这将是一条清贫的道路。”先生建议,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
当我最终表明我的态度后,我知道这是份郑重的承诺。
三
先生那时已年满六十,瘦弱,文静,有典雅的气质,说话总是慢慢的,轻轻的。一个和蔼的小老太太。退休前,所里要解决她的正高职称,她却淡然地说:“我都要退休了,要正高职称有什么用?还是给年轻人吧。”
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到《世界文学》实习,正好带带我,也让我感受一下编辑部的氛围。记得高莽先生初次见我,大声地说:“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
那个年代,当编辑,就意味着为他人做嫁衣。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以至于,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挖掘选题,发掘并培育译者。先生做起编辑来,认真,较劲,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会为了几句话,几个词,而把译者请来,或者亲自去找译者,对照原文,讨论,琢磨,推敲,反反复复。有时,一天得打无数个电话。那时,用的还是老式电话,号码需要一个一个转着拨。同事们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拨肿了,贴上胶布,还在继续拨。在编辑赛弗尔特的回忆录时,光是标题就颇费了先生一些功夫。起初,有人译成《世界这般美丽》。先生觉得太一般化了,还不到位。又有人建议译成《江山如此多娇》。先生觉得太中国化了,不像翻译作品。最后,先生同高莽等人经过长时间酝酿,才将标题定为《世界美如斯》。为几句话几个词而费尽心血,这样的编辑,如今,不多见了。
先生选材又极其严格,决不滥竽充数。每每遭遇优秀的作品,总会激动,眼睛发亮,说话声都洋溢着热情:“好极了!真是好极了!”随后,就叮嘱我快去读,一定要细细读。读作品,很重要,能培育文学感觉。先生坚持认为。在她心目中,作品是高于一切的。有一阵子,文坛流行脱离文本空谈理论的风气。对此,先生不以为然。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她不解地说。
“读到一个好作品,比什么都开心。呵呵。”这句话,我多次听先生说过。
四
这一辈子,太多的荒废,太多的消耗,什么事也做不了。先生常常感慨。
我能理解先生内心的苦楚。先生这一代人,从事东欧文学,总是生不逢时。上世纪50年代,刚刚能做些事情,中国和东欧关系恶化,陷入僵局。不少东欧文学学者还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才华,便坐起了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几十年。之后又是“文化大革命”。清查。大批判。下干校。折腾来,折腾去,政治总是高于一切,专业则被丢弃在一旁。到了70年代末,国家开始走上正轨时,他们大多已人过中年,临近退休。到了80年代末,一切正要展开时,又遇上了东欧剧变。东欧剧变后,困境再度降临:学术交流机会锐减,资料交换机制中断。看不到报刊,看不到图书,看不到必要的资料,又没有出访机会,这对于文学研究和翻译,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年,到后来才逐渐得到改观。而此时,不少人已进入老年。先生他们走的是一条异常艰难而残酷的人生道路。
我也能理解先生退休之后近乎拼命的劳作了。就是想做点儿事,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做点儿自己喜欢的事。喜欢,没错,就是喜欢。先生不会说热爱,也不会说敬畏,而是说喜欢。热爱和敬畏,对于她来说,太浓烈了,也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