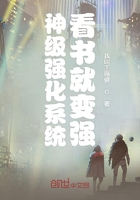我站在她面前,乞求她再给我安排一个训练时间。
“你叫什么名字?”
我把证件给她看了看,然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她的身后有一块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参赛选手的名字,她则一脸狐疑地在上面查寻可行人选。我不禁想到了G夫人。她的手指在左边那一栏上下移动着。
“好吧,”她说,“4点钟,8号球场。”
我瞥了一眼将和我共同训练的人的名字。
“真抱歉,我不能和那个人一起训练,我可能会在第二轮比赛中遭遇此人。”
她一边在黑板上开始重新查找,一边叹着气,表现出一副非常不耐烦的样子,这使我不禁怀疑G夫人是不是有一个失散了很久的姐妹。至少我现在不再留着莫西干头,对于这个女人来说,那会使我显得更加无礼。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我现在的发型也没有好到哪里,依然很是张扬。首先,我头发的一部分颇为蓬松,另一部分则很长,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这就是所谓的胭脂鱼发型。另外,我的发根是黑色的,而发梢则被染成了白色。
“好吧,”她说,“17号球场,下午5点。但还有其他三个人也要练习,你得和他们共用一个场地。”
我对尼克说:“我感觉我在这里随时都有危险。”
“不会的,”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整个地方从远处看起来会好很多。
什么事情不是这样的呢?有时我们需要距离。
第一轮比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英国的杰瑞米?贝茨。我们在一处偏僻的外场比赛,远离人群,也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我很兴奋,也很骄傲,同时我也很害怕。我感觉它就像是这项赛事最终在星期天举行的决赛。我紧张得颤抖不已,甚至直想吐。
因为这是一项大满贯赛事,比赛的气场与我所经历过的任何一场比赛都不同,更加狂热。比赛以一种扭曲的速度进行着,我对这种节奏十分陌生,加之又是个大风天,因此分数就像口香糖包装纸和灰尘一样从我身边不断溜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甚至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场网球赛。贝茨的实力并不比我强,但他打得比我好,因为他知道这次比赛中他将会面临什么。四盘比赛后,他战胜了我,然后他抬头看了看包厢里的菲利和尼克,并做了一个用拳头捶臂弯处的动作—“去你妈的”的国际通用手势。显然贝茨和尼克有段过节儿。
我感到很沮丧,还有一点儿尴尬,但是我知道我对我的首次美网或纽约之行显然准备不足。我看到了自己现处的位置和需要达到的位置之间的差距,同时我对弥补这个差距也相当有信心—适度的而非盲目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