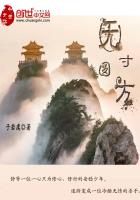)第一节艰难的选择
在建国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那些自由主义作家们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和被选择。大部分人选择了留下,选择了祖国。他们选择的时候虽然心情都很复杂,但都是心甘情愿的,被选择的时候却非常被动。他们的选择都非常单纯,就是为了祖国,为了下一代。但他们的被选择却有很复杂的条件。但这就是他们与新中国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沈从文的边缘性更加突出了。他这一关过得异常艰难。沈从文在一开始就失去了入选的条件。在左翼作家的眼中,他甚至不算是一个民主作家,而是一个“反动作家”。因为被新时代排斥和拒绝,沈从文陷入了自我迷失的疯狂境地。站在旧的边缘,沈从文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光,而且是一种特别孤独的痛苦。我们险些失去了他。他本来是习惯于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世界的,如今却要面对一个一切都不能质疑的世界。即他所谓的由“思”向“信”的转变,这也是他觉得转变特别难的一个地方,如果他真的有所转变的话。
沈从文在建国前的坎坷命运究竟源头何在呢?虽然并不是有意识的,但确实也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是他那持续不断的批评热情引来的。
一、选择“战斗”
决定了沈从文命运的选择是他的“政治热情”。言论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持续不断的表述的热情。以专家建国,专家治国论为基础,沈从文恐怕也有了专家心态。才非常积极的干预时事。如果说他之前的批评主要是对文坛的批评,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从解放战争爆发以后,他涉及了政治批评。当然他的政治批评仍然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发出的。
沈从文对政治的厌恶始于他对一切都不信任的怀疑论,也源于他特殊的时间观。他的时间观其实是一种历史观。他不追求时下的价值,认为时间会成毁一切。而政治在他看来恰恰是追求瞬时性的意义和成败的。他的目标在于超越时代的远方,人生的远景。对政治的厌恶还因为其功利性。沈从文的人生观和文学观都是审美性的,超功利性的。他主张官能化的审美。要在绝对孤独的境界中调用所有的官能去观察、审视和感知世界人生。世界的认识在他看来应当靠感受而不是分析。政治在他看来是一种太急于下结论,太急于命名的对世界充满了隔膜的认知方式。他对政治始终是厌恶的,而且一定要把这种厌恶表达出来,不厌其烦,以至于总是在某个关键时刻扮演一个不合时宜的角色。沈从文的政治的关注也是反抗性的。鉴于这样的态度,他其实缺乏政治敏感,但他对政治的逆反热情特别高。沈从文对待政治的态度就像唐·吉诃德战风车,他实际上并没有看清对手,却一定要向其开战,失败是一定的,还要伤了自己。政治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大致就像是一个怪物。他并不真正懂它,但对它很有看法,要不停对它进行战斗。所以,他就像唐·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地不停地对“政治”发出反对的言论。沈从文的政治关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要求政治给文学以自由,另一个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内战。文学在他是个生命,他像母鸡保护小鸡那样维护着文学的安全。而政治就像是狼外婆,随时窥视着文学。他知道自己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但他一定要乍起自己的翅膀,表示自己的态度。他觉得政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总是在干扰着文学自身的磁性。他针对左翼提出的反对“差不多”问题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这些政治言论很容易被人误解,就像是唐·吉诃德刺向风车的矛,注定要折断。他因为反对文学作为宣传而评判“抗战八股”,希望作家的作品能够以“与战事好像并无关系,与政治好像并无关系,与宣传好像更无关系”的方式来写“与这个民族此后如何挣扎图存,打胜利后建国,打败仗后翻身,大有关系”(《一般与特殊》.《沈从文全集》17卷.)的作品。结果被归入了“与抗战无关论”。他的意思只是希望有人热衷于宣传的时候能有人投身于实际的工作。两场论争的核心,沈从文都是在强调作品大于理论的观念,他忽视了一定时期宣传的必要性。但这还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触碰了政治。他所有的政治批判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政治态度是一种充满了功利的态度,受其影响,人就会成了“《金瓶梅》中之应伯爵谢希大一流人物,本色是凑趣帮闲,从中捞点小油水”,他们多“朝秦暮楚”现象和“东食西宿”(《文学运动的重造》.《沈从文全集》17卷.)现象。以这种态度来从事文学是对文学最大的伤害,文学就远离它本身了。结果,他反对作家持这种政治态度被总结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反“差不多”、“与抗战无关论”、“反对作家从政论”都是从文学的角度反对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干涉。因为天真地维护文学而往往把矛头指向左翼,为他后来的被批判留下了充分的证据。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沈从文并不反对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且对文学的功能有积极甚至是夸张的强调。他这些论调都是在强调谈文学就不能没有作品,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文学不能流于空谈。而他这种积极的批判热情其实也源于他相信文学,包括这些批评能对社会生活起到干预作用。
给他带来更严重的危机的是他反对内战的论调。他对待战争的态度则像一个地道的乡下人,并没有特别的政治意识,而是对于流血和牺牲有着本能的厌恶。他的态度正像会明,“不打仗,他仿佛觉到去那大树林涯很远,插旗子到堡上,望到这一面旗被风吹的日子还无希望。但他喂鸡,很细心地照料它们,多余的烟草至少还能对付四十天,他是很幸福的。六月来了,这一连人没有一个腐烂,会明望到这些人微笑时,那微笑的意义,是没有一个人明白的。”(《会明》.《沈从文全集》9卷.)眼前的幸福和快乐是最重要的,生命是最珍贵的,其他都不重要,哪怕是正义的理想,也应该让位给这幸福和生命。所以他才会不止一次地说解放战争是“民族自杀悲剧”。此说最早出自于沈从文写于1946年的《从现实学习》。1948年的9月1日,大局已定,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沈从文写了《中国往何处去》说:“这种对峙内战难结束,中国往何处去?往毁灭而已。”(《中国往何处去》.《沈从文全集》14卷.)他以人民渴望和平的立场而反对战争,但他把希望寄托在专家学人和知识青年身上。他的人民立场和共产党的人民立场有着根本的不同。他说自己“写城市,全把不住大处,把不住问题,不过是一种形式的抒情而已”(《致布德》.《沈从文全集》19卷.67.)。实际上这可以说是他理解事物的特点。他重视的是细节,是情感。他对解放战争的理解上正体现了这一点,他只看到人民的苦难而不相信战争实际上还会主持和决定正义。他所有的政治言论都成了他的罪状。郭沫若说“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罪重不在反动,而在“有意识”。罪状就是:“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48.)其实,沈从文说这些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意识。我们一再强调,他一切言论的发论点其实都是文学,都是审美化的。言论引来的批判都成为了沈从文难以摆脱的精神负累。他一直忧虑着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桥梁。结果,他甚至没有办法让别人理解自己。他很难想通自己错在哪里了。其实他和郭沫若等批评他的人一直都不在一个层面上想问题。最初,他感觉到的是失败而不是错误。他是因为想不通才陷入自我迷失的疯狂境地的。
二、选择方向
在时代转型的时期,沈从文等京派作家最希望的是能保留自由选择自己的文学方向的权力。明显地,他们已经感觉到他们所坚持的文学选择和方向会失去存在的空间。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发表于1948年3月1日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这一辑的总称就是《文艺的新方向》。郭沫若、冯乃超、邵荃麟等人主编和主笔的《大众文艺丛刊》所宣传的文艺新方向就是新中国文学的方向,其依据就是充分大众化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工农兵生活为内容,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形式的方向就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和沈从文等京派作家所坚持和主张的知识分子化的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方向分歧是很大的。这也是他们要谈新文学方向的最重要的时代背景。因为,就京派文人而言,他们实际上是不会把“方向”这样的词汇放置到他们的文学批评视野中去的。他们关于文学方向的讨论,显然是针对左翼所提出的新方向的,也是在考虑自己在这种新方向中的位置。
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今日文学的方向》发表于1948年11月24日的《大公报·星期文艺》。我们可以从对照中看出,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对文学方向完全不同的态度。《斥反动文艺》明确表示了政治第一,文学完全服务和服从于政治的思想。“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作品,倾向和提倡。”(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48.)方向性极强。如此壁垒分明的界说偏偏对准的是第三者。《今日文学的方向》表达了京派自由主义作家们对于文学前途的深切的忧虑。沈从文已经感觉到了政治的强大渗透力。他提出了“红绿灯”的比喻。
冯至:他们(指马克思与弗洛德)是以为他们的路是正当的路呢,还是大家应该知道有这二种路子呢?如果指后者,知道一点自然是应该的。
钱学熙:他们认为他们的是唯一的,正当的道路。
金堤:实际上这就是文以载道的问题了(马、弗都代表一种‘道’)。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也许可以说得更确切一点:即文学是否必须载道呢?目前认为文学非载政治的‘道’不可,不知诸位先生的意见如何?
……
沈从文:驾车的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汪曾祺: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即是承认他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诸位前辈能告诉我们自己的经验。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废名:第一次大战以来,中外都无好作品。文学变了。欧战以前的文学家能推动社会,如俄国的小说家们。现在不同了,看见红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
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受规矩而已?
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比如孔子)
废名:文学与此不同。文学是天才的表现,只记录自己的痛苦,对社会无影响可言。
钱学熙:沈先生所提的问题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关键在自己。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很对,而与实际有冲突时,则有二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不顾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枪毙为止。另一条是妥协的路,暂时停笔,将来再说。实际上妥协也等于枪毙自己。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
钱学熙:刚才我们是假定冲突的情形。事实上是否冲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对?如认为对的,那末要牺牲也只好牺牲。但方向是否正确,必须仔细考虑。(《今日文学的方向》.《沈从文全集》27卷.)
可见,整个京派作家对于文学的前途都是充满忧虑的。他们提到文学是否应该有唯一正当的路,路上是否应当有“红绿灯”的问题。“路”和“红绿灯”的比喻说明以京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对文学的是否应当由文学之外的力量来决定和控制的忧虑。他们的讨论其实已经是在为自己选择位置了。文学不可能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在任何的社会情境之下都是如此。不过约束的方式不同罢了。在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的过程中,必然要将文学纳入到政治的约束范围之内。自由主义作家如何适应这种约束,如何在这种约束中寻找自己的创作路径,是他们都在思考的问题。
用“红绿灯”来比喻政治的方向,用其规则来比喻新中国的文艺政策是比较形象的。正如汪曾祺说的,政治的方向是法定的,是大家必须遵守的。如果遇上了红灯,是无论如何不可以通过的。结果,大部分的人只能选择钱学熙所说的第二条路,就是妥协,停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此时的沈从文还是希望新的时代能为文学在政治的缝隙中留出一点自由的空间。“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文学的批评功能是否还能延续,是他很关心的。他还是坚持认为文学的社会能就是传达人类共同感知和渴望的光明:“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他渴望文学创作的自由,文学功能的宽广。就是这份渴望使他不能像别人那样清醒,也就不具备别人那样的接受心理。他的理想化让他在现实面前栽了很大的跟头,以至于“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