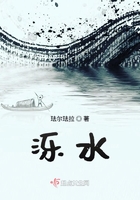这一幕,沈长安是舒心了,可急坏了阿莲,跺着脚直囔:“小姐怎就这么不开窍啊,世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怎还急着赶人呢!”
沈长安缓步走向阁楼,完全不理会身后焦急的阿莲,只问了一句:“洛阳的信,可送去了。”
“刚打算交给张三哥,恰巧碰见姑爷前来,一时忙着招呼姑爷,信还没送过去。”说完,看沈长安脸色不对,赶紧补充道:“小姐莫急,快马加鞭的话,明儿傍晚前六少爷就能看到信的。”
沈长安却是转身说道:“信,还是别送了,你撕了去吧,等会空了,去库房点算下我的嫁妆。”
这回换阿莲一头雾水:“点算您的嫁妆做什么,您的嫁妆一直是王叔打理,并没有交与王府的管家,肯定少不了的。”
沈长安却是瞪了眼阿莲:“就你话多,等会把王叔叫过来见我。”说罢,径直往阁楼走去。
阿莲挠了挠头,连声应下,又觉有些不对,半晌才反应过来,囔着:“小姐莫转移话题,我们刚明明是在说姑爷呢……”
可惜,阿莲的声音即便再大,沈长安却是听不见了,她早转进了阁楼,走回自己房间去享受午后慵懒的休憩时光了。若说沈长安之前还有被休弃的担忧,如今却很是安心,有了皇上那句话,她应该能安然地待在南平王府,她不过只是想回家,她想,阿娘也想……
贪吃妇人不做家,贪吃懒做笑呵呵。
堂前有地不肯扫,桌上灰尘用手拖。
客人来了慢腾腾,端出半碗灰尘半碗茶。
日里东家走西家,夜里点灯纺棉纱。
三年纺个鹅卵苎,四年纺个菜头纱。
菜头纱啊菜头纱,老鼠拖去当尾巴。
街头熟悉的歌谣传入马车,沈长安嘴角微扬,她还记得,十年前的城西永巷嫁进新妇,贪吃又懒做,邻里时常笑话,也不知谁顺口编了歌谣,竟然一唱十年。
马车穿过永巷,行至街尾便渐渐停了下来。都说近乡情怯,在阿莲的几番催促下,沈长安终是放开了紧握着的双手,掀开车帘,映入眼里的,还是十年前的红漆木门,由于脱色,已是斑驳几块,显得很是老旧。
“小姐,还要进去么?”看沈长安站在这户人家门口许久,却没有动作,阿莲不由出声问道。
沈长安长舒口气,摇了摇头:“还是回去吧,许是我记错了,这儿没有我的亲戚。”
阿莲点头,带着些嫌弃,说道:“我就说嘛,小姐的亲戚岂能住在这又旧又破的穷地方。今儿没找到便算了,改明儿让世子替小姐寻亲戚吧。”
才要转身,眼前的红漆木门突地被拉开,就这么没有预警地,当年的两居室小宅院就这么敞开在沈长安眼睛,竟让她有些措手不及的慌乱。
“世子妃?”
不大确定的询问声,才是让沈长安注意到从里头走出的男子,周天龙,曾有过几面之缘。
“您,怎么到这里来了?”周天龙一脸诧异地看着沈长安。
还不等沈长安回答,里头却是走出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拄着拐杖,一下一下摸索着前行。
“阿龙,来朋友了么?快请进来坐坐啊。”
直到坐在了院子里的石桌旁,沈长安才终于理清楚,她曾经住了七年的院子,如今却是周家在住着,她从不知道,朝堂里最年轻的京畿右卫军校尉,却出身如此贫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