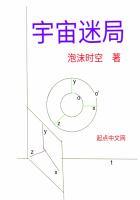沈长安挑眉:“沈燕怎么了?”
细雨连忙摆摆手,道:“燕姑娘没怎样,是,是福贵……福贵那日说,说他的荷包出宫时匆忙,没有来得及带出来,丢在宫里了。可,可其实出宫后,就是在这间酒坊里,我还看到过一次的。”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细雨仔细想了想,道:“也就是夫人带燕姑娘来的前半个月。”
沈长安沉默了会儿,没有说话,让细雨很是忐忑,赶紧解释着:“那日他们兄妹相认,我看着想起了自己的兄妹们,一时太感动而没反应过来,后来忆起,我想着许是福贵那几日自己弄丢了荷包不敢和夫人说,才扯了个谎,便没特意和夫人禀报,细雨当真不是想刻意瞒着夫人的。”
看细雨急切的模样,沈长安也没再追究,“罢了,你也是无心,但再不希望有下次,否则,你我的缘分也就尽了。”
细雨赶紧地点头:“再也不会了。”
细雨抱着仨儿上了沈长安马车,正要下去时,沈长安突然叫住她:“福贵前些时日只在酒坊,没去过别处?或是,有什么特别的人来找过他?”
细雨想了会儿,摇头:“前头的事情得问两位王大哥,我只每日好酒坊关了门才见到福贵的,不过,我倒是知道他常去城东收购高粱。”
再次经过长安街时,街头人头攒动,人群间议论的声音传来,沈长安才恍然,今日竟是柳家入罪,游街后押往刑部死囚牢房的日子。
百姓总是这样,囚车里的人也许与他们并没有多大仇恨,可总是爱显得自己很是大义凛然,大伙儿跟风开始唾弃起囚车里的囚犯,更带起一众的仇恨,甚至有些急性的,随手招呼了一些自己家的烂菜叶或是臭鸡蛋,可他们中不乏许多光顾过柳家的钱庄酒楼或是当铺赌场的。
沈长安的马车被官兵推开,甚至被人群挤走,却没有阻挡住沈长安的视线,黑压压的人群围着一条大道,两排有官兵护出了人墙。沈长安就这么安静地坐在马车里,看向前方大道,看着已经满身狼狈的柳泽成。想他贪婪一世,晚年竟是这般下场,那双眼眸一片灰白,已然绝望。而整条长安街上,最恨他的,便是此时平静得如同看一场好戏的沈长安,她恨他,恨了十年,恨到他不死,她不罢休。
“娘亲在看什么?”仨儿坐起身,也想往窗口探去,外头的热闹听得见却看不着,实在难受。
“没什么,在看报应。”沈长安放下帘子,阻隔了仨儿的视线,只道:“你生着病,莫要吹了风,咱们,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