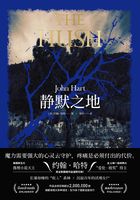我听见她们说,王春妮交了两千元钱准备拍影集,程兰香更了不得,不只交了影集的钱,而且交纳了培训费,她们现在要回去准备下,然后返回来,拍照片。王春妮问小鱼儿拍了哪一种,小鱼儿搔了搔头,说:“拍了个一千的,我没带那么多钱,先交了五百。拍摄那边忙,约了明天来拍照。”说话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听了她们的话,我就更不好意思说自己只拍了两百元的卡片了,站得远远的等了一会儿,见电梯来了,赶快走过去拉了小鱼儿进电梯,下楼的过程里只是和王春妮她们点了点头,没敢插话。
一路上小鱼儿一直很兴奋,鼓励我明天一定要去公司拍影集。可是让外头的冷风一吹,我心里原本的那份热切反倒消褪了些许,回头想了想整个事情的经过,觉得有点儿可疑,却说不清到底是哪里不对。
我问小鱼儿,你不是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吗?哪来的五百元钱交过去?
小鱼儿说他有个习惯,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留五百块钱存在银行卡里不动,遇上什么特别急的事儿才拿出来用,平时就是饿死,也不会取出来,刚刚他在环球公司是刷的卡。
原来还可以刷卡的?我摸了摸身边的小包,里头有那张妈妈给的卡片。
在回去的路上换车的时候,我看了看路边的自动提款机,想了想,还是没去取款。大学村里治安是很不让人放心的,我想还是明天来时的路上再取款吧,而且,我忽然觉得,这事儿还是去和丹露姐商量下好。
丹露一听到“影视公司”这几个字,就打断了小鱼儿眉飞色舞的讲述,大声对着我们喝问:“你们去了?影视公司?”
我和小鱼被她的气势所慑,齐齐望着她,点头。
“好,那说说吧,是拍无极第二部还是拍夜宴续集啊?”
我和小鱼儿看着丹露的表情更呆了。
“是,是黄金甲二。”小鱼儿说。
“那你们是表演了小品还是唱了歌啊?或者朗诵‘我轻轻的来’了?”丹露向我们眨着眼睛,表情与声音都忽然温柔起来,温柔得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你,你怎么知道?”小鱼儿的声音有点怯怯的。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丹露喃喃地说了两句,然后忽然跳起来,照着小鱼儿的头上就是一个狠狠的爆粟,“这种招式来北京混过三两个月的,有哪个不知道的?你去看看那些报纸,哪期上没有个三五十家招特邀演员、群众演员、平面模特的?亏你还在这里混了一两年了,竟然连这点小骗术都识不破!看你们俩这样子一定是上过当了,说,都交了多少钱?是照片费还是培训费?”
“我,交了五百。”小鱼儿说。
“我交了两百。”我低头,不敢看丹露姐,心里觉得特别羞惭,觉得自己特别白痴。
“你们,你们,气死我了!”丹露又打小鱼儿的头,没打我,只是用手指狠狠地指我,“你们有点头脑行不行,这么好哄好骗的,还在北京混个什么劲儿,敢快回家给你们爹妈当小白兔去吧。”
我的头更低了,朵朵一直爱叫我小白兔,原来,所有事情都有双面性,单纯也是要分场合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的。在朵朵那儿,我的单纯是可爱,而到了那些“老师”的面前,我的单纯就变成“可欺可骗”了。
“丹露姐,我知道有很多公司招演员的,也可能有骗子,可是这家不同啊,他们是全球最大的星探公司,他们的老总和总监认识很多导演和名星,还和他们拍过照呢,不信你问云瑶……”
我刚要点头,就被丹露“狮吼”般的声音吓回去了:“还全球最大,他们全球最大,我还全宇宙最大呢;和明星拍过照?和明星拍照还不容易,你去买张那些大明星演唱会的票子或者去宽店影视城门口蹲两天,见了个明星你就扮粉丝去缠着他们照相,弄几张和明星的合影还不容易!再说,电脑合成你懂不懂?不懂你听说过没?就是可以把两张照片上的人弄到一起去,明白没?”
小鱼儿不说话了,可还是有点疑惑的样子。
“我跟你说,这百分之百是骗局,不,百分之一万是骗局!你知道姐以前是干啥的吗?五年前刚到北京时我就和朋友开过一个星探公司,要说收报名费、服装费、培训费、照片费,靠着糊弄小朋友做明星梦发财,姐可是他们的祖宗,知道不?”丹露说,“你们怎么就不长点脑子,电影学院的专业毕业生有多少?别说是找男主角女配角的,就是露个脸有个镜头的演员,要多少还不有多少?轮得上你们?需要在报纸上招聘?你们去看看,电影学院门口蹲着多少等着当群众演员的呢,需要花钱在报纸上打广告或者满大街地拉人吗?”
我觉得丹露姐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现在我已经确信,这的确是一场骗局。
“我,我也是觉得这或者是个机会,需要好好把握。”小鱼儿说。
“机会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你看看你自己,全身上下哪里有一点儿是当明星的材料?”丹露喝问。
“话也不能这么说,露露姐,那王宝强还能当上明星呢,孙红雷以前还被人笑被人说成疯子呢,现在不都当了影帝了?只要坚持……”
小鱼儿刚刚抬起头准备发表长篇的慷慨陈词,丹露又是一巴掌打下去:“王宝强?孙红雷?你也不看看,全中国有几个王宝强孙红雷?这么大了你怎么还在做梦?进入影视圈,就算是真有那个机会,给你们个群众演员当当,想要当明星出人头地那是那么容易的吗?你们看见的是一个成功的,那背后可站着数以万计的失败的,不,不是站着是躺着,而且是躺在土里。站在那儿星光璀璨光茫四射的是一个人,下面埋的是几万几万的尸首!别的不说,你就看看我们隔壁郑家那姐俩,下场还不够惨的吗?”丹露说最后那一句时,压低了声音。
“郑家姐妹?她们怎么了?”我问。
郑家姐妹俩住在丹露的隔壁,同时也是住在我的隔壁,丹露是楼上第一间,我是第三间,郑家姐妹和姐姐的老公住在我们之间,就是晚上经常发出呻吟声被朵朵学了去的那个房间。可年后搬回来,好像晚上就没有声音了,而且,只见她们姐俩,从没见过那男的回来。
“怎么了?她们姐俩就是做着当影星的梦,一天到晚地做,天天到电影学院门口去找活干,四处托人找机会哪怕是当群众演员,只要有机会进入剧组不给工钱也干。为了在镜头上露个脸哪怕是一秒钟,为了说句台词哪怕是一个字,姐俩都可以陪那些剧组里说得上话的人上床。她们说这是为了梦想而牺牲,很有种视死如归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儿。可结果怎么样呢?她们来北京三年了,做临时演员也做了三年了,年前姐俩不知在哪儿染了性病,而且是一起染上的。郑秀秀就是老大的老公问怎么回事儿,连打带闹了好几场才搞明白,原来姐俩为了上镜一起去陪了一个男的,所以一起染上病了。秀秀她老公实在是受不了,连夜就搬走了。听郑文文说,她姐夫和姐姐高中时就好上了,都十几年了,而且一直对姐姐特别好,总在背后给她们打气默默地支持她们实现理想。可最后呢?姐俩不仅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染上了坏病,还把个好好的人给逼走了。”丹露说。
我呆呆地听着,原来,这姐妹俩的身上竟然藏着这样的故事,真是既可悲,又可怜:“那她们,她们的病好了吗?以后怎么办呢?”
“可能好了吧,前阵子总看她们手上贴着吊水后的白胶布,现在没有了,应该是治好了;可那病治好了也有后患,以后结婚生孩子都会受影响。不过以后的事儿,谁说得准呢。她们现在还是每天出去找活儿,继续以前的生活呗,继续向着理想努力呗。理想这东西啊,还真说不准,有时候,是个很光辉伟大的词儿,有时候,就像个黑洞,跳下去,就上不来了。”
我认真地回味着丹露的最后几句话,觉得,还真挺有道理的。凡事大概都是要有个限度吧,所谓的,物极必反。
很快大家都知道了我和小鱼儿的遭遇,以老巴为领头人对小鱼进行了一番批判,而且说他不只是自己糊涂,还给那些骗子变相当了回帮凶,把我也给连带进去了。小鱼儿特别地难过,不只是心疼他那五百块钱,而且对我也充满了歉意,他一个劲儿地跟我说,等赚了钱他一定把我那两百元还给我。我对他的逻辑有点不解,跟他说那些钱又不是进了他的口袋,凭什么让他还呢;的确是他让我去那家环球公司的,可我也是有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能力的,上不上当还得看自己。我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怎么能让别人埋单?
小鱼儿于是不再提还我钱的事,专心地去为自己的五百块钱心疼了。一直没说话的卫君泽说:“小鱼儿你得跟云瑶学学,像人家那样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五百块钱没了是小事儿,重要的是,你得在这件事里吸取经验,要不然,五千五万的大当还有得上呢。”
我觉得卫君泽的话很有道理,可小鱼儿却不以为然,叨念着说:“五千五万,我想去上那样的当我也得有那么多钱啊,五百元,已经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晚上我躺在榻榻米上想着这一天的经历,从看到偶像般的“徐总”到那些墙上的明星偶像;从环球公司宽敞明亮的办公环境到那些像模像样的“专业老师”;从唱歌的王春妮、羞怯得说不出话来的程兰香到那些在地上摸爬滚打的男孩……后来我想,那几十个和我一样的年轻人,能够在环球公司这种专业化系统化的“组团忽悠”下不掏钱不上当的只怕不多吧。那一天是几十个,一个月就是上万个啊。丹露姐说这样的公司很多,在北京至少有上千家,他们就是在依靠我们的单纯、我们的梦想活着,用他们的欺骗赚钱,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可恨。可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天真,那些人又怎么能得逞呢?而且说“天真”,也是个极美化了的词,天真地追求梦想,那些梦想又是什么呢?广义上说,是“成功”,可成功又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这不也是一种物欲的贪婪吗?只有我们本身有贪念,才会给那些骗子以可乘之机。那么按照这样的推理,我们在北京打拼奋斗不也是为了成功吗?那是不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艰苦的生活全是因为我们对物欲的“贪念”?这才是所谓的理想背后的真实?
我想了很多,想不懂、想不通。然后我想起,从“凤翔”公司面试出来时,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成熟了,整个人长大了,并且因此而生出一种带着些许苍桑的自得。其实,我并没有长大,也没有我想象中成熟,还有太多东西,我看不穿、弄不懂。
又想了一会儿,我睡着了。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希望明天是愉快的一天、好运气的一天。